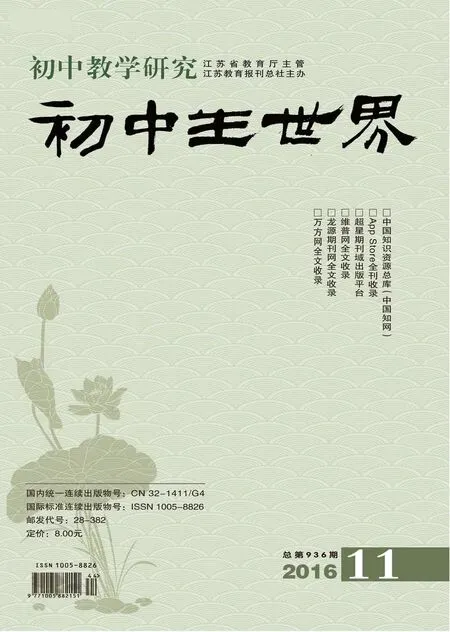適度教學如何從應然走向實然
■秦曉華
適度教學如何從應然走向實然
■秦曉華
《中庸》首章即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位育之道,在于和諧、適度,古人早就知道。只是,知道是一回事,做到是另一回事。否則,明代王守仁就不會在《傳習錄》中說出“若近世之訓蒙稚者,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這樣的話了。現在的教育教學狀況也不盡如人意。在我看來,主要問題是失之于窄,失之于淺。
所謂失之于窄,是指把教育窄化為教學,把教學窄化為學業,把學業窄化為考試,把考試窄化為分數。見分不見人,幾成常態。我們常抱怨社會道德浮薄,公民素養滑坡,我們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我們的學校教育在社會所需要的核心素養培育方面到底做了什么?做了多少?我曾在美國一所小學看到過兩個“怪現象”。一是所有的走廊、道路兩側均劃了一條黃線。正不明所以,下課鈴響了,我們瞬間明白了黃線的意義:所有的孩子排成一隊,在教師的帶領下,沿黃線行走。二是所有的孩子在行走時,均把食指輕輕放在嘴唇上。正不明所以,一小朋友見到我們這些外國人,本能地張口喊道:“Hello!”只見后面的小朋友用手指戳了戳他,做了一個將食指放在嘴唇上的動作。我們瞬間明白了這個動作的含義。像這樣從小就高度重視培養公共生活習慣(比如靠右行走,公共場合不大聲喧嘩)的做法,值得我們認真借鑒。
所謂失之于淺,是指將復雜的思維過程淺化為結果或結論的識記。實事求是地說,現在數學學科也幾乎成了文科,培養的不是思維,而是記憶。我曾到一所高考成績非常突出的學校聽了一節數學課,看到令人震驚的一幕:當老師給出高考真題(填空)時,學生直接提筆寫答案。我問學生為何不經計算就得出答案,他的回答是,這個題目已經不知刷過多少遍了。這種答題的自動化程度,讓人且喜且憂,喜的是學生的乖巧勤奮,憂的是這樣的過度訓練已背離了數學學習的本義。基礎教育重在奠基,奠基的關鍵不是精細、精致,而是深廣、扎實。粗糙一點不要緊,可怕的是根基太淺,沒有上升空間。畢業于西南聯大的任繼愈先生曾這樣評價現在的學生:除了題目做得很深以外,他們知道的很少,他們上不去。任先生可謂一語中的,基礎淺薄,視界狹隘,難成大器。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現在的孩子缺少獨立思考的能力,更缺少理性質疑、探究評價等高階思維能力。他們不乏觀點,但缺少思想。當然,問題的癥結不在學生,而在教育的價值取向。價值的特性離不開工具性(功利性),工具性甚至是價值的必然屬性;但工具性絕不是價值的唯一屬性,正當性毫無疑問也是價值的必然屬性。教育有其功利性,但不能將功利性作為唯一的追求和取向,它必須在功利性和正當性之間取得平衡、求得中和,才有可能是適時適度的。比如追求高分本無可厚非,但如果因此而全面占領學生的時間、空間,濫用題海戰術,無視學生的興趣愛好、內生動力,一味死揪硬灌,那就失去了價值的正當性,是不道德的教育。因此,確立正確的價值取向是實現適度教學的思想基礎。
實現適度教學還要思考的一點是,適度不適度應該由誰說了算。我認為不能僅由教師說了算,要充分重視學生的意見。教學如何適應學生的需求,這才是適度教學的本質追求。夏丏尊先生曾感慨:“學校教育到了現在,真空虛極了。單從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馬燈似的更變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從未聞有人培養顧及。好像掘池,有人說四方形好,有人又說圓形好,朝三暮四地改個不休,而于池所以為池的要素的水,反無人注意。”夏先生說的極是,如果不能堅持學生立場,所謂適度教學的提倡很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就像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里描述的那樣,以“愛”和“憂”的名義“害之”“仇之”。
適度教學的本質是以正當的方式促進每一個學生全面、和諧、可持續地發展。因此,尊重差異性的原則就顯得非常重要了。每一個孩子都是不同的,對所謂的“度”的適應性也是不同的。比如,對一個喜歡數學的孩子來說,用兩三個小時甚至半天時間攻克一道難題,應該算不上不適當;但對于一個數理邏輯感受力比較弱,對數學缺乏相應基礎和興趣的孩子來說,則可能是一種巨大的折磨。謝邦敏是新中國成立后北京第一刑庭庭長。他在南開中學讀書時喜歡文學而物理極差,參加畢業考試時物理一道題都不會,只好在試卷上賦詞《鷓鴣天》一首:“曉號悠揚枕上聞,余魂迷入考場門。平時放蕩幾折齒,幾度迷茫欲斷魂。題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電磁溫。今朝縱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組人。”他的物理老師,也是后來的中科院資深院士魏榮爵先生看到后,認為該生雖然物理交了白卷,但詞寫得真不錯,是個人才,不能斷送他的前程。于是賦詩一首:“卷雖白卷,詞卻好詞。人各有志,給分六十。”謝邦敏居然就憑借這60分順利畢業,成就了后來的功業。
承認差異,容人之短,揚人之長,這是適度教學的基本前提。基于這種認識,我認為實現適度教學的路徑就是給學生提供豐富的、可選擇的課程資源。在西方世界,課程(Curriculum)一詞最早出現在英國教育家斯賓塞《什么知識最有價值?》(1859)一文中。它是從拉丁語“Currere”一詞派生出來的。“Currere”一詞的名詞形式意為“跑道”,由此理解,課程就是為不同學生設計的不同軌道;而“Currere”的動詞形式是指“奔跑”,由此理解,課程的著眼點應放在個體認識的獨特性和經驗的自我建構上。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我對課程的理解就是讓不同的學生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跑道上奔跑,換言之,適度的教學就是讓不同的學生以不同的方式學習不同的課程。
要想建構適度的教學,課程體系必須從單一走向多元,從封閉走向開放。就像佐藤學所說的那樣,我們必須擯棄階梯型的課程體系,那是單向度的、重結果的、封閉的;我們必須轉向登山型的課程體系,那是可自由選擇的、重過程的、開放的:我和誰一起登山、如何登山、從哪條線路登山、什么時候登山等等,都是可以選擇的。學科之間與學科內部的整合、微課程與課程鏈的解構與建構、校本選修、社團活動、研究性學習、游學傳統的恢復等等,都是滿足學生不同學習需求,促進其多樣選擇、多元成才的有益方式。總之,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可選擇的課程是實現適度教學的根本路徑。
實現適度教學的第三個要件是適度師生關系的構建。教學失度的始作俑者固然不是教師,教育的本質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矛盾沖突、考試的指揮棒作用、用人單位的高門檻、唯分數論英雄的管理思維、家長以及社會對學校和教師的輿論“綁架”等等,都可能導致教育教學的失序失范。但不可否認的是,至少在師生關系這個范疇里,教師居于強勢地位,學生處于弱勢地位,教師的主動選擇、理性作為還是可以改變很多東西的。而實際上,教師在師生關系上的處置不當,很多情況下會加重教學的失度。我在前文提到,現在的學生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那是因為在教學中,我們幾乎沒有給他們自由思考的機會。當一切都要統一到標準答案上的時候,所謂獨立思考、自由表達只能是遙遠而美好的文學想象罷了。然而吊詭的是,生活可不像考試,哪有那么多的標準答案?生活無非是一系列選擇和接受的過程,可惜的是,學校從來沒教過這些東西。如此看來,很多成績優秀的孩子進入社會后感到茫然無措,根本不足為奇。適度的師生關系,在我看來,就是教師退居暗示、指導的地位,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角。朱熹曾經說過:“讀書是自己讀書,為學是自己為學,不干別人一線事,別人助自家不得;某此間講話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只是做個引路底人,做得個證明底人,有難處,同商量而已。”這種說法雖有以學程代課程之嫌,但就對師生關系的剖析來說,無疑是很有道理的。梅貽琦的“從游說”對師生應然關系的闡釋也非常親切:“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同商量”也好,“從游”也好,體現了師生的和諧關系,在這一關系中,學生是主動的、活潑的,教師是引領者、陪伴者。這種適度師生關系的確立是實現適度教學的必要前提。
(作者為江蘇省中學語文特級教師、中學正高級教師,江蘇省徐州高級中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