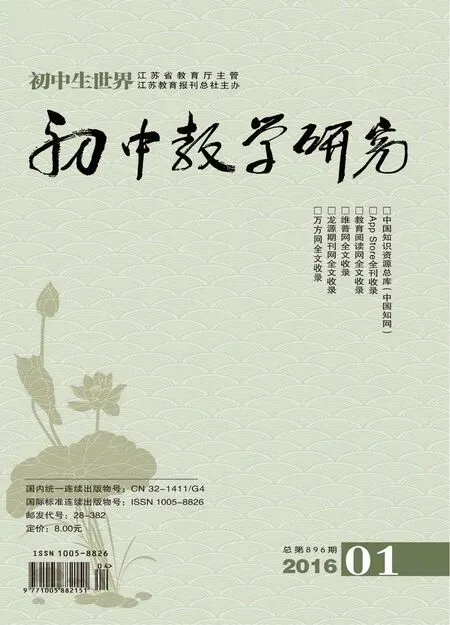“審美人生教育”美術課堂教學模式詮釋(上)
■陳鐵梅
?
“審美人生教育”美術課堂教學模式詮釋(上)
■陳鐵梅
編者按
中小學美術課堂教學的理想境界是怎樣的?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怎樣的課堂學生才會收獲更多?學生能從這樣的課堂上收獲什么?本文作者經過20多年的美術教學實踐與研究,煉成了“審美人生教育”教學主張,梳理、總結出了“寬度·密度·向度”美術課堂教學模式。本文對此教學模式進行詮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也許會給其他學科的課堂教學帶來一些思考。本專欄分三期連載刊發,本期刊發上篇。
一直以來,我所追尋的理想的美術課堂,一定是高效且愉悅的——它與審美目標、技能目標、情感目標如影相隨,或是名作和大師撲面而來,或是線條、構圖、透視直抵內核,或是臨摹、創作應接不暇……但這絕不累人,學生與教師同在課堂,同在這生命場,徜徉其中,享受至真至純的唯美、心定心靜的安寧、創生創造的快意。
這樣的美術課堂是常態下的。常態,不排除公開課那樣的“表演”,因為每一個教師都當是“演員”,更當是導演。是演員,激情投入,心無旁騖,不管誰坐在教室里,教師依然旁若無人,心中只有學生。是導演,周密安排每一個教學環節,以高超的教學藝術吸引每一個學生“入戲”。這樣的美術課堂也是平時都能上的課,而不是很多人、很多次“教研”后才能上的課。這樣的課堂也許有著些許缺憾,但“教學是缺憾的藝術”,只要愿意,缺憾就給教師留有反思的余地、進步的空間、重建的可能。
這樣的美術課堂是生成性的。每一個學生的生活經驗不同、個性不同,對美的感悟不同,對美的領悟、表述、創造也各有千秋,這也就決定了課堂不完全是預設的,而是有教師和學生的真實的、情感的、智慧的、思維的、能力的投入和互動,氣氛活躍,有感而發,有悟有創。在這個過程中,既有資源的生成,又有過程、狀態的生成。
這樣的美術課堂是有效率的。它融聚了全班每一個學生的情感和智慧,大家都積極參與其中,不僅喜愛美術的學生能碰撞出思維的火花,對美術喜愛程度一般的學生也會在美的召喚下樂在其中,即便是對美術課程“愛理不理”的學生也會在教師的啟發下、在同伴的影響下接收到美的信息。
這樣的美術課堂是有意義的。它在課件媒體、游戲討論、展示表演等熱鬧中剝離出“有意義且有意思”的味道。學生在這樣的課堂里能學到并增長美術技能,開闊美術視野,增強觀察能力,啟發創造性思維,享受審美快樂,甚至產生以藝術門類的工作為終身職業和事業的志趣,而更多的學生則隨時隨處享受到藝術所帶來的快樂。
這樣的美術課堂將帶著學生從幸福出發,作美麗而愜意的徜徉。我以此強調,美術教學的根本任務,是為學生當下的快樂和未來的幸福提升必需的藝術素養,為他們的天性稟賦和成長發展培養必備的創新能力。
一、問題的提出
2006年,已經在初中美術教學一線工作了16年的我,經歷了“木散為器、帛裁成衣”圖案分解構成教學思考,進行了“取象造化、妙趣天成”工藝教學探索、“寓教于樂、教學相長”和“后導式教學法”的探索,以及“中學美術課堂階段過程評價與階段考評研究”的探索,對美術教學內容、學習興趣、評價體系進行了摸索、實驗;也經歷了教育部首屆跨世紀“園丁工程”全國美術骨干教師培訓,以及美術教育學者、課程標準制定組組長尹少淳教授主持的《美術課程標準》制定前期準備工作,對初中生身心健康成長的目標和方向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作為一線美術教師,我認為初中美術教學面臨著一些新的問題和困境。
美術教學與人生教育脫節,育人功能得不到全面、充分的彰顯,主要表現為:
首先,美術教學過程中對學生人生價值導向的關注度不夠,教學時不時游離于道德教育之外,教學功利色彩濃重,學校里的美術教學有時候變成了素質教育的外衣。美,無時不在,也無處不在。滿目蔥蘢中,紅色和黃色的小花隨風搖曳,它以無聲的語言昭示著對比之美;故宮建筑群在“黃道”中軸線上鋪展開來,它用布局演繹著對稱之美;敦煌飛天,揮舞曼妙羅袖,它用造型展示著韻律之美;詩詞歌賦朗朗上口,韻味十足,它用語言表現節奏之美……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美常被熟視無睹,緊隨而來的美的法則,也就無從談起。
其次,美術教育依然在不知不覺中被窄化成技能教學,初中美術教學“重術輕美”的現象依然存在,教師用成年人的感覺、視野、思維和方法來“越位”和“代替”處于審美“敏感期”“興奮期”的學生,用艱深的技能“恐嚇”學生,使得學生審美的眼睛被迫逃離,原本美妙的美術變得不再美妙,美術學習被扭曲、被肢解。美術與學生漸行漸遠,而遠離了學生的美術就可能永遠無法回歸其自身。正如蘇霍姆林斯基所說:“兒童時代錯過了的東西,到了少年時代就無法彌補,到了成年時期就更加無望了。這一規律涉及孩子精神生活的各個領域,特別是美育。”
教學過程中,地方美術文化課程內容的缺失導致文化傳承斷裂,學生無視生活中的美、身邊的美,培養的“藝術人”的文化基因不全。地方美術文化傳遞、展示著一個地方精神生活的結晶,因此,美術教育天生就與地方美術文化血脈相連,二者在相互作用中,共同提升著學生的審美品位,也鍛造著學生的民族文化之魂。但是,我們常看到,在對現代藝術設計推崇備至的課堂上,難以見到地方美術的蹤影,這樣的缺失,使學生無法融入民族文化的海洋中;這樣的缺失,使學生無法理解魯迅先生說的那句話,無法理解地方美術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二、相關思考
以上問題,觸發了我對美術教學的重新思考。在我看來:
1.美術教學應該給學生的將來帶來超越學科知識與技術的審美人生。也就是說,學生通過美術學習,除了掌握一定的美術學科知識和技能之外,還應該樂觀進取、積極向上,學會關注社會、尊重他人,為成長為人格健全、生命充實的社會人夯實基礎。這既指向學生當下的生活,也指向學生未來的生活。因為,美術的學習過程,在培養記憶、觀察等能力的基礎上,一定伴隨著聚精會神、堅持不懈、有的放矢等,這些都是形成人的完整人格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美術的不斷學習的過程,就是促使形成富有個性化的、獨特的、穩定的、統整的行為模式、思維模式和情緒模式的過程,這無疑對人的當下生活和今后的成長、發展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2.每一個學生都有美術潛能,它與生俱來,并隨著人的誕生和思維發展一同生發,而且由于其思維的形象性,往往最早被發現,繼而被重視與開發。所以,在以表達動作經驗為特征的涂鴉期、以符號推理以及空間概念為特征的樣式化期和有了一定寫實概念的黨群期,人的美術表現能力極強,這是大家都認同的。但隨著人的心智水平的不斷發展,語言能力、邏輯能力、數學能力等被慢慢強化,而美術潛能相比之下被弱化、被淡化,甚至被遺忘。初中階段是這一變化過程的分水嶺。由于個體智力水平的提高、教育的導向以及生活經驗等因素,初中階段的學生在美術表現形式上開始有意無意地希望表達主觀,“寫實”是其目標,“像”與“不像”是其評判標準,這一標準不乏成人的評價導向所起的潛移默化的作用。漸漸地,他們發現做到“像”很難,當失敗的經驗不斷地被復加和強調時,學生逐漸喪失了信心,這也就是一部分人在這一時期中斷了美術創作的原因。總而言之,美術潛能極容易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喪失,這就對美術教育教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學校教育不能使美術成為“兒童時代錯過了的東西”,我們有責任幫助學生擁有追求美、創造美的幸福美好人生。
3.美術教師不僅僅是知識技術的傳播者,更應該是學生的人生導師。美術教師與其他學科的任何一名教師一樣,有責任幫助學生去省察日常生活、反觀自我成長。而美術教師擁有一個更為神奇的、重要的“魔杖”,那就是審美,它可以“點化”學生的雙眸,幫助學生學會用美術的眼睛去看待世界,在心靈上發現自我,在精神上獲得豐盈,在生命上感到平等,在人生中活得從容。
基于以上認識,2008年,我提出了“審美人生教育”教學主張,旨在幫助學生通過美術學習獲得知識技能,感悟生活,提升素養,拓寬胸襟,涵養人格,升華人生境界,成長為人格健全、生命充實的人。
三、理論依據
1.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
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認為:任何事物的發展變化,都是內外因相互作用的結果,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教學中,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是內因,只有通過主動學習,才能建立自己的認知體系而求得主動發展。美術教學一方面讓學生在教學中體驗知識學習的理性壓迫力,鍛煉用意志克服困難,獲得對世界的認識和適應并超越世界的能力;同時,讓本該體驗的感性愉快——滲透了理性的感性愉快,即審美愉快,也常駐學生心間。這就在發展學生理性的同時,優育他們的感性,讓他們真正擁有“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和“有音樂感的耳朵”(馬克思語)。須知,感性對于人的成長,并不比理性的發展來得次要。
2.席勒等國外美學家關于美育的理論。
世界美育的先驅席勒這樣說:“只有通過美,人才能到達自由。”他以此強調審美教育在整體教育中有著獨特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高爾泰等美學家都以自己獨特的理論強調了審美在人的精神領域里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審美教育能激發人的情感,能引導人成為摒棄功利思想、追求真理的人,從而達到生命自身的美化和歡悅。試想,當經由我們教育的學生長大成人后,不為物累,能以非功利的審美態度來觀照人生;不受自然必然性和社會必然性的羈束,從容淡定,去建設自己和他人共同擁有的美好生活,這是怎樣一種教育的成功!
3.孔子等中國思想家、教育家關于美育的理論。
孔子認為,教育的過程是人格塑造,是一個“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過程,他高度評價了審美在教育中的作用。中國美學史上關于美育理論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還有王國維、蔡元培等,王國維提倡要把美育和德育、智育、體育相提并論,使美育成為培養“完全”人的一項重要內容。蔡元培則提出“教育和美育才能真正陶冶人的情操,培養人的良好品質”。中國現代學者王統照、郭沫若、呂徵、豐子愷、朱光潛和周揚等人也都對美育提出過至關重要的論述。他們的核心思想就是通過審美教育激活“審美態度”,并以此觀照生活,實現美的人生即在于“使受教育者一輩子受用”(葉圣陶語)。這些理論不僅具有極高的理論價值,也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為本模式的構建提供了翔實和可借鑒的依據。
(作者為江蘇省人民教育家培養對象、江蘇省特級教師、教授級中學高級教師,現任教于江蘇省海門市東洲國際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