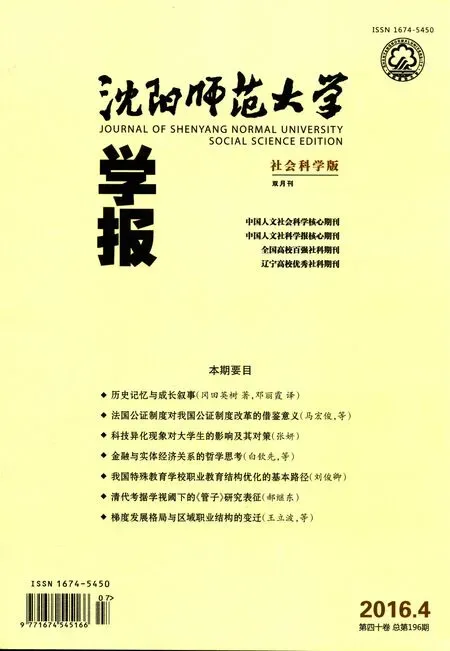清代考據學視閾下的《管子》研究表征
郝繼東
(沈陽師范大學文學院,遼寧沈陽110034)
文學綜論
清代考據學視閾下的《管子》研究表征
郝繼東
(沈陽師范大學文學院,遼寧沈陽110034)
有清一代,考據是其學術標簽。《管子》是明清以來學以致用的讀本。通觀清代考據學者研究《管子》的文獻,并結合有清一代的學術環境來分析,不難發現考據學者研究《管子》的一些共性:由于文字高壓而去政治化,但又試圖表達經世致用;由于以子證經而形成札記體,但又因考據而泥于考據等等。分析考據學家對《管子》的研究特征可以感知清代學者的學術取向。
清代;管子;考據;表征
有清一代,考據學在學術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因考據而產生一大批學者和學術成果。考據學是以考據為主要研究手段而形成的一門學問,其學者可稱之為考據家。乾嘉時期的大多學者以考據學為主形成了頗具特色的學術流派,我們稱之為乾嘉學派,此學派后來也包括整個清代的考據學者。樸學是指清代考據學者的學術思想主要回歸到漢代以來的樸實學術風氣上來,形成的著作以實學為主。因此,考據學、乾嘉學、樸學是對同一學術群體從不同角度的稱呼,筆者以為同實而異名。以下所述有可能會有互稱之處。
作為影響有清一代的學術,考據學有其自身獨特的學術風格,并以獨特的學術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影響了清以后的學術世界。在《管子》研究上,考據學也表現出一貫的特色。如果我們觀照整個有清一代乃至前后的學術流變,就會發現《管子》的研究在這一學派的眼里具有不同于其他學派、其他諸子研究的獨特學術魅力。
一
在清代學術高壓政策的影響下,學者遵循去政治化的學術研究規約。
受清初封建專制文化高壓政策的影響,再加上統治者的政治利誘,乾嘉及以后的學風較之早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清代早期學術大師們的“務博”“求實”學風雖在,而“經世致用”的學風卻在文字獄等政策的打壓和其他學術因素的影響下漸漸內隱,許多知識分子由積極入世的“外王”走入了修身養性的“內圣”,埋頭于故紙堆,從事古籍的校勘、注釋、考證等工作。楊緒敏、安超曾撰文認為,“但是應該看到,乾嘉學者在治學的過程中,往往只能進行一些脫離實際的繁瑣考據,滿足于一事一物的孤立考證,對一些重大問題無法做出帶有規律性的解釋,更無法將他們對某些問題的認識提高到哲學的高度(戴震例外)”[1]。從學術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乾嘉學者在學術研究上脫離政治是時代的必然,但如果說乾嘉學派的學術研究脫離現實則為過激之辭,它是適應時代需要而形成的特有學風,有其義理的曲折主張。
明末清初之際,學風由空疏轉而求實,以顧炎武為代表的學者舉起樸實大旗,一反明末之空疏學風,并提出“經世致用”的主張。從學術思想的角度看,顧氏對樸學的張揚是新時代學術變革的要求,也是學者試圖“以學治國”的表現,可以說走的正是“外王”的路子。但清初的政治策略并不能讓這些飽學之士獲得政治認可的機會,而他們的學術成就反而受到了清朝統治者的青睞。于是客觀上出現了兩種結果:一是明末空疏的學風得到了扭轉,樸學、實學得以流行;二是“以學治國”的試圖受到打壓,脫離政治的純學術卻得到了承認并宣揚,清初文字獄等就是前者的體現,組織編撰大型圖書及在全國興辦書院就是后者的注腳。
乾嘉學者對《管子》的研究,依然遵循著去政治化這一學術規約,即便是在學術空氣較為自由的清代中后期。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清廷的政治打壓,雖然清代中后期有相對學術自由,但學者依舊對文字獄等政治迫害心有余悸,再加上民族矛盾的逐漸深入,乾嘉學者仍不敢大膽地提出自己的主張,而是做借助考據之功復原古籍之事;二是考據手段對義理發揮的限制,考據是一種求真務實的治學方法,雖然“由文字訓詁而義理”“訓詁明而后義理明”是乾嘉學派的終極任務,但多數學者是實踐了前者而輕視或忽視了后者,當然在求真上比前代更進了一步,但在義理發揮上是一種倒退。總之,考據學者的《管子》研究,從總體思想上仍然是就學術而學術,由考據而考據。當然,其對《管子》的整理研究之功,還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劉仲華認為:“清代考據學者試圖通過文字訓詁以闡明圣賢之道這種學術邏輯的建立,致使清代學者對先秦古籍的研究從群經開始,接著為求證經學,又涉及先秦諸子。諸子之中最先遭遇到的是儒家陣營之內不受歡迎的《荀子》,接著是儒家以外的‘異端’,如《墨子》《老子》《管子》等。”[2]劉氏的評價是從宏觀的角度探討整個先秦諸子的,但也涵蓋了對《管子》的評價。而去政治化的學術規約無疑使考據學者只問學術而不及其余,其積極意義是《管子》的基礎研究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并為后世深入研究做好了儲備。
二
由于考據理論的成熟,《管子》研究文獻中出現了考據學方法的規模化運用。
明末清初理學的式微和乾嘉時期的學術延展給了考據學者更多的壓力與動力,他們既要考慮同舊有的宋明理學風格迥異,也要照顧學術的延續與繼承。因此,學者們試圖找到二者的平衡點。于是,他們將儒學仍定為亙古不變的研究對象,但研究手段有所變化,考據成為重要的研究方法被提到相當高的位置。美國學者艾爾曼認為:“清代學者不僅注意學術進步的連續性,還追求學術的獨創性。盡管宋明理學也推崇學術發明,但直至清代,學術創新才成為明確的學術目標。考據研究各個領域都面臨著‘發前人所未發’的壓力。……考證是四庫館臣審議其著錄圖書的標準之一。‘發明’‘心得’則是他們評判古今圖書的另一標準(如同資料引用、史料考證等)。人們鼓勵學者們超越前代的學術成就,充實已有的學術定論。”[3]因此,考據方法的運用是作為有別于理學空談的重要方法論而提出的,是學術的創新,其目的是對宋明理學說解的糾偏,最終目的是建立新的學術研究體系。
清初顧炎武曾主張博學于文,并在經學之外對諸子有所重視。他作《著書之難》一文,說:“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匯而為書,此子書之一變也。”[4]他對那些自成一家之言的子書青眼有加,也就是強調了立言的重要性。乾嘉學者以博學為第一要務,應當是受到了顧炎武的啟發。而考據的形成條件之一就是這種博學兼采的學風。另外,考據學的顯性表現是重視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的考證方法,立論一定要有證據,而且要廣征博引,故有“言必有征,典必采本”[2]104之說。
乾嘉時期,考據達到了規模化運作的程度,就以四庫館臣為例,據李杰援引清代學者張之洞《國朝著述家姓名錄》介紹,四庫館臣中學者雖然多達360人,但實際著述者僅21人,這21人除7人外,均為漢學派,即所謂考據家,并在四庫館內擔任要職,“充分發揮考據學派的特長,都為《四庫全書》的編纂做出了重要貢獻”[5]。《四庫全書》的編纂是清代重要的學術活動之一,得到統治者的大力提倡,其中所用的編纂人員多為考據學者,不難想見當時考據風氣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
《管子》的研究雖然在不同時期的考據學者表現為不同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成果,但其研究方法卻極其相似,這種方法便是考據。考據講求實證,而實證在當時又被認為是科學的方法而大量使用,并逐漸形成無所不用其極的情形。我們看乾嘉學者的《管子》研究,大多表現為繁瑣的考據,最為典型的是王紹蘭的《管子地員篇注》,注一句而動則千言萬言,因此郭沫若《管子集校》稱其為“說頗滋蔓”[6]。筆者認為,考據的繁瑣也并非一無是處,起碼在后學看來,這樣的成果為他們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基礎材料。現代《管子》研究一派繁榮局面,大多得益于乾嘉學者扎實的考據成果。
三
由于以子證經學術理念的影響,子學研究并未出現規模化。因此在研究體式上,學者自覺運用札記體的學術研究范式。
一般來說,札記是讀書時摘記的要點和心得體會及見聞的單篇文章,匯集多篇成書,仍稱“札記”。而清代乾嘉學者多采用這種形式對諸子研究進一步總結。美國學者艾爾曼認為:“宋明理學家的多數作品是抽象的思辨的記錄,它們大多采用問答、格言、辯論、詩歌等著述形式。理學信徒逐字逐句地把朱子、王陽明的談話內容記錄下來,尊為其學說思想加以傳播。與之相反,從17世紀的顧炎武到19世紀的學海堂學生,清代學者都十分推崇札記體,用以記錄偶爾碰到、讀到乃至聽到的有價值的史料。清代考據學者運用札記冊子,收集與有關選題相關的史料。“事實上,札記體本身即是清代學者重要的著述形式,又可被視為供其他學者引用的資料性著作。”[3]122以札記為考據學最終表現形式,是與宋明理學以問答、格言、辯論、詩歌為著述形式最大的不同。
考據學者采用札記體的著述形式不單單為了追求和明清理學風格上的不同,而是另有原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以子證經的研究初衷。清代以經學為中心的學術建構依然有強大的話語場,它必然要求學者在學術研究時以經學為主,這導致學者在擴大學術視野時難以脫離經學的束縛。因此,當諸子研究重新恢復學術生命時,便以“以子證經”或者坦白地說是以被利用的身份出現,即使在道咸以后,也擺脫不了為經學服務的干系。劉仲華將清儒“以子證經”用途列為四端:解經、古音、訓詁、辨偽,并于訓詁下有一段比較精要的論述,茲引于下。
一般來講,六經與先秦諸子的產生時代,早于史書和文集。也正因為經、子的時間更與三代相符或相近,所以治小學者往往特別重視六經與先秦子書中的證據。至于六經,自漢代以來,一直是訓詁的主要對象和材料來源,對于先秦諸子的重視則不夠多。明末清初以后,考據學逐漸興起,尤其是音韻學與訓詁學發達起來。清儒治小學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除了立足于六經以外,更注重于先秦子書以及其他書籍。他們不僅援用子書的材料進行音韻訓詁學研究,而且對眾多子書進行訓詁注釋。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講,清儒對子書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清代音韻訓詁學的發達[2]122。
“以子證經”正說明了諸子在學術研究中的地位,而正由于處于這樣的地位導致諸子研究成果的形式便以札記體為主。札記體的研究比較符合以經學為中心的諸子研究觀念,即博搜廣考經學以外諸子的客觀需要,當材料被累積成書時,其原有的札記形態仍然保留在著述中。
清代中期學者王念孫父子,后期學者俞樾、孫詒讓,他們對諸子的研究乃以札記的形態呈現。王念孫的《讀書雜志》中有《管子》札記的部分,俞樾的《諸子平議》中有《管子》札記的部分,孫詒讓的《札》也有《管子》札記的部分。這些都是比較典型的札記體研究。如果我們把目光轉向其他乾嘉學派《管子》研究者,就會發現札記形式是他們研究的共性。比如戴望有《管子校正》24卷,表面看似乎是著作形態,但實際上仍保留著札記形態的影子,或者說保留著由札記而成書的形成過程。戴望博覽群書,于《管子》版本及校釋著作皆有所涉獵,就其《管子校正》編撰的形態來看,即以各本及研究著作為參照,以自己的心得體會為總結,有則出注,無則不出,體現了札記式的自由。當然,在最后輯集刊刻時,經過了后期的加工,使其更加規范及有規律性可言。可見,考據家在《管子》研究中都普遍接受札記體寫作范式,形成了在形式上較為自由的札記體著作。
四
由于《管子》是一本實用之書,在政治高壓下,學者們對經世致用思想以內隱的方式表達。
前面提到,乾嘉學者在著述時往往有去政治化的思想傾向,致使有些學者認為其脫離現實,如前面所提到的楊緒敏、安超的觀點。筆者認為,這樣的評價過于嚴刻。乾嘉學者之學風并不是嚴重脫離現實,而正是出于對現實社會的考慮而做出的無奈選擇。更何況他們校勘、注釋、考證的終極目的是“明義理”,其真實意圖乃與“經世致用”暗合。
汪高鑫先生曾對“通經致用”(筆者按:應與“經世致用”類同)有很好的注釋,茲引如下。
所謂“通經致用”,顧名思義,是指通曉經術以求致用。這個“經”,是指以“六經”經傳為主要代表的儒家經典;而這個“用”,其具體內涵即為儒家所說的“立德”與“立功”,或者說“內圣”與“外王”,前者主要是指個人的儒家道德修養,后者則是指用經術經世干政。在“通經”與“致用”二者關系中,“通經”是“致用”的前提,而“致用”則是“通經”的目的。在中國經學發展史上,“通經致用”一直是作為一種中心觀念和核心價值被加以標榜和提倡的[7]。
汪氏認為,無論是通經、立德、內圣,還是致用、立功、外王,二者雖然有明顯的不同,但二者研習的是相同文本的儒家經典,遵循的是儒家共同的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從上述觀點我們可以認為,乾嘉時期學者表面上追尋的是通經、內圣的路子,但也不排除他們通過對經典的習得而達到致用、外王的訴求。
之所以對經世致用之說作如此多的敘述,是為了更好說明考據學者的《管子》研究成果是對這一思想的隱性表達。前面我們提到,乾嘉學者的《管子》研究遵循著去政治化的學術規約,但去政治化并不等于不關心“致用”。其實,乾嘉學者熱衷于《管子》研究的原因即是《管子》具有極其豐富的“外王”內涵。黎翔鳳先生的《管子校注》對《管子》的義理有過總結,他說:“《管子》樹義有五:曰政治,曰法令,曰經濟,曰軍事,曰文化。政治以《牧民》為主,……法令以《法禁》《任法》《明法》《重令》為主,……經濟以《國蓄》為主,……軍事以《參患》《七法》為主,……文化以《幼官》《水地》為主,……別有故事,在政治理論之外而兼有其內容,以《小匡》為主,……主要者不過六七篇,為全書之綱領,而《幼官》則為腦神經中樞,理論體系由是出焉。”[8]可見,《管子》中多為王道、霸道之學。如果我們將古代學術分為“內圣”與“外王”兩個方面的話,乾嘉學者對《管子》的研究恰好是二者巧妙的結合,表面是“內圣”,即“獨善其身”;內里是通過《管子》的內容來暗示學者們經世致用的企圖。因此,與其他子書的考據略有不同的是,《管子》一書內容的獨特性,決定乾嘉學者對其考據的獨特性,除了“證經”、“證史”、提高自身修養之外,還有學者們“兼濟天下”、建功立業思想的隱性表達。
[1]楊緒敏,安超.明清學風嬗變之大勢及對學術的影響[J].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3):117-121.
[2]劉仲華.清代諸子學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102.
[3]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M].趙剛,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142-143.
[4]顧炎武.日知錄[M].陳垣,校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1406.
[5]李杰.乾嘉學派與《四庫全書》[J].圖書情報工作,2004(4):45-49.
[7]汪高鑫.論“通經致用”的經學傳統[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3):96-102.
[8]黎翔鳳.管子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4:21.
Characterization of Guanz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ology in Qing Dynasty
Hao Jidong
(Collegeof LiberalArts,Shenyang Normal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110034)
The textology was an academic label in the Qing dynasty.Guanzi was a textbook which was put it practical use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By studying the documents of Guanzi throughout the Qing textology and combining with academic environment to analysis of the Qing dynasty,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som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gained by textology researchers.They were depoliticized by high-pressure cultural policy,but they tried to express the idea of practical utility;they proved Confucian classics with zhuzi and formed Liji;they also used themethods of textology research but localized by it.It’s possible to have percep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scholars’academic orientation by textology.
Qing dynasty;Guanzi;textology;characterization
I206.2
A
1674-5450(2016)04-0112-04
2016-04-26
郝繼東,男,內蒙古通遼人,沈陽師范大學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從事古代漢語與文獻研究。
【責任編輯:楊抱樸 責任校對:趙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