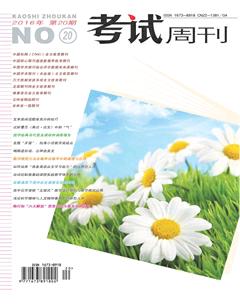發掘“矛盾”,找準小說教學突破點
林廷全
小說是對觀念矛盾的想象性解決,小說本身就是對矛盾的一種反應,它的獨特價值在于把握矛盾的方式。小說教學教什么?有沒有好的突破點?很多老師對文本缺乏深刻的解讀,常圍繞“人物、環境、情節”三要素展開分析,顯得單一而缺乏創新,常導致課堂教學效率低下。實際上,在一些小說文本中蘊含著極其豐富的教學資源,如看似明顯或隱藏的“矛盾”,或是作者的匠心獨運所在,或是點睛之筆,或是揭示小說主旨的關鍵點。教師若能深入發掘,根據文本特質深刻解讀,提煉有價值的教學點,則勢必能讓小說教學別樣精彩。
一、析文句矛盾,領悟小說主旨
小說文本的文句內部有時存在自相矛盾的現象,大多為蓄勢之筆,作者言在此而意在彼,多與主旨相關,蘊含極為豐富的內涵,需要教師引導學生深入發掘,解析、探究文字背后的真正用意,深刻領悟文章的主旨。教《孔乙己》,小說的結尾寫道:“我到現在終于沒看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大約”與“的確”兩詞從語義角度而言,自相矛盾,如果教師能夠關注并發掘這一矛盾,緊扣“大約”、“的確”兩個詞進行探究,就可以從人物性格和社會環境兩個方面深刻地理解這篇小說。學生自然聯系到文本中孔乙己的遭遇、性格(懶惰、迂腐等)、言行等斷定他悲慘的結局。然而,為什么又說“大約”死了呢?一個人的最終命運除個人因素外,也離不開當時的社會背景,在大家的眼中,孔乙己充其量只是大家取樂的對象,“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么過”。像他這樣迂腐、寒酸的讀書人,有誰去關心?他到底死了沒有?沒人可以給出確切的答案。因此可以看出:孔乙己的悲劇同時是那個時代的悲哀,作者劍指封建科舉制度而發出強烈的抨擊之聲。深入解析文句矛盾的同時,文章的主旨豁然開朗,強似教師不厭其煩地講授。在魯迅先生的另一篇小說《故鄉》中也有這樣一句話:“地上本沒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文句矛盾同樣值得探究。
二、解“反語”,前后貫通理思路
在一些小說文本中,存在“反語”,即文本語句字面所表述的含義并不是作者想要表達的真實意圖,往往是“反其意而言之”。為什么要以“反語”的形式出現呢?仔細揣摩、探究這些言說與實意相悖的語句,聯系上下文、寫作背景等,對理清小說的情節線索、了解作者真實的寫作目的,有時會達到“牽一發以動全身”的效果。教學小說《社戲》時,引導學生揣摩最后一段“真的,一直到現在,我實在再沒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戲了”。讓學生結合文本談談“那夜的豆真得好吃嗎?那夜的戲真得好看嗎?”,通過閱讀,學生發現,“我”愛看的鐵頭老生并不翻筋斗,最不想看的老旦卻長時間地坐在交椅上不肯下臺,踱來踱去、磨磨蹭蹭地在唱難聽的戲,可見戲并不好看。同樣豆并不好吃。這里存在顯而易見的矛盾,反話正說,教師引導學生深入探究,小說中的“夏夜行船、船上看戲、月夜歸航”的情節逐步清晰,發現“我”更關注的是在看戲、吃豆途中伙伴們在一起的那種無憂無慮、無拘無束的童年生活,那里人們的純真質樸的情懷,向我們展示了一幅人性美、人情美的優美畫卷,讀之令人心有所往。
三、看內心矛盾,品嘗人生百味
在小說文本中,人物的內心矛盾極常見。由于職業不同、階層不同、社會地位懸殊,人們的心態往往不同,這需要教師在引導學生發掘文本人物內心矛盾時,善于讓學生變換角色,換位思考,站在小說人物的立場考慮問題,與小說文本人物心相通、意相會,感同身受,才能深刻感受其內心的律動,品嘗大千世界的人生百味,從而豐富學生的情感體驗。教學小說《臺階》,我們發現文章中的父親在理想與現實中徘徊、掙扎,生存狀況與理想追求存在巨大反差。《臺階》中的父親“老實厚道低眉順眼了一輩子”,“沒有人說過他有地位”,“也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有地位”,然而父親總覺得自家的“臺階低”,總想方設法提高家庭的“地位”,而在歷盡千辛萬苦之后,新屋終于建成了,“父親從老屋里拿出四顆大鞭炮時,父親的兩手沒處放似的,抄著不是,貼在胯骨上也不是。仿佛許多目光在看著他……父親沒有神采飛揚,而是露出尷尬的笑。他又從開始的坐在新屋的最高臺階上,感到渾身的不自在,一步一步往低處坐,最終干脆就坐在門檻上去”。教師引導學生通過深入發掘父親的內心矛盾,想得到別人的尊重、刮目相看,而又極度不自信,讓學生結合自己父親或其他親人的經歷,或閱讀類似文章的體驗感悟,體會到以父親為典型的幾千年來農民艱難的命運與不屈的追求,在超越與困惑、迷茫之間徘徊。小說《我的叔叔于勒》,當“我”面對極度窘迫、狼狽不堪的叔叔時,想認而又不得的內心矛盾,教師可透過解讀這些矛盾,帶領學生體會當時世態炎涼、世風日下的社會現實。
四、品“情景矛盾”,披文入情,發掘蘊含情愫
“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一些優秀的小說作品,飽蘸作家的思想感情,甚至凝聚心血和生命。語文教師首先要做到披文入情,認真理解語言文字表達的情和意,挖掘作品思想內涵,聯系生活經驗,啟發學生步入至真至美的情感世界,使之受到熏陶感染。(于漪:《語文教育與人的完整性建構》)在一些小說作品中,有時存在景物與情感的極不協調,語文教師若能像于漪所言,披文入情,引導學生探究小說中的情景矛盾,深入發掘其間蘊含的情愫,從而提煉出好的教學點。教學《最后一課》,引導學生抓住課文幾處的景物描寫。開頭部分寫道:“畫眉在樹林邊宛轉地唱歌;鋸木廠后邊草地上,普魯士兵正在操練。”作為戰敗國的法國被迫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給普魯士,普魯士士兵占領了這兩個省,并且不許他們學習祖國的語言,飽受失去家園之痛苦的法國人民心情可想而知。然而,小說卻寫畫眉在宛轉地唱歌,小鳥歌唱本是大悅人心之景,這里情與景顯得極不協調。教師若能引導學生挖掘該處的矛盾,聯系文中的小弗郎士前后對比,這里是以他的眼光來寫,描寫他逃學到野外所見到的情景,也許他對亡國并不知情,覺得在外游玩是多么令人開心、興奮的事情,后文當他在課堂上所見到的種種,看到鎮上那些前來聽課的鄉親們時,悲痛欲絕的韓麥爾先生,對比自己,令他后悔莫及,深感慚愧。小說教學中品味“情景矛盾”,容易激發學生情感,深刻發掘蘊含于文本的情愫。
五、以矛盾制造矛盾,思維碰撞引共鳴
“閱讀是學生個性化的行為,不應以教師的分析來代替學生的閱讀實踐”。只有學生親身體驗的才能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在小說教學中,教師可以利用文本中的已知“矛盾”,制造新的“矛盾”,讓學生參與討論、辯論,使他們的思維得到碰撞引發共鳴。教學《羚羊木雕》,顯而易見,“我”圍繞羚羊木雕該不該要回,陷入兩難境地,心中十分矛盾。這樣的經歷也許是每個學生成長中都有可能經歷的尷尬,容易產生共鳴。因此,教師可以此為突破口提煉教學點,要求學生圍繞“是否應該要回羚羊木雕”展開討論,學生中必定有不同的觀點,繼而以此為主題正反兩方面展開辯論,正方認為應該回,畢竟那是父親從非洲帶回來給女兒極貴重的心愛之物,豈可隨便贈送給他人。反方認為人不可無信,即便是再珍貴的東西已經贈送給朋友,怎么可以又重新要回來呢?更何況朋友萬芳對我十分仗義。“水本無華,相蕩而成漣漪;石本無火,相擊而發靈光”,教師巧用文中“我”的矛盾制造學生間觀點的矛盾,讓學生的思維得到碰撞,喚起學生的閱讀體驗,切己體察,與文本對話,引發共鳴。學生在唇槍舌劍中明辨是非,體會到人世間美好的友誼應該珍惜,父母應多理解孩子,多關注他們的內心世界,尊重他們的人格。
“教什么比怎么教更重要”,發掘“矛盾”,是確立小說教學內容的有效方式,是涉及“教什么”的問題,它需要語文教師有敏銳的洞察力,善于發掘,啟發學生探究蘊含于文本中的矛盾,才能找準教學突破點。這樣的小說課堂教學必定富有情趣、生動活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