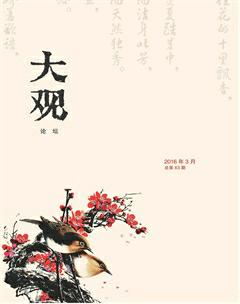藝術是歷史的救生圈?
摘要:揚·馬特爾的《碧翠絲與維吉爾》描述了作家亨利經歷新作夭折后搬到新城市并與標本師亨利一同完成新劇本的故事,通過動物視角指控了納粹大屠殺事件的滔天罪行。馬特爾在作品中借由元小說特征中創作與批評交融的書寫,對歷史編纂提出了藝術化的觀點。本文主要通過納粹大屠殺事件的敘述、處理和后人對待的角度,揭示其文學創作中的史學見地。
關鍵詞:碧翠絲與維吉爾;揚·馬特爾;后現代主義;歷史編纂元小說
引言
加拿大著名文學理論家林達·哈琴(Linda Hutcheon)在《一種后現代主義詩學》一書中首次提出了“歷史編纂元小說”的概念。其特點是“在理論上對歷史與小說均屬人為建構物具有清醒的自我認識,從而為它對過去的形式和內容進行重新思考和再加工奠定了基礎。”《碧翠絲與維吉爾》正是通過呈現四部看似各自獨立實際上卻隱含牽連的子文本,最后將其一并融為全書完整的文本,雖然各文本形式和內容不盡相同,但都是以對異類的殘殺迫害為主題。阿多諾在1955年出版的文集《棱鏡》中寫道:“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 面對人類歷史上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歷史人類又該如何記錄?馬特爾讓作家亨利經歷了挫敗和陰森恐怖的創作活動,借其心路歷程對史上殺戮行徑能否真實反映提出質疑,通過解構和重構歷史的書寫來對歷史敘事態度和形式進行新思考,并對藝術化呈現的大屠殺事件進行了審視和加工。
一、敘事:歷史的虛構與文學的真實
后現代主義理論認為,真正公正的歷史學家是不存在的,而且“歷史的寫作總是帶有為自己立傳的性質”。也就是說,歷史其實也是一種小說文本,歷史編纂元小說的產生正是“利用了歷史記錄的真實與否尚待考證”這一漏洞進行文學上的補充。對于歷史記錄的虛構問題,馬特爾在書中給出了自己的答案:“藝術作品之所以管用,不是因為它是真實存在的,而是因為它是真真切切的。”就此創新式地完成了以往對大屠殺文學常規記錄的突圍。
馬特爾借由作家亨利之口傳達了自己對歷史編纂的獨到見解:“我們不僅要了解歷史,同時要理解藝術”,這也就是翻轉書的構思原型。因此無論是全書五個文本中的哪一個,都“講的是對大屠殺的呈現,講的是新的講故事的方式”。馬特爾將歷史和小說兩個看似客觀性不同的文本融合在一起,揭示出標榜真實的歷史所固有的不確定性及歷史話語內在的虛構性,因此他大膽地用脫節于納粹大屠殺慘案的發生地,另辟蹊徑地選取標本店作為故事縱橫發生的歸屬地,用子文本的時空穿梭展現了宏大的敘事空間大大充實了本書訴諸筆端所記錄的史料,用兩個動物的經歷涵括了人類遭受的苦難并極力放大它們延宕的無意義對話,展現厄運來臨時的無助無知和無力。“后現代主義文學的個案研究若能以共時的人文——歷史框架作為參照系則有希望減少以偏概全、故弄玄虛的弊端。”
但歷史編纂脫離事實發生情境的程度性對于一個有企圖心的作家來說并不容易拿捏。元小說的積極意義在于,它使人們重新審視自己的現實觀。但“在強調現實的虛構性時走向了極端,容易步入虛無主義的歧途”。與《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不同的是,本書中代替人類遭受苦難的動物,引發了批評家們不尊重真實受難者的非議,他們認為真真切切受過折磨的人類就此消解為動物未免形同兒戲。小說中關于納粹大屠殺事件的真實描寫過少,從“諾沃立普基大街68號”這類只言片語中,構建起的只是屠殺事件的零星碎片,從碧翠絲與維吉爾慘遭荼毒的片段描寫,讀者也只能短暫地激起對非人道行為的戰栗。藝術和歷史之間共同的部分并非諸如物種、國籍這種客觀的成分,而是當事人所感受和經歷的事件“本質”。但因人而異的藝術審美,使得讀者對該技巧運用精巧與否的評價毀譽參半。
二、當事:游戲化的殘忍
如果將納粹大屠殺事件僅僅格式化為“瘋狂邪惡的劊子手對善良無辜的猶太人所犯下的一次沒有人性的可怕罪行”,那么他們的殘忍瘋狂與劫難的慘痛應該深為人知,隨著戰爭的結束、審判的塵埃落定,受譴責的與受傷害的也行將過去,這樣的傷疤放到今日依舊來緬懷又有什么意義呢?事實上,大屠殺產生的可能性依舊潛伏在各個角落。《碧翠絲與維吉爾》便對讀者提出來終極審判:我做過什么?或者如果當時我在現場,我會做什么?
在對歷史細節的處理上,本小說采用了游戲化的處理:“許多元小說都把人如何被‘游戲規則——即社會制度、社會習俗和慣例等——所操縱當作了題材。”馬特爾將讀者直接從平靜的閱讀中剝離出來,拋擲到不安、痛苦的倫理兩難的拷問中,在蠻橫、粗暴的條件中,逼迫讀者做出自己不愿面對的無解答案。細讀十三個游戲會發現,它們都是在模擬猶太人大浩劫中對人類勇氣與倫理的十三種極限考驗。比如游戲四中,荷槍實彈的警衛寓意的是野蠻的控制,用殺戮的隨意性和生殺予奪的所有權威脅“你”做任何他叫你做的。警衛不過是浩大體制中的一顆螺絲釘,他竟可以依仗手中的武器為虎作倀,凌辱同樣生而為人的人類的尊嚴和體面。諷刺的是,游戲中“你”聽不懂他在說什么的時候你會做什么,這個問題已經隱含了人之地位不對等的恐懼在里面,當信仰與道德分文不值的時候,當憤怒無法控訴的時候,人類隱忍保全自己茍且的存在還有意義嗎?馬特爾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沒有寫出來警衛的指令,但讀者都能參透最后的結局,無言勝有言的隱秘書寫越發讓人驚恐。人們就會進入到第十三種游戲,這是一張空白頁,是對這一“集體暴行”的失語狀態。馬特爾將讀者置于終將死亡的命題中,對于怎樣等待暴斃的過程懸置住人們思考。除了“你”會如何選擇之外,馬特爾設置的“警衛”身份也意味深長:他不過是一個平凡的干事,確是千千萬萬罪惡的幫兇。如果片面化地指摘首領的狂暴、卡通化地接受劫難發生后的道歉,類似的人間慘案依舊會發生,因為事件發生的土壤沒有變化,每一個體制內的人都應該向褻瀆生命認罪。
這十三個游戲依據納粹屠殺發生的線索,以平凡人在一場聲勢浩蕩的殺戮中如何自保、如何處事、如何死亡、如何指控、如何遺忘、如何記憶為主線,提出生存與生命、道德與倫理、隱忍與尊嚴、控訴與無力、自嘲與記憶、忘卻與反省等問題,展現了諸多隱而不宣的微妙心理,如:加害人在殘害過程中對罪惡感的缺失、殘害手段極盡殘酷卻缺乏目的性、被害人心中難以言喻又無法抹卻的深遠恐懼、被害人身處恐懼中卻不得不繼續生存所展現的虛假歡樂、幸存者在事件過后無法言說該事件的失語沉默。endprint
三、處事:集體沉默的失語癥
凱爾泰斯·伊姆雷1998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演講時說:“當奧斯維辛從幸存者們那隨著年歲一同羸弱的手中緩緩滑落的時候,奧斯維辛將會成為誰的呢?”正如第十一號和第十二號游戲鋪陳的終極拷問,經歷過希特勒暴行的人們應該如何面對過去的回憶?沒有親歷折磨的的后人又應該如何記憶?對于后一個問題,《碧翠絲與維吉爾》這部歷史編纂元小說有意將歷史和虛構的連接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我們是如何了解過去的?我們現在對過去可能了解些什么?
馬特爾在小說開始的部分,借作家亨利的失落道出了振聾發聵的問題:“公園里平和的明媚午后。在這里談大屠殺有什么必要嗎?……都這個年代了,干嘛還要寫一本關于大屠殺的小說?”當一樁人類歷史上慘絕人寰的悲劇塵埃落定,難道后人不應該用各種媒介去記錄它以表示對生命的敬意嗎?標本師這個前納粹分子將劇本名字取為《一件20世紀的襯衫》確有隱喻,他將整個世界化為一個全然的富有深意空間:動物們是受害的無辜者,是制度下茫然無知的犧牲品;他對這些消失的物種深感同情,但畢其一生將它們的身體肢解;作家亨利在書寫有關納粹大屠殺的故事,卻沒辦法真誠地面對象征著殺戮原型標本師的殘暴與血腥;作家亨利在創作上的介入,似乎意味著“眾多心甘情愿的幫兇”。在小說最后,標本師在大火中自焚,也帶走了他不堪觸碰的印記。但是毒瘤依舊存在,它依舊是光鮮亮麗的現代文明肌理上不可抹去的傷疤,所以會有《碧翠絲與維吉爾》這部小說,也所有會有“翻轉書”這樣不落窠臼的念頭。集體沉默的漠視是繼殺戮后再次對逝者的褻瀆,是納粹陰魂的再次勝利!
海登·懷特強調過:“當人們忘記了‘歷史——既包括事件又包括對事件的描述的‘歷史并不只是發生過、而且制作出的,那么歷史的意識也就完結了。”馬特爾并沒有忽視記錄的問題,他更進一步地反彈琵琶,不落入陳詞陳語的窠臼,對用語表意的可能性提出質疑。劇本中形容梨需要旁征蘋果、香蕉、葫蘆等名詞,碧翠絲也直接跳出來說“這些術語有什么意義?而且它們真的重要嗎?”歷史學家凱西·戴維斯說過,解構是語言的最終去等級化,因為解構不相信文本和話語能夠決定自己的表面意義。這種方法否認文本表面的統一,它揭示了文本如何通過自相矛盾、含混不明以及對相反意見的壓制而推翻了自己所發出的信息,并以此說明文本的異質性和內部的緊張關系。
語言說明了一切,但它總是在說謊。對于同一事物人們的認識可能存有偏差,始終用另一個事物來說明這一個事物是有危險的,這個危險恰恰是普遍存在的語言困境。結構主義語言學認為,語言是一種代碼和信息,這種代碼和信息具有意指性。馬特爾在大篇幅上索性拋棄了語言的正面描述,靠一種“非語言表達”試圖超越語言,他杜絕對客體的感知,旁敲側擊地建構親歷者的心態和事件發生時的恐怖陰影,如用諸多生造詞來描述“恐懼”這個感受,給讀者帶來了藝術上的體驗而非歷史性的穿越。
四、結語
揚·馬特爾認為歷史如若無法轉為藝術,最終對所有人而言都會是死的,除卻歷史學家。歷史有著自己的內在邏輯,而在后現代的今天馬特爾更傾向于從文本的背后去考察,經由對歷史的“重訪”(revisiting)和“再加工”(reworking),探索向歷史汲取創作源泉并貫以藝術鑒賞的文學新形式。通過把歷史中所有的敘述模式都降低為它們的表現形式,從而消解了深埋其間的真理和權威性,用藝術化的手法喚醒20世紀的罪惡和良知,他在歷史編纂元小說書寫上的嘗試和試水為世界文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嘗試和貢獻。
除此之外,小說中還有諸多精彩的地方,比如貫穿始終的互文和借用讓文本的理解充滿了文學上的厚重感。短短的篇幅包含了觸目驚心的場面、毛骨悚然的恐懼、別開生面的劇本、望而生畏的真相等等,著實為一篇實驗性很強的精悍小說,也給我們審視“翻轉書”式虛實相間的歷史帶來了新的觀看視角和啟發。
【參考文獻】
[1]劉璐.后現代主義歷史編纂元小說中的史學性敘事[J].貴州大學學報.2011, 29(6):85-88
[2]楊春. 歷史編纂元小說——后現代主義小說新方向?[J].山西師大學報. 2006,33(3):55-60
[3]劉璐.歷史的解構與重構——后現代主義歷史編纂元小說研究[D].天津:南開大學,2012
[4]黃文凱,王曉燕.論楊馬特爾的大屠殺文學想象[J]中國圖書評論.2015(03):97-103
[5]王麗.淺析揚·馬特爾小說《標本師的魔幻劇本》敘事框架[J].長春教育學院學報.2013,29(22)
[6]殷企平.元小說的背景和特征[J].杭州大學學報.1995(03)
[7]袁洪庚.繁花似錦的奇詭世界——簡評首版《諾頓美國后現代小說選集》[J] .譯林出版社,2003
[8] Linda Hutcheon.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History,Theory,Fiction[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88.
[9] Yann Martel.Beatrice and Virgil:A Novel.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New York,2010
[10] Geary D.Labour History,the“Linguistic Turn”and Post-modernism [J].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2000
[11] Cathy Davidson.Revolution and the word:The Rise of the Novel in America[M].New York,Oxford U.P.1986
[12]羅蘭·巴特.符號學原理[M].三聯書店,1998
作者簡介:張穎(1995—),女,漢族,浙江金華,本科在讀,杭州師范大學。研究方向:戰后英美文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