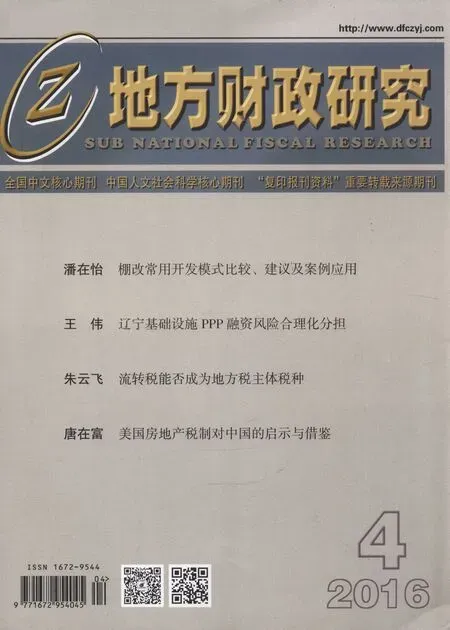財政相對收支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
——基于縱向財政不平衡和地方財政支出規模的視角
顧程亮 李宗堯 成祥東
(中共江蘇省委黨校,南京210009)
財政相對收支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
——基于縱向財政不平衡和地方財政支出規模的視角
顧程亮 李宗堯 成祥東
(中共江蘇省委黨校,南京210009)
根據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業聯合會(WBCSD)定義的生態效率公式,在量化環境效率和資源效率的基礎上降維合成生態效率綜合指標,并進一步從縱向財政不平衡和地方財政支出規模的視角研究財政相對收支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結論如下:總體而言,縱向財政不平衡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表現為即期作用,地方財政支出規模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表現為滯后作用,一般滯后3年以上;基礎設施將強化地方財政支出規模的促進作用,弱化縱向財政不平衡的抑制作用。分地區比較,發達地區縱向財政不平衡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不顯著,地方財政支出規模促進區域生態效率的發展,欠發達地區縱向財政不平衡和地方財政支出規模均抑制區域生態效率的發展。
區域生態效率 縱向財政不平衡 財政支出規模 IV估計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黨的十八大報告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布局,生態文明建設由此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進一步提出將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的戰略位置,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可持續發展將成為我國未來區域發展的主旋律。而現實中,“三高一低”①“三高一低”就是指“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經濟增長方式。的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部分區域甚至超出環境所能容納的極限,這種發展方式已難以為繼,因此,探索綠色低碳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新路刻不容緩。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充分發揮環境保護主陣地的作用。生態環境保護由于存在外部性屬于公共產品或服務的范疇,需要借助外部力量使之資源配置優化。當下我國包括生態環境服務在內的公共服務是以政府供給為主,相關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由于受當地選民和管轄區政績的直接激勵,在該領域的供給效率優于中央政府(Inman & Rubinfeld,1997;Besley & Coate (2003)、Bordigon等,2002)[1-2]。 1994年我國進行財政體制改革,實行分稅制,部分財權下放以期提高公共服務績效和實現基本服務均等化,但實際效果欠佳。剖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地方財政收入來源的縮減,加之其支出責任的相對擴大(陳碩,2010)[3],地方政府的縱向財政不平衡問題愈發嚴重(江慶,2006;江慶,2007)[4-5];另一方面由于轉移支付制度的扭曲,土地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地方財政透支現象明顯(劉玲玲,馮懿男,2010)[6],地方財政支出規模及其差異性均呈上升趨勢(郭慶旺,賈俊雪,2010)[7]。基于目前的政府考核機制,在縱向財政不平衡加劇和地方財政支出規模擴大的雙重壓力下,地方政府往往會通過壓縮科教文衛等基本公共“軟”服務來提高基本建設支出等“硬”產品或服務的比重(傅勇,張晏,2007;龔鋒,盧洪友,2009)[8-9]。
區域生態效率是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基礎,是衡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水平的有效工具。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即為追求一種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其內涵強調的是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保護生態環境。而筆者通過查閱資料發現剖析地方財政收支兩個維度對區域生態效率影響的文獻并不充分,其對地方財政的研究往往以理論分析為主。
鑒于此,本文把地方財政分為相對收入能力和相對支出能力兩個部分,采用縱向財政不平衡來衡量公共財政收入的相對能力,采用地方財政支出規模來衡量公共財政支出的相對能力,通過全國30個省市(由于西藏2007年之前的電力數據未統計,故剔除)2001年-2013年的面板數據分析縱向財政不平衡、地方財政支出規模等因素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并針對實證結果提出相應政策,以期對政府生態環境公共服務供給有所啟發。
二、生態效率與財政相對收支的相關定義及其關系
(一)生態效率的定義及數據分析
自1990年Schaltegger和Sturm[10]首次提出生態效率概念以來,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業聯合會(WBCSD)[11]、經合組織(OECD)[12]、歐洲環境署(EEA)[13]和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D)等分別對生態效率的內涵進行不同層面的補充,其應用范圍也得到拓寬。雖然生態效率的定義與解釋尚未形成共識,但其本質沒改變,即用最小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換取最大的社會福利,是一種投入與產出的比值。國內比較主流的做法是在建立生態效率水平指標體系的基礎上,通過數學模型和軟件進行分析[14]。其中,由WBCSD提出的生態效率比值公式最為經典:

根據對資源消耗與環境影響的因素分析及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參考黃和平[15]對于生態效率的處理方法,將公式(1)中分子用人均實際GDP表示,代表社會產品或服務的價值量,資源消耗則用電力消耗、用水、能源消耗來表示,環境影響則用COD排放、SO2排放、固體廢棄物排放來表示,在此基礎上分別得出研究地區的以上6種資源環境效率,并進一步通過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推算其生態效率。
按照前述對資源效率和環境效率的定義,分別計算各項指標增長速度,具體按照公式(2)和公式(3)依次推算出資源效率中的電力消耗資源、水資源消耗和能源消耗的效率及環境效率中的COD排放、SO2排放和固體廢物排放的效率。

對上述求得的資源效率和環境效率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全國30個省市2001年-2013年的生態效率綜合指標。由于按照生態效率概念模型的要求,生態效率的取值應在[0,1]之間,因此應對其進行標準化。本文選用離差標準化方法,其公式如下:

其中,Z為標準化后的值,Xi為歷年各省市生態效率值。
圖1顯示了2001年-2013年期間中國30個省市生態效率的年均值。若以0.75與0.70為劃分點可以將30個省市劃分為三個梯度,第一梯度(0.75以上)有吉渝桂遼魯川貴黑豫鄂10省市,第二梯度(0.70-0.75)有蘇皖陜京甘蒙贛湘津浙滬粵冀寧閩15省市,第三梯度(0.70以下)有晉云瓊青新5省市。

圖1 2001年-2013年中國各省生態效率年均值
(二)縱向財政不平衡的定義及數據分析
本文采用縱向財政不平衡度量地方政府財政相對收入的能力。當下對縱向財政不平衡的定義主要有以下3類:
Roadway和Tremblay(2006)[16]從財政轉移支付的角度定義縱向財政不平衡,他們把縱向財政不平衡看作是一種聯邦稅收水平,在這種稅收水平下聯邦政府的轉移支付數額少于相對其支出責任數額。從這個意義上說,縱向財政不平衡就是不同級別政府對轉移支付的需求,縱向財政不平衡出現在地方政府本級收入與支出之間的不匹配在轉移支付或其他法定途徑中并未得到抵銷的狀況下(Shah,2006)。[17]Breton (1998)[18]從本級政府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之間不匹配的角度定義縱向財政不平衡,他認為資金在地方政府之間的循環流動導致縱向不平衡的出現。并且,地方政府的融資水平和財政支出規模也與縱向財政不平衡息息相關。Collins(2002)[19]認為縱向財政不平衡代表某一級別政府自身財政收入以及依靠本級政府資源進行融資的水平與按照法定職責進行公共財政支出之間的差距。Matier C、L Wu & H Jackson(2001)[20]從不同級別政府權力不對等的角度定義縱向財政不平衡,他們認為政府之間的權力不對等直接導致縱向財政不平衡的出現。具體地說,當某一級別政府有權利要求其它級別政府通過增加稅收或減少財政支出來滿足其減稅或增加公共支出的目的時,就會產生縱向財政不平衡。實質上,這就是各級政府財權與事權的不匹配,中央政府具有超出其事權的財權,而地方政府具有超出其財權的事權(Hallwood,MacDonald,2005)。[21]
國內學者大多根據Hunter提出的方法界定并量化縱向財政不平衡(江慶,2006;江慶,2007)。[4-5]Hunter提出VFI=1-G/E,其中VFI表示縱向財政不平衡,G表示來自中央的地方財政收入,E表示地方政府的總支出。本文借鑒Hunter的方法用地方政府公共財政收入與公共財政支出之間不匹配的部分占本級政府公共財政支出的比例來實現對縱向財政不平衡度量。
國家政府基于提高地方基本公共服務效率的考慮,在財稅改革中下放部分地方財權。但由于財政分權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導致國內產生嚴重的縱向財政不平衡問題。由圖2可知,縱向財政不平衡值在各個省中差異明顯,且分布較廣。樣本的平均VFI為0.484,最小值是北京的0.130,最大值是青海的0.816。VFI的不同反映出各個地區政府相對財政收入能力的不同,一般而言,經濟欠發達地區的VFI往往偏高,因為該類地區經濟不發達,當地政府的財政稅收不足以支撐本級政府的支出責任,往往依靠轉移支付進行彌補。
(三)財政支出規模定義及數據分析
本文采用地方財政支出規模指標衡量政府的財政相對支出。學界對地方財政支出規模測算通常有2種方式。第一種為絕對指標,一般采用考察期內地方政府的財政安排支出的數額表示。第二種為相對指標,一般采用地方財政支出占GDP(GNP)的比重來表示。本文考慮數據獲取與處理的方便,借鑒龔鋒(2010)[22]等所構建的財政分權多維指標體系,采用地方財政支出占全國財政支出的比重來衡量地方財政支出規模,進而分析在財政分權下地方政府財政支出規模與區域生態效率水平的關系。
由圖3可知,財政支出規模值在各個省中的表現與縱向財政不平衡一樣都差異明顯,且分布較廣。樣本的平均FD為2.500,最小值是海南的0.525,最大值是廣東的6.331。FD的不同反映出了各個地區政府相對財政支出能力不同,一般而言,地區行政面積越大其財政支出占全國財政支出的比例越高,即FD值越大。
(四)財政相對收支與區域生態效率的關系
根據30個省市2001年-2013年的區域生態效率值、縱向財政不平衡值和地方財政支出規模值計算13年間每年的各省整體平均值,以區域生態效率和縱向財政不平衡值為主縱坐標,以地方財政支出值為次縱坐標,以時間為橫坐標觀察財政相對收支與區域生態效率的關系。由圖4可知,除了2009年-2011年期間的全球金融危機外,總體上,區域生態效率值在上升;地方財政支出規模在2011年增長放緩,但繼續保持向上趨勢;縱向財政不平衡在2007年出現了一個高峰值,總體上呈下降趨勢。據此猜想地方財政支出規模與區域生態效率之間有著某種正相關關系,而縱向財政不平衡與區域生態效率之間有著某種負相關關系。

圖2 2001年-2013年縱向財政不平衡各省年均值

圖3 2001年-2013年財政支出規模各省年均值
(五)其它變量的設置與假設總結
地方財政支出規模和縱向財政不平衡對地方經濟生態效率的影響程度很可能與該地區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有關。本文引入公鐵路密度(公路里程與鐵路里程的和與該行政區域土地面積的比值)來衡量該地區的基礎設施情況。欠發達地區往往傾向把財政用于提供這種硬公共產品的供給,擠占對生態環境軟公共產品的財政投入。在這種情況下,若該地區擁有更多的財政支出自主權,在中短期來看必將降低經濟的生態效率,并且往往這種地區的財政收入會偏低,縱向財政不平衡程度較高。

圖4 2001年-2013年財政相對收支與區域生態效率的關系圖
依據已有的研究[23-24]和上述分析,本文的3個假設如下:
H1:提高地方政府相對收入能力,即降低縱向財政不平衡可以提高該地區的生態效率水平。
H2:地方財政支出規模的提高能夠提高生態效率的水平。
H3:一個地區的基礎設施越差,將強化縱向財政不平衡對生態效率的作用,弱化地方財政支出規模對生態效率的作用。
三、實證分析
(一)模型設定及指標選取
為研究縱向財政不平衡、地方財政支出規模等作用因子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本文將基本模型設定為:

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被解釋變量Ecoeit為某省份某年的生態效率,其具體數值由文章第二部分得到。本文在上述模型中引入被解釋變量滯后3期作為自身的解釋變量,以此考察初始的生態效率對未來的影響。
解釋變量VFIit為某省份某年的縱向財政不平衡水平,本文利用VFIit系數α來證明假設H1。VFIit系數α衡量了在控制其他變量的前提下,VFI對生態效率水平的影響,預計α值是負數。同時為驗證VFI對Eco-e是否存在理論上的最值效用而引入一個VFIit的平方項,若VFI平方項的系數為負,且通過檢驗,則為倒“U”型,存在“最大值”;若為正,則為“U”型,存在“最小值”。并且聯系系數α可進一步判斷當前其處于“U”型曲線的什么階段。
解釋變量FDit為某省份某年的地方財政支出規模。通過FDit系數β來檢驗假設H2。地方財政支出規模系數β度量了在VFI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政府支出規模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預計估計出來的β為正。同時,本文引入財政支出規模的滯后3期來考察其是否對地方生態效率存在長期影響。
Xit表示控制變量。根據Turnbull和Midas(1995)的研究,類似生態保護等基礎公共服務的效率與人口規模、居民的收入水平等宏觀因素緊密結合。因此,本文采用對數化人均GDP(ln gdp)來控制居民收入水平對生態效率的影響;采用人口密度(pd)來控制人口規模對生態效率的影響;采用人均財政收入的對數形式(ln afr)控制地方財政收入變化。εit是隨機誤差項。此外,模型中還包括一個虛擬變量——基礎設施(Dh&r)。這里的基礎設施度量指標是該地區公路和鐵路的密度,當一個地區公鐵路密度達到或超過0.825(該值上下的省份數量大體相當)時為1,沒有達到0.825則為0。由上述的猜想可知,縱向財政不平衡和財政支出規模的作用強度可能與該地區的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相關。為檢驗假設3,本文增添基礎設施虛擬變量與縱向財政不平衡、財政支出規模的交互項z1,z2,預估這兩個系數υ1υ2為一正一負。
綜上所述,引入新變量后的總模型為:

本文所有的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1-2014)、《中國財政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1-2014)和部分省市統計年鑒。
(二)模型結論分析
通過STATA軟件得出計量結論。運用Hausman檢驗對表1中的3個模型分別進行測試,均拒絕原假設,故采用固態效應模型估計。3個模型的具體回歸結果詳見表1。模型(1)增添了VFI的平方項,模型(2)增加了縱向財政不平衡、地方財政支出規模與基礎設施虛擬變量的交互項,模型(3)則是考慮解釋變量VFI的內生性而使用工具變量的IV估計模型。其中,模型(3)由于使用了工具變量除了一般意義上的R2和F統計量外,還需對工具變量進行過度識別檢驗、識別不足檢驗和工具變量弱相關檢驗。Kleibergen-Paap rk LM統計值為22.246,其自由度為6的卡方分布P值為0.0001,高度拒絕原假設,故工具變量不存在識別不足問題;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統計值為3.417,小于5%-30%水平下的臨界值,故工具變量存在較強的相關性;Hansen J統計值為20.393,其自由度為5的卡方分布P值是0.0111,無法拒絕原假設,故工具變量的選擇較為合理,不存在過度識別問題。因此,模型均通過計量的各個檢驗,具有可信度。
由表1可知,區域生態效率具有滯后效應,即區域前期的生態效率會影響本期生態效率水平,且前期生態效率與本期生態效率成負相關。這與一般認知似乎相悖,主要因為我國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的傳統生產模式并未得到徹底轉變,后發地區轉型發展難度大,更多的以被動接受傳統產業轉移實現地區發展。資源豐富,環境良好的地區,當地政府為求GDP考核,很少去考慮產業發展的生態效率。值得注意的是,生態效率的影響具有長期性。因為從表1可以看到,生態效率滯后1期對當期生態效率的影響不顯著,而滯后2期和3期的生態效率系數對當期生態效率有顯著負作用,在模型3中滯后2期和3期都在1%水平下顯著。
由表1模型(3)可知,假設H1成立,縱向財政不平衡與生態效率成顯著負相關。即縱向財政不平衡水平越高,該地區的生態效率水平越低。這主要因為縱向財政不平衡高,說明該地區政府公共財政收入相對于公共支出缺口大,為彌補缺口做出政績,該地方政府更傾向于把資金投入到能短期快速得到財政收入的公共基礎項目建設或產業布局上,忽略地區發展的生態效率因素。如此循環往復,加劇兩者之間的負相關程度。另外,縱向財政不平衡的平方項與生態效率成正相關,結合縱向財政不平衡與生態效率負相關,由圖5可知,我國生態效率與縱向財政不平衡的關系狀態處于“U”型曲線的A區,在目前的經濟發展模式下,隨著地方政府縱向財政不平衡水平的加深,生態效率水平會越來越低,但下降的速度則會放緩。這成為國家倡導創新發展,注重集約生產,綠色消費的考慮依據。
當期、滯后1期和滯后2期的地方財政支出規模對生態效率的影響不顯著,而滯后3期的地方財政支出規模與生態效率成正相關關系,假設H2部分成立。表面上來,這個結果很難理解,實際上這是由我國政府機構的選舉架構與政績考核所導致的。我國政府每5年一屆,在5年任期內施政風格往往趨于一致,而下一屆的施政風格又會根據上一屆地方的實際狀況而變化,故地方財政支出規模的影響具有較長的滯后性。當一個地區的財政支出自由度變大時,它會更有主人翁精神,更傾向于全局的、長期的計劃,在地方引進產業,社會管理方面都會有所選擇,有助于當地生態效率的提高,故地方財政支出規模滯后3期的系數為正。
人均財政收入水平與區域生態效率成負相關。人均財政收入高,意味著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高,但由于我國政府根深蒂固的追求“硬政績”的政府慣性,加大對硬公共基礎服務的供給和對短期較快能產生經濟效應的企業的引進,降低了該地區的生態效率水平。人均GDP與區域生態效率成正相關。根據實際情況判斷,人均GDP高的地區往往是經濟較為發達的省市,而經濟較為發達的省市的發展管理理念較為先進。開發區從以前的“招商引資”到現在的“招商選資”就是明顯的例子,故人均GDP的系數為正。人口規模與區域生態效率成負相關,而其滯后1期和2期對生態效率無顯著影響。因為當期的人口規模影響當期的生態效率,人口擁擠的地區顯然環境負荷較重,生態效率提高難度增大,故其系數為負。

表1 區域生態效率水平和VFI、FD的回歸結果
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與縱向財政不平衡交互項的滯后2期與生態效率成負相關,而其當期和滯后1期對生態效率無顯著影響;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與地方財政支出規模交互項的滯后2期與生態效率成正相關,而其當期和滯后1期對生態效率也無顯著影響,即假設H3部分成立。一個地區的基礎設施越完善,將弱化縱向財政不平衡對生態效率的作用,強化地方財政支出規模對生態效率的作用,且其作用時間均有滯后性,原因在于基礎設施的投建都是周期較長的工程。
(三)模型的穩健性研究
為研究地區經濟發展差異對上述結論的影響,本文將分別對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進行面板數據回歸,并對上文結論的穩健性做出判斷。表2分別匯總了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財政相對收支能力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回歸結果。經Hausman檢驗拒絕原假設,所以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基于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以及全國范圍內3種模型有效性的考慮,本部分只對我國東中西地區進行IV估計,表2中三個地區的模型均通過檢驗。
由表2可知,東部地區生態效率從滯后2期起與當期生態效率成負相關,中西部地區從滯后3期起開始負相關。中西部地區縱向財政不平衡與生態效率成負相關,縱向財政不平衡的平方項與生態效率正相關,而東部地區這兩項均對生態效率無顯著作用。筆者結合圖5認為,東部地區處在A區的偏底端,即實線與虛線的交接處,正在進行轉型發展。H1對于中西部的作用依舊成立,東部地區無顯著影響,說明在東部地區縱向財政不平衡與生態效率的關聯性不穩健。
東部與中部地區地方財政支出規模滯后3期與生態效率成正相關,而西部地區成負相關。原因在于盡管各個省市的財政支出都在增加,但相對增長的速度不一。從而導致西部地區政府公共財政支出占全國財政總支出的比例反而下降。H2對于東部中部地區成立,在西部地區表現為負數,我國西部地區地方財政支出規模與生態效率之間的關聯性并不穩健。

圖5 生態效率與縱向財政不平衡關系圖
三個地區縱向財政不平衡與基礎設施交互項的滯后2期與生態效率成負相關,地方財政支出規模與基礎設施交互項的滯后2期與生態效率成正相關。H3對于我國東中西三個地區依舊成立。
此外,東中西部地區的人均財政收入與人均GDP對生態效率均無顯著影響。人口規模與生態效率三個地區都成負相關。
綜上所述,縱向財政不平衡與地方財政支出規模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不穩健,并與經濟發展程度相關。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縱向財政不平衡對生態效率的影響不顯著,地方財政支出規模對生態效率有正面作用。經濟欠發達地區縱向財政不平衡對生態效率有負面作用,地方財政支出規模對生態效率有負面作用。且經濟發達地區生態效率處于A區底端,欠發達地區處于A區生態效率快速下降階段。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根據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業聯合會(WBCSD)定義的生態效率公式,在量化環境效率和資源效率的基礎上降維合成生態效率綜合指標,并進一步從縱向財政不平衡和地方財政支出規模的視角研究財政相對收支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結論如下:(1)在較發達地區,縱向財政不平衡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不顯著,地方財政支出規模促進區域生態效率的發展;在欠發達地區,縱向財政不平衡和地方財政支出規模均抑制區域生態效率的發展;(2)縱向財政不平衡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表現為即期作用,地方財政支出規模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表現為滯后作用,一般滯后3年以上;(3)在基礎設施較為完善的地區,地方財政支出規模對生態效率的促進作用較強,縱向財政不平衡對生態效率的抑制作用較弱,其作用同樣具有滯后性。

表2 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生態效率與VFI、FD回歸結果
從分析的結果看,提高我國生態效率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第一,樹立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積極引導較發達地區進行科學創新發展,進一步優化結構,形成經濟增長新動力,鼓勵欠發達地區進行金融創新促使政府形成更好的融資能力,降低縱向財政不平衡水平,同時有選擇的引進產業,孵化新業態、新模式;第二,國家應積極開展財稅體制改革,進一步調整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的責任,在可控范圍內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共財政支出能力。有關地方政府加快對接“一路一帶”、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戰略規劃,抓緊機遇,迎難而上;第三,繼續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傾斜力度,擴展水陸空三維空間通道,通過轉移支付縮小東中西財政收入的差距。推進全國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建設,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減弱縱向財政不平衡對生態效率的抑制作用,強化地方財政支出規模對生態效率的促進作用;第四,改革政府考核機制,進一步轉變并明確界定政府職能。轉變地方政府唯GDP論的發展,引入生態文明到整個社會發展的每個層面。
〔1〕鄒超.財政分權、政府競爭與教科文衛支出[J].北方經濟,2013(22):11-20.
〔2〕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J].經濟研究,2007(7):36-50.
〔3〕陳碩.分稅制改革、地方財政自主權與公共品供給[J].經濟學(季刊),2010,4:1427-1446.
〔4〕江慶.中央與地方縱向財政不平衡的實證研究:1978-2003[J].財貿研究,2006(2):78-84.
〔5〕江慶.分稅制與中國縱向財政不平衡度:基于Hunter方法的測量[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7(1):13-16、26.
〔6〕劉玲玲,馮懿男.分稅制下的財政體制改革與地方財力變化[J].稅務研究,2010,4:12-17.
〔7〕郭慶旺,賈俊雪.財政分權、政府組織結構與地方政府支出規模[J].經濟研究,2010,11:59-72、87.
〔8〕傅勇,張宴.中國式分權與財政支出結構偏向:為增長而競爭的代價[J].管理世界,2007(3):4-13.
〔9〕龔鋒,盧洪友.公共支出結構、偏好匹配與財政分權[J].管理世界,2009(1):10-21.
〔10〕W illard B.The Sustainability Advantage:Seven Business Case Benefitsofa Triple Bottom Line[M].Gabriola Island:New Society Publishers,2002.
〔11〕W 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 BCSD)Eco-Efficiency:The Business Link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M].Cambridge:MIT Press,1999.
〔12〕OECD Eco-efficiency.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and Development[R].Paris:OECD,1998.
〔13〕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Making sustainability accountable:eco-efficiency,resource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R].Copenhagen:EEA,2001.
〔14〕顧程亮,李宗堯.中國經濟發展的生態效率研究——基于FA-DEA組合模型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J].資源開發與市場,2015,,31(8):932-937.
〔15〕黃和平.基于生態效率的江西省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研究[J].生態學報,2015(9):1-11.
〔16〕BoadwayR,Tremblay JF.A TheoryofFiscalImbalance[J].FinanzArchiv,2006,62(1):1-27.
〔17〕Shah A,Boadway R.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Transfers:Principlesand Practice [M].W ashington D.C.:W orld Bank Publications,2006:1-51.
〔18〕Breton A.Competitive Governments:An Economic Theory ofPolitics and Public Finance [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19〕Collins D J.The 2000 Reform ofIntergovernmentalFiscal Arrangements in Australia [R].Commission on Fiscal Imbalance,Quebec,2002.113-143.
〔20〕Matier C,W u L,Jackson H.Analysing 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 in a Framework of Fiscal Sustainability[Z].Ottawa:DepartmentofFinance,2001.
〔21〕Hallwood P,MacDonald R.The Economic Case for Fiscal Federalism [A].Ashcroft B,Coyle D,Alexander W .New W ealth forOld Nations [C].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96-116.
〔22〕龔鋒,雷欣.中國式財政分權的數量測度[J].統計研究,2010(10):47-55.
〔23〕劉成奎,柯勰.縱向財政不平衡對中國省際基礎教育服務績效的影響[J].經濟問題,2015(1):7-14.
〔24〕羅偉卿.財政分權及縱向財政不平衡對中國基礎教育質量的影響[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S1):13-20.
【責任編輯 郭艷嬌】
F812.4
A
1672-9544(2016)04-0046-10
2015-06-06
顧程亮,經濟學教研部,經濟學碩士,研究方向為區域可持續發展;李宗堯,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區域經濟等;成祥東,經濟學教研部,經濟學碩士,研究方向為區域經濟。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基于利益相關者視角的區域生態文明多層次協同治理研究”(14BJL102);江蘇省社科基金“‘五位一體’的江蘇生態文明新體系研究”(13W TB024);江蘇省第四期“333高層次人才培養工程”江蘇生態文明建設的多層次協同治理研究(BRA2014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