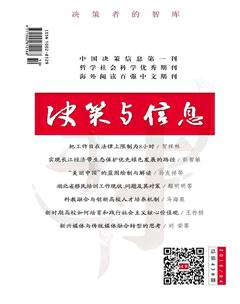論定價(jià)權(quán)的客體
[摘 要] 定價(jià)權(quán)的客體既是對定價(jià)權(quán)進(jìn)行法學(xué)認(rèn)知的邏輯起點(diǎn),也是定價(jià)權(quán)進(jìn)入立法、執(zhí)法和司法等實(shí)踐領(lǐng)域的前提。定價(jià)權(quán)的爭奪是以交易成本貨幣化制度為手段,并以獲取交易成本貨幣化利益為目的,因而定價(jià)權(quán)的客體是交易成本貨幣化制度與制度性交易成本貨幣化利益共生共融而形成的制度與利益的辯證統(tǒng)一體。應(yīng)當(dāng)以“經(jīng)邦濟(jì)國、經(jīng)世濟(jì)民”這一經(jīng)濟(jì)法的價(jià)值目標(biāo)作為定價(jià)權(quán)制度預(yù)設(shè)體系的審美和評價(jià)標(biāo)準(zhǔn),由此構(gòu)建信息文明時(shí)代科學(xué)的法制秩序。
[關(guān)鍵詞] 定價(jià)權(quán);交易成本貨幣化;定價(jià)權(quán)客體;制度;經(jīng)濟(jì)法
作為信息文明時(shí)代最重要的法律權(quán)利,定價(jià)權(quán)已經(jīng)從根本上決定著利益在國內(nèi)和國際的流向和歸屬,這是因?yàn)閮r(jià)格可被交易成本貨幣化制度鎖定在國內(nèi)和國際的壟斷資本所預(yù)設(shè)的范圍,通過掠奪性高定價(jià)人為提高貨幣化的交易成本而使利益流向國內(nèi)和國際壟斷資本的勾結(jié)體系中,使得大多數(shù)國家特別是發(fā)展中國家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失去任何福利意義。相反,經(jīng)濟(jì)發(fā)展都成為掠奪性高定價(jià)手段,從而使民眾普遍背上住房、教育和醫(yī)療等民生方面的沉重債務(wù)。全世界債務(wù)規(guī)模已經(jīng)基本與全世界的貨幣發(fā)行規(guī)模相等,因?yàn)楦鶕?jù)貨幣的發(fā)行原理,貨幣的本質(zhì)就是債務(wù)。可以肯定的是,一個國家的貨幣發(fā)行規(guī)模越大,那么這個國家的債務(wù)也就一定會越大,因而,貨幣的發(fā)行本質(zhì)上是交易成本貨幣化的過程,是通過交易成本貨幣化的制度完成的過程,以最終獲取交易成本利益。本文就此談?wù)剛€人想法,以就教方家。
一、 定價(jià)權(quán)的本質(zhì)是交易成本的貨幣化過程
定價(jià)權(quán)的法律化是法學(xué)界一個公認(rèn)的難墾領(lǐng)域。法學(xué)界在近幾十年的發(fā)展中之所以陶醉于財(cái)產(chǎn)權(quán)、知識產(chǎn)權(quán)、營利權(quán)、行政權(quán)、刑罰權(quán)和訴訟權(quán)等體系構(gòu)建,就是因?yàn)椋@些體系的構(gòu)建是重要的。但不要忘記,這些體系對于調(diào)節(jié)利益平衡卻很難起到作用,因?yàn)槔娴穆窂揭来婧椭贫孺i定,所以,這些權(quán)利體系構(gòu)成的制度體系就將本已嚴(yán)重的利益失衡鎖定在既得利益集團(tuán)預(yù)設(shè)的藩籬內(nèi),且一步一步地將社會矛盾推向火山口,如果不能在社會矛盾集中爆發(fā)前找到一種新的治理方法,那么,定價(jià)權(quán)失衡的交易成本貨幣化核彈就有可能炸毀整個社會乃至世界,因而作為法學(xué)界有義務(wù)反思并制止這個問題發(fā)生。
經(jīng)濟(jì)學(xué)和金融學(xué)已經(jīng)關(guān)注定價(jià)權(quán)問題,國內(nèi)研究稀土、大豆、藥品、住房、股票、期貨和人民幣的定價(jià)權(quán)的論文已經(jīng)多達(dá)近2000篇,而法學(xué)論文卻只有18篇,從總體上對定價(jià)權(quán)進(jìn)行法學(xué)研究的論文更是寥寥數(shù)篇,至于從法理學(xué)研究定價(jià)權(quán)問題,至今仍為空白。如果法學(xué)界不能從法理上解析定價(jià)權(quán),那么只有兩種可能:一是智力資源缺失,二是立場問題。
回到現(xiàn)實(shí)中來。今天彌漫全國乃至全球的貧富差距問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中原因有千百種,但不可否認(rèn)的是:現(xiàn)有的以價(jià)格發(fā)現(xiàn)機(jī)制雙軌制為利益傾斜性杠桿的定價(jià)權(quán)制度體系,正在將全國乃至全球的利益流向鎖定在大多數(shù)人日益走向貧困乃至破產(chǎn)的方向,這種利益流向是通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貨幣化實(shí)現(xiàn)的,其手段是將大眾的基本福利(住房、教育和醫(yī)療等)單邊市場化并進(jìn)行掠奪性高定價(jià),劫略了大眾的存量財(cái)富尺度和未來幾十年的增量財(cái)富尺度。貨幣作為勞動的價(jià)值尺度正在不斷被弱化、模糊化和邊沿化,作為交易成本尺度的功能正在被房產(chǎn)、證券和期貨等交易工具無限度立體式擴(kuò)張,在貨幣領(lǐng)域,幾乎沒有實(shí)體經(jīng)濟(jì)的喘息空間,一張由交易成本貨幣化制度體系構(gòu)成的天網(wǎng)正在灑向全球,人類正在作繭自縛。個案的公正或許可以滿足人們的好奇與眼球,但對于系統(tǒng)性的利益失衡和貧富懸殊來說,法律所主張的公平、公正和公開在哪?“天賦”的“人權(quán)”又在何處實(shí)現(xiàn)?
回答這些問題的可能是以歷史事實(shí)的邏輯作為研究的基礎(chǔ)和出發(fā)點(diǎn)。其實(shí)國內(nèi)乃至全人類的系統(tǒng)性利益失衡和貧富懸殊的根本原因是資本占有者有意或無意地將創(chuàng)造人本身的勞動異化為獲取財(cái)富尺度的手段,人類正在錯誤地將財(cái)富尺度理解為財(cái)富,正在進(jìn)一步將貨幣化的交易成本理解為財(cái)富,因而普遍通過交易房產(chǎn)、貴金屬、股票、期貨等金融活動使財(cái)富增值發(fā)生非理性沖動。如一套普通住房的交易價(jià)格,在不同地點(diǎn)的差值高達(dá)數(shù)十倍甚至數(shù)百倍,那這套住房在時(shí)間這一維度就實(shí)現(xiàn)了完全的交易成本貨幣化。因?yàn)樵诮灰字黧w者看來,住房的造價(jià)可以忽略不計(jì),說白了這就是泡沫經(jīng)濟(jì)。再如股票、期貨、金融期貨等虛擬經(jīng)濟(jì)交易,完全是對契約本身的買賣,成為了交易成本的貨幣化對賭游戲。定價(jià)權(quán)就在交易成本貨幣化過程中凸顯其無可替代的主導(dǎo)性地位。在國內(nèi),如果某一階層失去了定價(jià)權(quán),那么,他們就會失去現(xiàn)有和未來的所有財(cái)富尺度;在國際上,如果某一國家失去了定價(jià)權(quán),那么,這一國家就會被鎖定在越來越貧困的深淵。歷史已經(jīng)證明、現(xiàn)在正在證明、將來必將繼續(xù)證明,筆者對國內(nèi)外經(jīng)濟(jì)形勢的總體判斷不會錯 [1]。
定價(jià)權(quán)作為交易成本貨幣化的制度利益,它的客體由交易成本貨幣化制度和利益兩個層次構(gòu)成,交易成本貨幣化制度是手段,交易成本貨幣化利益是目的,因而定價(jià)權(quán)雙方或多方總是圍繞交易成本貨幣化制度的運(yùn)行展開博弈,無論哪方,說到底都是為了獲取交易成本貨幣化利益。
二、 定價(jià)權(quán)客體是交易成本貨幣化的制度與利益的辯證統(tǒng)一體
根據(jù)法哲學(xué)和法理學(xué)關(guān)于權(quán)利(力)客體的基本原理,權(quán)利(力)的客體是指權(quán)利(力)指向的對象。法學(xué)界大多數(shù)學(xué)人認(rèn)為,現(xiàn)有的權(quán)利(力)客體主要有物、人身、行為、精神產(chǎn)品及信息。尤其值得贊賞的是,我國著名法學(xué)家張文顯教授認(rèn)為,國家權(quán)力和勞動力也可作為法律關(guān)系的客體[2]。經(jīng)濟(jì)法學(xué)家陳乃新教授認(rèn)為,國家權(quán)力本質(zhì)上是反思性勞動力,主張將勞動力權(quán)作為經(jīng)濟(jì)法的基石范疇來奠定經(jīng)濟(jì)法理論體系的基礎(chǔ)[3]。這些研究模式或創(chuàng)造性的研究成果很有價(jià)值,值得定價(jià)權(quán)研究借鑒。對于定價(jià)權(quán)客體的考察,除了要充分吸收現(xiàn)有的研究方法外,更多地是要將視野轉(zhuǎn)向經(jīng)濟(jì)、金融和法律等多學(xué)科整體性思考,必要時(shí)應(yīng)置于哲學(xué)層予以分類和整合。
(一)定價(jià)權(quán)的手段性客體是交易成本貨幣化的制度
對定價(jià)權(quán)客體的研究需要深刻理解定價(jià)權(quán)的歷史和邏輯,定價(jià)權(quán)是雙方或多方博弈的結(jié)果,這個結(jié)果就是規(guī)則,由規(guī)則構(gòu)成的系統(tǒng)和整體就是制度,因此定價(jià)權(quán)各方都圍繞系統(tǒng)化的規(guī)則(即制度)展開激烈的博弈,誰制定規(guī)則,誰就掌控定價(jià)權(quán)。理解制度對定價(jià)權(quán)的決定性意義需要遵循歷史演變的基本邏輯:農(nóng)業(yè)文明時(shí)代分配財(cái)富主要靠拓展領(lǐng)土范圍和統(tǒng)治權(quán);工業(yè)文明時(shí)代分配財(cái)富主要靠技術(shù)先發(fā)優(yōu)勢爭奪殖民地范圍并通過培植代理人實(shí)現(xiàn)對殖民地國家或地區(qū)利益的整體性盤剝;而信息文明時(shí)代分配財(cái)富則主要靠規(guī)則爭奪定價(jià)權(quán)來實(shí)現(xiàn)對全球利益的超時(shí)空獲取和輸送。制度已經(jīng)成為最重要的權(quán)利(力)客體,今天幾乎所有的利益爭奪和分配,都是以制度為手段實(shí)現(xiàn)的。在信息文明時(shí)代,由于信息在全球超時(shí)空共享,定價(jià)權(quán)各方通過規(guī)則對全球資源和財(cái)富進(jìn)行超時(shí)空分配,如美元和美國主導(dǎo)的世界規(guī)則掌握著全球資源和財(cái)富的定價(jià)權(quán),所以美國總是以“國際法”的名義并憑借其強(qiáng)大的科技和軍事實(shí)力充當(dāng)世界警察,進(jìn)而在世界各地執(zhí)行規(guī)則(即“執(zhí)法”)。
我們知道,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客體是財(cái)力,行政權(quán)的客體是組織力,刑罰權(quán)和訴訟權(quán)的客體是司法力。定價(jià)權(quán)的客體則與它們不同,是直接指向制度這一對象,這些制度包括民事制度、行政制度、刑法制度、經(jīng)濟(jì)制度、土地制度、知識權(quán)制度、司法制度和金融制度等等,這些制度由誰來制定和實(shí)施,誰就掌握該領(lǐng)域的定價(jià)權(quán)。無論制定和實(shí)施何種制度,本質(zhì)上都指向交易成本的貨幣化利益。因而,在上述定價(jià)權(quán)的客體中,金融制度是啟動其他所有制度的發(fā)動機(jī),沒有金融制度提供動力,上述制度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定價(jià)權(quán)也就無法賴以存在。所以,金融制度或稱貨幣制度是定價(jià)權(quán)的終極客體。在國內(nèi),通過金融制度的設(shè)置,可以剝奪他人的利益或?qū)⒗孑斔偷教囟ǖ睦婕瘓F(tuán);在國際,可以剝奪他國利益或?qū)⒈緡孑斔偷剿麌貏e在信息文明背景下的電子貨幣時(shí)代,這種利益剝奪和輸送僅在鼠標(biāo)一點(diǎn)之間即可完成,就可通過金融杠桿打破定價(jià)權(quán)的均衡,將交易成本的承受度向制度的制定者和實(shí)施者(利益集團(tuán))傾斜。
通過制度來爭奪利益在信息文明時(shí)代可暢通實(shí)現(xiàn)。因?yàn)橹挥行畔⒏叨裙蚕恚庞锌赡苁估婕瘓F(tuán)整合成一個制度化的共同利益體。針對這一現(xiàn)象,有學(xué)者提出了共濟(jì)會整體利益概念,盡管這一認(rèn)定還處于推斷和求證階段,但從世界定價(jià)權(quán)及其游戲規(guī)則的制定和利益的最終流向情況看,的確有一個無形組織在指揮著人類財(cái)富的生產(chǎn)、分配和消費(fèi)。例如股市和房市泡沫破滅后的貨幣性財(cái)富流向哪里了?如果將貨幣視為能量,那么這些能量所導(dǎo)致的負(fù)債和破產(chǎn),又是被誰吸走了?股市和房市的定價(jià)權(quán)決定在誰的手上,誰又最終獲益?等等。要知道單就中國房市的市值就達(dá)到了300萬億元人民幣,那么,這個巨大的貨幣泡沫將會給中國經(jīng)濟(jì)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呢?要回答這些問題,還不能簡單歸責(zé)于我們對經(jīng)濟(jì)泡沫本身的無知,應(yīng)該看到,確實(shí)有人想通過房地產(chǎn)這個制度化的賭博將泡沫籌碼兌現(xiàn)成天文數(shù)字的貨幣性財(cái)富,以將中國賤賣資源、環(huán)境乃至本屬國家資產(chǎn)的工廠所得的外匯作為兌現(xiàn)的籌碼,形成制度化的不可逆轉(zhuǎn)的綁架性交易成本貨幣化利益,形成一個基于定價(jià)權(quán)的顛倒性設(shè)置的利益分配鏈。到頭來,留給國人的只是天文數(shù)字的以GDP為量度的負(fù)債率。這從目前中國已經(jīng)陷入的環(huán)境資源危機(jī)、貧富分化危機(jī)、經(jīng)濟(jì)滯脹危機(jī)、藥品和食品安全危機(jī)、理性過度膨脹危機(jī)和德性逆向選擇危機(jī),便可看出中國現(xiàn)在已經(jīng)陷入經(jīng)濟(jì)、金融、社會和道德的系統(tǒng)性崩潰的巨大風(fēng)險(xiǎn)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交易成本貨幣化制度的當(dāng)下,不少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加入到了不擇手段、不計(jì)毀譽(yù)和不論后果地賺錢大潮中。然而當(dāng)杠桿性定價(jià)權(quán)的海潮退去后,交易成本貨幣化的光芒便照見誰在裸泳、誰又是真正的游泳者,于是制度性的住房、教育、醫(yī)療的交易成本貨幣化吞噬社會正義的基礎(chǔ)并醞釀著覆滅性的金融危機(jī)和經(jīng)濟(jì)危機(jī)便一目了然,真正的游泳者和裸泳者的貼身肉搏盡然展現(xiàn),繼續(xù)徘徊在有共識卻無共利的理性和德行的沖突中的雙方最終都走上了不歸之路。
(二)定價(jià)權(quán)的目的性客體是制度性的交易成本貨幣化利益
定價(jià)權(quán)是一個由經(jīng)濟(jì)、金融和法律等構(gòu)成的復(fù)合性概念,是與經(jīng)濟(jì)法將經(jīng)濟(jì)和金融內(nèi)化為法律而構(gòu)成的新法律部門相適應(yīng)的。在今天的利益分配中,透過貨幣的房地產(chǎn)按揭杠桿市場、股指期貨市場及商品期貨保證金杠桿市場等金融手段來分配貨幣化利益,這些貨幣化利益分配手段的特征,是純粹的制度分配。就是說,自進(jìn)入信息文明時(shí)代以來,分配利益的手段主要靠制度(游戲規(guī)則),在國際市場,正是國際金融和貿(mào)易規(guī)則的制定者掌控國際投資和貿(mào)易的貨幣化利益;在國內(nèi)市場上,同樣是由國內(nèi)金融和貿(mào)易規(guī)則的制定者掌控著國內(nèi)的貨幣化利益,這些貨幣化利益都是在交易中完成的,都是在交易中通過提高交易對方或他方的交易成本來實(shí)現(xiàn)貨幣化利益轉(zhuǎn)移而最終實(shí)現(xiàn)財(cái)富制度化轉(zhuǎn)移的[4]。
以中國房地產(chǎn)泡沫市場的形成為例,中國房地產(chǎn)制度由土地市場國家一級壟斷制度、商品房市場開發(fā)商集體二級壟斷制度、銀行按揭貨幣供給獲利制度3極3方構(gòu)成。其中,土地壟斷是這一制度的啟動基礎(chǔ),銀行按揭制度是這一制度的貨幣能源,正是這種按揭制度使能源不斷燃燒而釋放貨幣能量,從而導(dǎo)致土地和住房價(jià)格飛速上漲。在這種狀況下,如果取消按揭制度就會撲滅貨幣能量,那么,房地產(chǎn)市場必將熄火而進(jìn)入冰河時(shí)代;反之,正因?yàn)榉康禺a(chǎn)制度催生了房地產(chǎn)的巨大泡沫,而這個巨大泡沫使絕大多數(shù)國人喪失了安居工程的定價(jià)權(quán):鬼城遍神州,橋洞有露宿。這就預(yù)示著,一個嚴(yán)重的社會動蕩和分裂危機(jī)即將到來。
再如,2015年中國股票市場牛市和熊市急速交替而成的“猴市”,在多頭開戶、融資融券和股指期貨三大投機(jī)工具的推動下,迅速拉高股票指數(shù)(上證指數(shù)最高5200點(diǎn),股票流通市值高達(dá)近50萬億元人民幣),“莊家”及其“主力”以“多頭戶”自買自賣。一方面鼓勵散戶融資買進(jìn),一方面又暗暗出貨,使得散戶在很短的時(shí)間內(nèi)輸?shù)羰种械娜炕I碼,加上媒體唱合,莊家和主力瘋狂套現(xiàn)低位使籌碼殺空,將股市變成對散戶的集體獵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證券監(jiān)管部門竟以千篇一律的“股市有風(fēng)險(xiǎn)、入市須謹(jǐn)慎”打發(fā)廣大股民,于是在牛市和熊市不斷交替中損失散戶們20萬億元人民幣。問題在于,為什么“莊家”和“主力”能輕易將20萬億的交易成本貨幣利益收入囊中呢?那就是由證券監(jiān)管部門預(yù)設(shè)的多頭開戶、融資融券(金融杠桿)和股指期貨等虛擬經(jīng)濟(jì)交易制度造成,實(shí)質(zhì)上反映出證券監(jiān)督管理部門不僅沒有履行好牧羊人的角色,而是主動拆除羊圈,人為造成群狼剿殺眾羊的資本市場血腥,導(dǎo)致交易成本級“股災(zāi)”的不斷發(fā)生——股市漲跌急速交替這樣一種制度性災(zāi)難。
在信息文明時(shí)代,制度(系統(tǒng)性的規(guī)則)是分配利益的根本手段,爭奪制度性交易成本貨幣化利益是定價(jià)權(quán)的根本目的,定價(jià)權(quán)是交易成本貨幣化的制度與交易成本貨幣化利益的辯證統(tǒng)一體。說明在定價(jià)權(quán)博弈中,“經(jīng)邦濟(jì)國、經(jīng)世濟(jì)民”這一價(jià)值目標(biāo),是經(jīng)濟(jì)法的立法、執(zhí)法和司法等博弈規(guī)則(制度)運(yùn)行體系的內(nèi)在要求和審美標(biāo)準(zhǔn)[5]。
三、定價(jià)權(quán)是“經(jīng)邦濟(jì)國、經(jīng)世濟(jì)民”之法律權(quán)利
定價(jià)權(quán)已經(jīng)并將繼續(xù)成為信息文明時(shí)代最重要的法律權(quán)利,它是一種在經(jīng)邦濟(jì)國與毀邦喪國、經(jīng)世濟(jì)民與欺世盜民之間進(jìn)行選擇的法律權(quán)利。經(jīng)濟(jì)法作為“經(jīng)邦濟(jì)國、經(jīng)世濟(jì)民”之法,理應(yīng)將定價(jià)權(quán)納入其權(quán)利體系并作為其基本范疇加以研究,借以重構(gòu)經(jīng)濟(jì)法的權(quán)利體系。但在目前,我國定價(jià)權(quán)的喪失情況非常嚴(yán)重:在國內(nèi),利益集團(tuán)一體化的制度性逐利行為不斷推高國內(nèi)的住房、教育、醫(yī)療和投資的貨幣化交易成本,而厘清公權(quán)私用界限的官員財(cái)產(chǎn)申報(bào)與公示制度卻遲遲未能出臺,這就使得絕大多數(shù)國人失去了住房、教育、醫(yī)療和投資的定價(jià)權(quán)。在國際上,“中國買什么,什么就貴;中國賣什么,什么就便宜”的現(xiàn)象十分普遍,且形勢嚴(yán)峻,說明中國已經(jīng)喪失了在國際市場上的定價(jià)權(quán)。目前,中國獲得的GDP統(tǒng)計(jì)數(shù)字是不計(jì)算資源環(huán)境損失的增長數(shù),如果將環(huán)境損失折算其中,那么,中國GDP增長應(yīng)該為-15%,說明僅環(huán)境損失一項(xiàng)就抵消甚至超過了GDP的10%左右的年增長率。因此,到頭來中國在國際上又完全喪失了對本國資源環(huán)境的定價(jià)權(quán)。更惡劣的是,中國因資源環(huán)境已被極度消耗,加上大規(guī)模的財(cái)富型和知識技術(shù)型移民,中國的符號性資產(chǎn)將沒有相應(yīng)的資源性財(cái)富與之對應(yīng),因而,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惡性貶值就成為必然。再加上融資融券、現(xiàn)貨、期貨等虛擬金融工具對人民幣價(jià)值符號泡沫化的杠桿效應(yīng),中國又必定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fā)達(dá)國家的提款機(jī),即中國將失去人民幣這一終極性和根本性的定價(jià)權(quán),人民幣將面臨對內(nèi)和對外雙重惡性貶值的全面信用危機(jī)。如果恢復(fù)對美國“次貸”危機(jī)的記憶,我們則正在踏著歷史的車輪不斷重復(fù)昨天的悲劇,中國數(shù)百萬億元人民幣的房地產(chǎn)市值和數(shù)千萬套的城鎮(zhèn)空置房預(yù)示著:中國要么面臨金融危機(jī),要么將爆發(fā)經(jīng)濟(jì)危機(jī),甚至金融危機(jī)和經(jīng)濟(jì)危機(jī)同時(shí)爆發(fā),這絕非危言矗聽。因此,國家如果不立即果斷地采取有力制度性措施奪回國內(nèi)外定價(jià)權(quán),以降低中國的國內(nèi)外貨幣化交易成本,那么,這一天離我們就不會太遠(yuǎn)了。
奪回定價(jià)權(quán)的切入點(diǎn)和著力點(diǎn)就是改變定價(jià)權(quán)的博弈規(guī)則,即改變現(xiàn)有的交易成本貨幣化制度體系,以能否有效實(shí)現(xiàn)“經(jīng)邦濟(jì)國、經(jīng)世濟(jì)民”這一經(jīng)濟(jì)法的價(jià)值目標(biāo)為準(zhǔn)則,重構(gòu)現(xiàn)有的法律秩序,將信息文明時(shí)代的法律需求作為主導(dǎo)性法律秩序,盡快從所有權(quán)沖突中解脫出來,走上科學(xué)地緩和剩余權(quán)沖突的法制秩序新路。
[參考文獻(xiàn)]
[1]羅納德·哈里·科斯.企業(yè)、市場與法律[M].盛 洪,陳 郁,等,譯.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張文顯.法哲學(xué)通論[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9.
[3]陳乃新.經(jīng)濟(jì)法理性論綱[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
[4]陳雨露,楊 棟.世界是部金融史[M].北京:北京出版集團(tuán)公司,北京出版社,2011 .
[5]劉運(yùn)新.經(jīng)濟(jì)法實(shí)體法權(quán)利的可訴訟性研究[J].理論導(dǎo)刊,2010,(3).
[責(zé)任編輯:李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