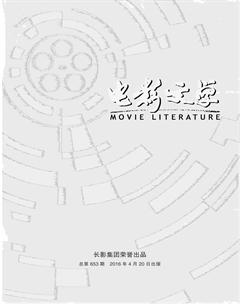《太平輪》對歷史與人性的詩意美學勾勒
[摘要]吳宇森最新電影作品《太平輪》被譽為中國版《泰坦尼克號》,同樣根據史實拍攝的兩部電影都共同表現了愛情主題。而電影《太平輪》的史實背景有著另一部作品不具備的戰爭因素,使得影片所表現的愛情更為復雜,映照出的人性特征也呈現出更為深刻的時代烙印。在《太平輪》當中,戰爭與船難歷史被以宏大的影像視角展開,卻將敘事的焦點落在了人性的描摹上,愛情主題最終只是淪為詩意化歷史與人性的媒介。
[關鍵詞]吳宇森;《太平輪》;歷史;人性
20世紀70年代,吳宇森以香港電影為起點開創了獨具個人特色的“東方暴力美學”,此后轉戰好萊塢,開始了中西文化融合的電影創作路線,在其執導的多部好萊塢電影當中,都滲透著深刻的中國傳統儒家思想與東方美學意識。與眾多香港電影人“北上”拍片的發展趨向一樣,在經歷多年的好萊塢電影制作以后,吳宇森也走向了回歸中國內地拍片發展的道路,這不僅是汲取多年好萊塢制片經驗對中國電影創作的反哺,同時也是順應當前電影市場發展趨向的必然選擇。
電影《赤壁》可謂吳宇森重返中國內地電影市場的標志性作品,取材于古典文學藝術使該片呈現出濃厚的文學性和古典美學特征,三國時期的歷史故事又賦予該片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吳宇森回歸中國內地電影市場的“開山之作”史詩題材的選定用意頗深,不僅表明吳宇森對于歷史感厚重的題材故事的創作喜好與意識傾向,同時也表現出適應當前商業電影市場環境的電影創作題材的轉型。因此,吳宇森導演的最新電影作品《太平輪》(上、下部)則具有內容題材的傾向性與商業電影市場的適應性雙重創作考量。電影《太平輪》取材于1949年的“太平輪事件”,在戰爭的硝煙與時代的變革當中,吳宇森以一種“廣角鏡”的呈現方式展現了掙扎求生存的眾生相,以愛情為糖衣,將戰爭歷史、船難歷史的展示以及對人性的探討詩意化,呈現出風格獨具的美學風格。
一、戰爭與船難的儀式化影像勾勒
對于吳宇森的新片《太平輪》,觀眾更傾向于將其看作中國版《泰坦尼克號》,相似的船難故事背景將兩部生長在不同文化環境中的電影聚攏在一起,甚至被安置在相同的災難片與愛情片的審美空間之中。但是,雖然同樣是災難片與愛情片的電影類型,吳宇森的《太平輪》與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號》卻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相較于《泰坦尼克號》而言,《太平輪》具有更加深厚的歷史底蘊與更加斑斕的時代色彩。從某種角度來看,電影《太平輪》橫跨了不同時期的歷史記憶,“太平輪事件”發生的時間也處于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歷史節點,致使該片絕非《泰坦尼克號》一般的小眾愛情視野,而是具有戰爭傷痛、民族仇恨、愛國情結、人性掙扎等更為復雜的情感體驗和主題維度。
歷史背景的復雜性與厚重程度決定了電影《太平輪》的拍攝勢必要有一定的格局和情懷,這樣才能將“太平輪事件”承載的歷史重量完全轉化為影像語言表現出來。因此,吳宇森將電影《太平輪》拆分為上、下部,即《太平輪(上)》(The Crossing Part 1)和《太平輪(下):彼岸》(The Crossing Part 2)。《太平輪(上)》主要負責描繪1949年“太平輪事件”之前的戰爭歷史,抗日戰爭勝利前夕與內戰的爆發激蕩出漂浮不定、殘酷冷峻的時代輪廓,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無論大人物抑或是小人物,命運都不曾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們的命運在時代的洪流之中被激蕩和擠壓;《太平輪(下):彼岸》主要負責描繪1949年“太平輪事件”船難歷史,八年抗日戰爭與紛繁內戰的徐徐落幕讓太平輪承載了比戰爭時期更為豐富的情感與歷史意義,本應承載船上的人們泅渡到幸福與光明彼岸的太平輪,卻隨著船難的發生將一切粉碎并一同沉入深海,象征幸福與光明未來的太平輪最終成了災難與毀滅的代名詞,而伴隨著死亡與毀滅,不同人物的命運及愛情也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對于戰爭歷史與船難歷史的影像化展示,吳宇森沒有選擇捷徑,并沒有嘗試從狹窄的個人敘事視角切入,而是選擇了規格龐大的敘事結構以及全面的大時代眾生相表現方式。而將審視《太平輪》的眼光放開后,我們也會發現吳宇森選擇1949年“太平輪事件”這一歷史事實也表現出別樣的家國情懷。“太平輪事件”不僅關涉內地人們的生計和命運,同時也牽連了內地與臺灣地區的諸多聯系,在歷史的觀察視角當中,太平輪號也呈現出隱喻性質的符號化意義。因此,電影《太平輪》的故事和選題本身就是情懷使然。
“太平輪事件”真實事件歷史背景的復雜性致使影像化展現的角度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向,即前文提到的格局問題。然而,吳宇森在影像化這段歷史的時候,并沒有刻意將戰爭的痛苦與船難的恐怖放大,而是選擇更宏觀與人性化的表現視角全面地展現這段戰爭歷史與船難歷史。在影像化戰爭歷史與船難歷史時,吳宇森利用自己擅長的儀式化電影語言進行表現,無論是戰爭場面還是船難場景,都在現實主義表現的基礎之上加入了超現實主義的表現技巧,現實世界與幻想世界的切換制造了一個儀式化的審美空間,一方面構建起影像的史詩感,另一方面也將人物形象之于歷史和時代進行了詩意化的展示。
因此,以《太平輪》(上、下部)為切入點反觀吳宇森的創作動機,恢宏龐大的戰爭場面與船難場面并非他想主要表現的部分,利用儀式化的影像語言,吳宇森將歷史記憶儀式化和詩意化,使之變成一種敘事氛圍與故事底色,讓其中的人物形象變得更加突出而個性鮮明,人物對于自己命運的無從掌握與人性的誓死掙扎也更加悲情與無奈。
二、大時代中小人物的人性探索
電影《太平輪》選擇的故事背景過于復雜與宏大,相較于以往的同類影片而言,該片將“大時代”這一概念變得更為龐大,“大時代”背景的過于龐大反襯出生活在當時人們的渺小,在這種背景當中,無論身處何種社會階層與生活境況中的人們,命運都有著一定的相似性,命運同樣不曾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是被時代所牽扯、激蕩甚至扼殺。抗日戰爭雖然即將結束,但是八年抗戰對于人們生活的毀滅性沖擊是無法忽略的。在戰爭的血雨腥風之中,人們求生的意志從未如此強烈和堅定,生命的脆弱也從未如此直接地展現在人們面前,而人們的命運也從未如此動蕩和無從掌握。經歷過戰爭的洗禮,戰爭的傷痛記憶始終根植于人們的頭腦深處,時時刻刻提醒人們和平年代與安定時光的可貴以及活著的美好。戰爭過后,上流社會的歌舞升平與燈紅酒綠回歸,而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們重新為了生計奔波忙碌。但是,抗日戰爭的余溫尚未褪去,內戰再次打響,戰爭的火焰迅速將人們的生活吞噬。吳宇森利用三個層次與結構對“太平輪事件”發生之前的戰爭歷史進行了展現和梳理,在三個層次的推進過程中,戰爭給予時代的灰暗色彩與傷痛被擴散開來,讓整段歷史呈現出無比龐大的輪廓。兩次戰爭給予時代的“大”規格被層層遞進的敘事方式與前后彼此觀照的影像語言構建起來。
由于這段歷史背景的復雜性,導致這一大時代背景中無論大人物或者小人物的命運都殊途同歸,無論是否權貴、是否平民,無論身處何種社會階層或生活境地,在抗日戰爭和內戰的輪番轟炸之下都變得體無完膚、傷痕累累,有些傷痛存留在肉體上,有些則扎根于精神之中,人們的命運都變得無從掌握。人們企圖掌握自身命運的愿望以及強烈的求生意志,使得不同人的人性呈現出不同的色彩,人性深層次的一面被戰爭與現實逐漸打磨出來。因此,電影《太平輪》當中的各色人物逐漸呈現出臉譜化的形象特征。在抗日戰爭中負傷瘸腿的國軍軍官雷義方,在抗戰中幸存下來的國軍通訊兵佟大慶,曾經的日軍軍醫、現如今成了往來海峽兩岸買賣藥品的嚴澤坤,一心尋找曾參加抗日戰爭的戀人的底層女性于真,身份不同的這些人卻在經歷戰爭的洗禮后表現出相同的生存愿望,并不奢求過分華而不實的理想和幸福,都表現出腳踏實地、實實在在地追求生活中微小的幸福感。他們急迫地想要回歸家庭生活,憧憬美好的愛情發生。但是,剛剛萌生新希望的眾人,再一次被內戰擊碎了關于未來的暢想。
因此,《太平輪》中眾人的人生再一次被卷入戰爭,理想生活再一次變得虛無縹緲,但眾人以無比堅定的信念堅持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戰爭的打擊與時代的雙重施壓之下,人性呈現出不同的特征。瘸腿的國軍軍官雷義方與富家千金小姐周蘊芬相戀并結合,懷揣著對于和平年代的憧憬與希望展開了新的生活;而雷義方與周蘊芬的幸福生活卻化作一張懸掛在照相館櫥窗中的結婚照,成為底層女性于真與國軍通訊兵佟大慶眼中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生活。于真與佟大慶的相遇相識源自對于基本生存生活的物質需求,二人為了能夠換取糧票而假裝夫妻拍了一張結婚照。在照片當中,于真并沒有像周蘊芬那樣穿著潔白的婚紗,而佟大慶依然一身軍裝。雷義方與周蘊芬的愛情對于二人而言,是更高層次的幸福生活理想;而曾經是日軍軍醫的臺灣人嚴澤坤,在抗戰勝利后重返臺灣,卻面對曾經的日本戀人被遣返回日本的失落境地,一心想要開始新生活的嚴澤坤夢想落空,日本戀人志村雅子只能存在于自己的夢中和記憶里。變革中的時代與動蕩的生活激發出每個人人性深層的另一面,為了生活與理想他們用盡全力地掙扎和抗爭。看似生活最為幸福圓滿的國軍軍官雷義方卻不得不重返戰場,戰爭奪走了他的生命,粉碎了他的生活理想;而國軍通訊兵佟大慶因為與底層女性于真的一面之緣而幻想出了自己理想生活的輪廓,并在反復想象描摹中越發真實,直到最終佟大慶開始相信自己的虛構和想象就是真實的,也正是這份虛幻的幸福想象讓他在戰爭中存活下來;底層女性于真為了能夠去臺灣尋找失散的戀人,白天在醫院上班,晚上則淪為妓女賣身籌錢,幻想著有一天賺夠了錢能夠買到登上太平輪的船票。
吳宇森對于片中的三對情侶——六個身份各異的人物形象,并沒有放大他們歷經戰爭的創傷與痛苦,反而更關注人性在動蕩時代的變化,他們在各自的生活軌道上對于理想所做出的努力和抗爭,在掙扎與抗爭過程中閃現的人性的光輝才是吳宇森竭力捕捉的動人瞬間。
三、結語
“太平輪事件”這一歷史過于復雜和沉重,時代的車轍在這段史實上留下了多條印記,也使得生活在這段特殊歷史時期的人們更為值得關注。對于當時的人們來說,“太平輪”絕非只是一艘通連海峽兩岸的豪華客輪,更是一艘泅渡心靈的希望之船,“太平輪”承載著他們對于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希望,帶領他們逃離戰爭,脫離苦海。而“太平輪”的最終沉沒也隱喻著宿命的悲劇,越是想要逃離,反而充滿不確定的動蕩時代會將一切頃刻間顛覆。“太平輪”的沉沒不僅是真實的歷史,同時也是導演吳宇森想象的屬于這段故事的應有結局,歷史決定了故事的悲劇性,在徹底的悲劇中才能迎來更徹底的全新的未來。所以,電影《太平輪》絕非簡單意義上的中國版《泰坦尼克號》,相對而言,杰克與露絲的愛情悲劇具有小格局的個人情感體驗,而《太平輪》中三對戀人的愛情故事則呈現出更強烈的屬于時代的悲劇色彩;船難的發生讓杰克與露絲陰陽兩隔,成就了愛情的悲劇和不完美,而“太平輪事件”幸存下來的于真和佟大慶的看似完美的愛情具有解讀的多面性,絕非單純的你儂我儂的純粹愛情。歷史的厚重感讓電影《太平輪》承載了太多的精神內涵,愛情主題只是影片實現詩意化表達的糖衣,包裹著宿命版的悲劇與無法釋懷的苦澀。
[參考文獻]
[1] 吳宇森,賈磊磊,許力勇.用電影傳播中國文化的精神——吳宇森導演訪談錄[J].當代電影,2010(10).
[2] 劉艷梅.淺析《太平輪(上)》片名與影片的不匹配性[J].電影文學,2015(05).
[3] 戈弓長.《太平輪·彼岸》:無力打撈的歷史[N].文學報,2015-08-13(024).
[4] 王妘,李坤晟.徐浩峰:好導演背后有自己的文化體系[N].新華每日電訊,2012-02-24(015).
[作者簡介] 王玉紅(1982—),女,陜西西安人,碩士,延安大學西安創新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藝術設計學、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