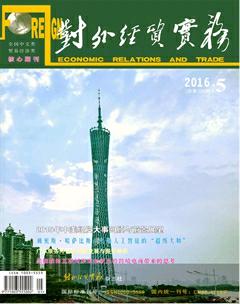中資企業跨國并購全鏡像
畢夫
依托著不斷烘熱的政策背景,借助著估值下移的有利時機,攜帶著厚重充盈的資本籌碼,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掀起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并購風暴。透過如火如荼的兼并行情,撥開起伏跌宕的競購波瀾,人們不僅觀賞到了資本要素彼此勾兌的神奇,也領略到技術因子互相匹配的精彩,同時強烈質感到了中國企業華麗轉身的健朗與魁偉。
“井噴”式行情
盡管過去一年中國經濟遭遇到26年來最低增速的尷尬,雖然人民幣留下了掉頭向下的貶值印跡,但卻并沒有稀釋中國企業漂洋過海大展資本并購拳腳的激情與張力。國際金融數據商Dealogic提供的數據顯示,2015年中資企業海外并購金額總計達到1239億美元,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的年度海外并購關口,同時也是并購金額第六年獲得連續增長。另據普華永道的統計報告,去年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實施的并購項目共394起,同比增長40%,創出歷史記錄。受此影響,中企海外并購交易存量項目達到9420宗。
沒等國人從盛宴之席上欣然離開,新年的精彩大戲就接著開幕。湯森路透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國企業跨境并購交易總規為951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了136%,同時創下單季海外并購中占比的最高紀錄,而且在當季亞洲最大10筆交易當中,全部都有中國企業的影子。按照全球兩大咨詢公司德勤和普華永道不約而同地預測,今年中國公司海外并購交易金額將比去年成長50%以上,并且未來幾年將繼續保持50%的增長。
中國化工無疑成為中資企業海外并購陣容中最為耀眼的明星。今年2月初,中國化工斥資430億美元收購瑞士先正達,開創了全球農業化工領域迄今為止的最大一起收購案,同時是史上第四大以全現金支付的收購案,更是中國企業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海外并購交易。資料顯示,先正達由歐洲藥企巨頭諾華和英國藥企阿斯利康的農業部門合并而成,在農藥和種苗領域居于世界首位,公司業務遍及全球90個國家和地區。
值得關注的是,在并購先正達的前半月,中國化工還以10億歐元收購了德國著名塑料和橡膠加工機械設備制造商克勞斯瑪菲集團,同時購入瑞士能源貿易商摩科瑞12%的股份,而在去年,中國化工出資79億美元完成了對意大利輪胎公司倍耐力的收購。當然,馳騁于國際并購市場的中國化工并顯得形影單吊。進入今年以來,人們不僅看到了天津天海投資以63億美元收購英邁、海爾斥資54億美元收購通用家電業務、萬達以35億美元收購好萊塢制片商傳奇娛樂、寧波均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斥資11億美元收購美國汽車安全零部件工程公司KSS等并購案進入收官階段,同時中聯重科以33億美元收購美國第二大工程機械制造商特雷克斯、北京控股以18億歐元收購德國垃圾焚燒發電廠運營商EEW Energy from Waste等也正處火熱推進之中。當然,這些收購也可能因某個確定因素,造成中途停止,但畢竟向四面八方傳遞了中國資本競走于全球的鏗鏘腳步聲。
朝著目標集結
波士頓咨詢公司(BCG)針對中國企業商業并購的一項市場調查表明,87%的中資企業希望通過橫向并購形成規模經濟,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5%的企業希望通過縱向并購完善上下游產業鏈;8%的企業希望通過混合并購整合資源。但從國內情勢看,目前中國政府正在推動供給側改革,加快“去產能”“去庫存”和“去杠桿”的進程,中國企業在本土發起并購的時機并不理想;同時,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日益推進,更多的中國企業試圖借此提前進入海外市場,以分享國家之間投資合作的紅利;不僅如此,中國政府已然啟動的“中國制造2025”,力推國內高端裝備業“走出去”,對接國外資源與產業。多方面力量的集合推動與倒逼著中國企業出擊和屯兵海外并購市場。
歐美國家特別是歐洲經濟增長的乏力,加之原油價格等大宗商品價格的持續下挫帶動歐洲國家資產價格估值中樞的不斷下移,同時出于對發達經濟體在科技與服務等無形資產戰略投資價值的追逐,歐美市場便成為了中國企業下注資本籌碼的最主要空間。Dealogic的數據顯示,去年中資企業在發達國家的并購規模占中國海外并購總規模的2/3左右,其中在美國的并購規模就占中國海外并購總規模的23%,同時在歐洲的并購投資占中企海外并購投資總額的近三分之一。而進入今年以來,這種趨勢還在強化。資料顯示,2016年截止目前所發生的5筆規模最大的跨境收購中,有4筆涉及中國企業競購美國和歐洲資產,總價值達617億美元。
正是看中了歐美企業的估值優勢,出海并購的中資企業陣營中于是頻現A股上市公司的身影。來自彭博社的數據表明,去年上海和深圳上市的中國公司海外收購和投資額達到了256億美元,同比增長48%。而Wind數據顯示,今年以來A股上市公司共發起46個海外并購項目,交易金額總計近500億元人民幣。對比發現,目前國A股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為53倍左右,為美國股市市盈率的三倍之多,同時為香港股市市盈率的五倍。對于上市公司,通過發起海外并購,不僅可以獲得目標公司的優質業務,還能拉低拉低本身的市盈率,從而彰顯出在資本市場的融資優勢。
相比于國有企業而言,民營企業對海外資源與要素的追逐意愿絲毫也不遜色。統計資料顯示,去年民營企業海外并購的交易數量是國有企業的近三倍,而在美國并購市場上,民企數量更是占到80%。不僅如此,與以往交易數量多但單筆金額相對較小而言,民營企業的并購如今也表現出了一定的規模級水平。如均勝電子對KSS的收購高達11億美元,中國商人盧先鋒收購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州范迪門土地公司的金額達2.02億美元。重要的是,據美國智庫榮鼎集團的統計顯示,目前中資企業的海外并購已擴展到近30個行業,這種并購多元化的格局也主要是通過民企的投資表現出來。
不再做“土豪”
押注澳洲鐵礦,染指非洲石油,競購南美有色……,對石油與礦產以及資源型企業的偏愛有加是中國企業過往并購留給外人的印象。但此一時彼一時。新一輪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將目光遷移到了品牌和技術以及能夠產生協同效應和利于提升自身管理水平的標的之上。榮鼎集團的統計報告顯示,在中企業海外并購中,資源領域的交易額占比已從2011年的83%猛降至目前的16%。特別是過去3年時間中,信息技術行業的出境并購案例逐年增加,分別為20起、54起和60起,共計投放資金達1100億美元。而今年截止目前,信息技術領域的境外并購已有5起,集合資金90多億美元。
將并購目光聚攏到海外科技標的的全新布局,反映了中國企業試圖提升自身在全球產業分工的層級以及完善自我產業鏈的商業訴求。以中國化工并購先正達為例,由于先正達不僅在在農藥和種苗領域具有與美國孟山都相抗衡的技術研發實力,而且在全球擁有廣泛的銷售渠道和網絡,中國化工將其納入麾下后,“微笑曲線”的兩端力量將大大加強;同樣,海爾日前并購了通用電氣旗下的家用電器公司,而通用家電擁有世界一流的物流和分銷能力以及美國市場強大的零售網絡關系,這對以硬件制造見長的海爾而言無疑可獲填缺補短之效。另外,在國內收購了展訊、銳迪科以及華三通信從而在手機芯片設計、銷售等領域布局棋子之后,前不久紫光集團出資38億美元收購美國數據存儲集團西部數據15%的股份,而且紫光正在發起對美國芯片制造商美光的收購,一旦落地,紫光集團的芯片設計、制造與銷售就可組成一個完整的價值閉環。
作為中資企業海外并購的另一個全新特征是,伴隨著國內傳統行業庫存與產能過剩壓力的增大以及策應結構升級與轉型之需,更多的出海資本將注意力轉移到了休閑娛樂、醫療保健以及體育健身等集結的服務行業。于是人們看到,大連萬達先后斥資6.5億美元和35億美元將世界鐵人公司和好萊塢電影制片商傳奇娛樂攬入懷抱,復興集團分別耗資18.4億美元和9.6億歐元將美國保險公司Ironshore和法國度假村集團“地中海俱樂部”納入麾下,安邦保險相繼斥資15.7億美元和 2.19億歐元將美國信保人壽保險公司和比利時勞埃德銀行收入囊中。接連不斷的資本大手筆無疑說明,收購標的在中資企業眼中不只是拓展海外市場的“橋頭堡”,更是支持自己未來爭奪未來國內服務業市場巨大紅利的強大勁旅。權威報告預測,未來10年國內服務業增加值占比將超過60%,市場空間十分巨大。誰先落子,誰就可能搶到制勝權。
被視為中資企業在海外并購市場愈走向趨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大部分中國企業在并購完成之后并沒有采取之前的“重手模式”,即向并購企業輸出管理團隊,強勢接管目標公司,而是采取了“輕觸模式”,即讓被并購企業保持獨立性,原公司高管團隊掌控公司運營,擁有較多的自主權,并最大程度地不裁員。如海爾保留了通用電器家電的所有高管人員,萬達保持了世界鐵人公司的完整管理班底,復星集團更是對地中海俱樂部高管職務按原職任命等等。“輕觸模式”表明中國企業更加注重并購后的組織與文化整合,從而謀求并購價值的整體提升,同時從財務的角度看,“輕觸模式”實際上是把中國的廣闊市場嫁接到收購標的中,在這種情況下最容易受到預期的商業效果。
坎坷中有忐忑
按照波士頓咨詢公司發布的研究報告,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交易的完成率僅67%,遠低于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企業的水平;同時,有統計數據顯示,國外的跨國并購有70%達不到股東預期,而同一比例在中國跨國并購中可能更高。另外BCG的一項統計調查發現,僅有32%的中國企業認為海外并案例“無故障”。不難看出,高歌猛進中的中資企業海外并購也并非一路綠燈或者紅旗招展。
諸如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FIUS)等國外政府監審機構無疑是羈絆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手腳的重要力量。據美國財政部發布的報告,最新一個年度內并購美國企業的國外買家中,遭到CFIUS審核最多的投資者來自中國,同時中國遭到的審核數量連續第三年超過其它國家。而進入今年以來,由于CFIUS的干預,飛利浦無奈取消了出售Lumileds照明業務給中資財團的交易,美國芯片制造商仙童半導體拒絕了華潤微電子的收購要約,中聯重科收購特雷克斯的計劃也陷入僵局。同時,中國化工收購先正達一案預計也將受到CFIUS的嚴格審查。
如果說CFIUS按照自身標準公正地審查中資企業并購案到也無可厚非,但經驗表明,在CFIUS所攔截或否決的并購商事中,絕大多數都是中國的國有企業。制度性歧視和排斥已經成為CFIUS的定向思維或慣常行為,其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涉及或危害到美國的國家安全。重要的是,一旦遭遇CFIUS的否決,中資企業不僅不能輕易脫身,還須同意支付一筆特殊的費用。以正在遭遇CFIUS審查的海航集團收購IT分銷商英邁一案為例,如果被CFIUS否決,海航將向英邁支付4億美元,高達收購價的6.7%。類似的結果均莫過如此。
排除CFIUS等外部擾動因素不論,中資企業自身的并購突進之舉也不能不令人捏汗。的確,通過收購目標企業,中資企業可能獲得技術、品牌等無形資產,以及提升自身規模經濟或者產業層次,但由此所支付的成本也定為不菲。觀察發現,目前中資企業海外標的的并購許多都是以高溢價完成的。如均勝電子收購KSS的溢價率達到94%,昆侖萬維收購Opera的溢價率達53%,中聯重科對特雷克斯開出了41%的溢價幅度,即便是中國化工收購先正達,溢價率也超20%。對此,不少專家將時下中資企業在海外市場的并購舉動與1980年代的日本企業與1990年代的韓國企業好有一比。上世紀80年代,日本企業攜帶巨額資金在全球瘋狂并購,甚至買下了紐約洛克菲勒中心,但由于收購溢價過高,同時沒能做好并購后的整合,最終95%的收購以虧損割肉出局;同樣,上世紀90年代,韓國在世界各地大舉兼并收購,但最終包括三星、LG在內知名企業不是摔得遍體鱗傷,就是無奈鎩羽而歸。
引人關注的是,支持中資企業高溢價收購的是高杠桿。一方面,中國企業在對外并購時的財務風險大,負債率偏高;另一方面,中國企業融資渠道單一,基本上依賴自有資金和銀行貸款,而且后者占大頭。因此,根據標準普爾全球市場情報的數據,54家公布財務報告并在去年進行過海外交易的中資企業的Total Liabilities /EBITDA(總債務與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的比值)中位數達到了5.4倍,而今年風頭正勁的中國化工并購則升至到9.5倍,中糧集團收購來寶農業的杠桿率為52倍,中聯重科更是高達83倍。但從全球來看,4到5倍就可以被視為“高杠桿”。
高杠桿驅動下的高溢價潛藏著的可能就是折價風險。望近處看,中國工商銀行55億美元投資南非標準銀行如今已縮水一半多,中國三峽集團35億美元收購葡萄牙電力公司EDP的35億美元至今已蒸發80%以上,紫光集團買入西部數據后如今賬面已浮虧超過110億元。看遠點,平安并購富通后承受巨額虧損之痛,TCL吞下湯姆遜后嚴重消化不良,上汽收購雙龍后尾大不掉……,初期期望種下龍種但最終收獲的是跳蚤,如此悲劇在中資企業海外并購中顯然絕非個案。
借勢與用謀
雖然中資企業在國際并購舞臺上展現出了較為凌厲的競發之勢,但全球著名的咨詢管理公司貝恩國際出具的報告表明,在中國企業的并購交易中,境外并購約占13%,而放眼全球,這個數字已經達到約50%。另外,按照頂層設計,未來10年中國對外投資將增長近三倍,即達到1.25萬億美元。跨國并購顯然將成為中國企業不可逆轉的選擇。不過,面對著前行路上的擾動風險與意外變局,中國企業必須增強自身的權謀決斷與應用技能。
隔離并購風險的首要前提就是中國企業必須做好充分而全面的盡職調查,調查的內容包括標的和潛在市場的吸引力、協同潛力、商業計劃和公司估值,以及并購執行的可行性等方面。 而在調查開始前,企業應當建立專司收購兼并的戰略制定和決策部門,以整合和串聯不同部門和人員并加強行動協調,同時企業還應設立合理的海外管控架構(包括財務管控中心、戰略管控中心和運營管控中心)及決策流程;在此基礎上,企業還應建立健全相關機制,明確并購工作流程以及各職能部門及人員的分工和職責,以此保證盡職調查按部分類的推進與落地。
與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相比,民營企業由于沒有政府背景的嫌疑,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東道國政府的抗拒感,并購過程中所面臨的管制成本要小得多。因此,出于規避國有企業在海外并購中屢成東道國監管機構靶子的風險,中企并購可采取民企與國企抱團出海的基本陣容,甚至可以選擇由民營企業打頭陣,國有企業背后提供資金與技術支持的合作方式。這就要求國企與民企必須消除所有制觀念的隔閡,正確處理并購后股權與公司治理權力分配的問題。政府也應當從審批程序,稅收豁免等方面為民營企業“出海”進一步松綁減負。
降低并購過程的投融資風險是中企跨國并購所要思考的最核心內容,為此,中國企業應當盡可能少用單方面的投資形式而轉為以合資的投資形式為主,以構造出國內資本與境外資本相融合的戰略聯盟。一方面,要與國內外私募股權基金尤其是跨國公司進行合作完成對目標企業的收購,以利用合作者的資本優勢和技術優勢,最大程度的分散與消除成本約束風險和政策管制風險;另一方面,要與目標收購企業進行合作,盡可能避免全資收購股權的嫌疑,同對方形成利益共同體。為此,中國企業可以考慮設立離岸公司,然后尋求境外合作企業,再行實質性并購的基本程序和路徑。
淡化收購的純商業化和功利化是中國企業應當修為的心態。為此,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不應當只滿足于獲取企業股權或者技術與品牌資源,而應當將并購行為與進入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事業結合起來。如企業并購過程之中或并購完成后可以將一部分資源放在當地進行深加工,以幫助當地增加就業和財政收入;另外,企業還可以與當地企業聯合進行基礎設施投資建設,或者參與當地的慈善事業;同時企業應當尊重當地國的法律法規和傳統文化,注重環境的保護等。
我們還須特別指出,中國企業應該學會運用購買并購保險工具來提高并購的成功率。由于并購交割后企業的風險主要來自于對并購目標的誤查和欺詐,而國際市場上基本都是通過購買購并交易保證賠償保險的方式轉移并購風險。通過購買與并購項目相關的保險資產,相關保險公司會為交易者提供財務追索權利,對交易結構進行設計,形成有效的價格談判工具,并保護交易方相關職務的經理人,同時有效地規避如稅務、財務、知識產權、環境保護等方面的風險。
需要重點強調的是,雖然不少中資企業將注意力轉移到了對技術與品牌等無形資產的收購上,但如何吸收新技術并產生化學反應卻是一們艱難的功課。須知,買得來技術,卻買不來研發能力,買得來研發團隊,卻買不來創意。因此,中國企業在海外并購中必須摒棄跑馬圈地的王者心態,在通過外部收購獲取技術的同時,更應不斷地提升自主研發能力與水平,構筑真正屬于自我的核心競爭力。也只有中資企業站到了為人仰視的平臺位置,才能底氣十足地統領那些歸于自己腳下的四方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