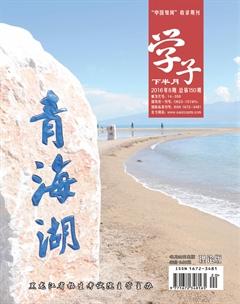歷練思維意識,閱讀教學的核心要旨
陸蕾
語言與思維相輔相成,沒有脫離了語言而單獨存在的思維,也沒有缺失了思維的語言空殼。因此,閱讀教學要在關注語言的過程中關注學生的思維意識,培養學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一、引導質疑,喚醒思維的潛在期待
閱讀教學,教師不能依循固有的思維方式、延續原本的思維路徑,在改變傳統思維習慣的基礎上,激活學生的思維動力,點燃學生的思維火花。
如在《嫦娥奔月》一文中,作者描寫嫦娥反抗逢蒙的威逼利誘時,僅以“周旋”一詞加以描述。教學中,教師則引領學生進行質疑:“同學們,關于這一段你們讀得過癮嗎?”學生若有所悟,紛紛這樣質疑:“作者這里只是說‘周旋,嫦娥究竟是怎么跟逢蒙‘周旋的呢?”此時,教師則緊扣學生的質疑,引導學生進行補充,要求學生想象設計嫦娥與逢蒙進行“周旋”的細節,并且要設計三個以上的回合。在學生的質疑想象中,兩人之間你來我往,“周旋”的細節和盤托出,嫦娥機智冷靜、逢蒙奸詐貪婪的人物形象扎根于學生的意識深處。
在這一案例中,教師正是依托學生文本閱讀的體驗,引領學生以質疑的思維關照文本,從而開掘出文本創作中的留白,并引領學生在補白的過程中豐富了故事發展的細節,歷練了學生思維的完整性和嚴密性,起到了較好的教學效果。
二、深入辨析,改變思維內在模式
辨析歸謬是鍛造學生思維品質的重要策略,也是促進學生批判性思維特征的重要舉措。教師可以結合具體文本中的某一知識點,巧妙地設置思維認知的障礙,引領學生在自主性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走出完全依托教師點撥、告知的認知窠臼,而在自身意識的對比、鑒定和批判中促進對知識的構建與運用。
如《林沖棒打洪教頭》一文中,作者以生動、簡練的筆觸刻畫了林沖處處謙讓、洪教頭驕橫跋扈的人物形象。教學中,教師緊扣文本語言引領學生對人物進行了深入細致的體悟,但并沒有就此止步,而是引領學生進一步深入辨析:林沖是這段故事的主人公,但課文中涉及林沖的語句并不及洪教頭多,你覺得這樣的構思合理嗎?在描寫中,作者運用了“一橫”“一退”“一掃”三個動作展現林沖的武藝高強和謙讓性格,并沒有一個“打”字,你覺得課題中的“棒打”準確嗎?作為一位名震武林的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有著一身本領,為什么還要處處忍讓呢?你還認為林沖是一位英雄嗎?你心目中的英雄究竟是怎樣的?……
三、窺探“風景”,再現思維的認知歷程
《語文課程標準》倡導“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閱讀教學就應該利用文本自身的特點,選擇適切的契機引領學生深入文本,引領學生在自主、合作和探究式的學習中開啟思維模式,嘗試著從不同的側面和維度來考量問題、解決問題,從而促進學生的認知與思考,提升學生的思維品質。
如在教學《愛因斯坦和小女孩》一文時,很多教師會涉及這樣的問題:愛因斯坦究竟算不算得上是一個偉大的人?這個問題或許對于教師等成人來說并不值得一提,但從兒童的視角來關注,愛因斯坦如此不修邊幅,著實令人費解。而在引領學生探究爭鳴的過程中,教師總是無意識地解釋為愛因斯坦潛心于科學研究,根本無暇打理自己的裝扮。如此解答真的契合生活實際和兒童的認知心理嗎?此時,教師則為學生拓展補充了資料,文本解讀不必提升到節約時間、潛心研究等上綱上線的層面上,原來愛因斯坦根本就是一個老頑童,他根本不屑于做這些事情。
四、促發辯論,鑄造思維的獨立意識
在閱讀教學中,教師不能以自身的解讀遮蔽學生的獨立認知,而要在鼓勵學生多元解讀的基礎上珍視學生的個性化認知體驗,改變他們唯唯諾諾、人云亦云的陋習,從而培養具有獨立思維與精神的現代公民。
如在教學《牛郎織女》時,很多學生都對王母娘娘棒打鴛鴦的行徑萬分痛惡,可一位學生則指出:“牛郎織女知法犯法,王母也是秉公執法而已,怪不得她痛下殺手。”這位同學的解讀雖然與眾不同,但其認知只是浮于表面,看待問題并不深刻。教師則以“你們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回了一招“太極推手”。此時另一位學生“拍案而起”指出:“這樣的法律是為誰制定的?制定得合理嗎?”教師順勢而下,激發了學生進行認知爭鳴,從而讓全體學生體悟到只有基于正常的倫常道德下的法律才是合理的,才值得我們遵守。
爭鳴的價值不在于結果順應,而在于兩種不同認知的交融碰撞、爭鳴辯論,學生逐步形成了自身獨立思維的意識。
總而言之,語言是思維的載體,閱讀教學要想促進學生生命的不斷發展,關注思維歷練、鑄造思維品質就必須成為教學不可獲取的重要內容。
(作者單位:江蘇省張家港市錦豐中心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