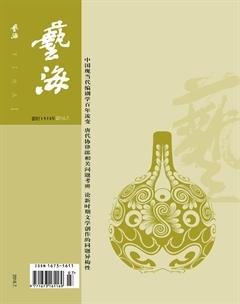“世紀之交”德奧音樂創作技術的總體發展
蘇楊
〔摘 要〕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嚴重的精神危機,這種精神危機直接波及音樂界, 對當時許多晚期浪漫派作曲家的世界觀和創作思想影響甚大,表現出音樂思維上“多維性”與“超人精神”的特征,也具體的體現在形式、結構、配器、和聲等作曲技術上的變化。
〔關鍵詞〕世紀之交 德奧音樂 理查·施特勞斯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下文簡稱“世紀之交”)是浪漫主義音樂活動的黃昏, 同時, 也是一個新的音樂時代來臨的轉折點。在這一時期中, 整個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動蕩、各階級的分化以及政治、經濟危機的出現給意識形態領域帶來了嚴重的精神危機。這種精神危機直接波及音樂界, 對當時許多晚期浪漫派作曲家的世界觀和創作思想影響甚大,精神上的重壓和多種復雜情感的交織, 更刺激了晚期浪漫派作曲家們表現內心世界的意欲, 他們試圖高度概括, 淋漓盡致地揭示外界生活與內心世界之間的尖銳矛盾,這樣也就使藝術形式和表現技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發展,在音樂創作中體現為形式結構、樂隊編制、音響概念等一系列突破性發展變化。
首先是形式結構的自由性。以理查·施特勞斯的交響詩為例,這一體裁的曲式結構沒有特別的規范,往往由所表現的具體內容來決定形式,但習慣上將創始人李斯特的交響詩作品結構相對典型:在整體上,將奏鳴曲快板和奏鳴交響曲的特點結合在單樂章中———從奏鳴曲快板的角度來看,它與主部、副部、展開部、和再現部相吻合;從套曲的角度來看,它又合乎于四個樂章的布局。“然而,施特勞斯并不遵循李斯特確立的這種交響詩的典型結構,他的音詩都有龐大的結構,但常以一種曲式作為基礎,如:《唐璜》以奏鳴曲式為基礎,《梯爾·歐倫什皮格爾》以回旋曲式為基礎,《唐吉訶德》是一首變奏曲,因而它的副標題是《茨岡主題交響變奏曲》。所以雖然他的交響詩結構復雜,聲部相互交織,卻錯落有致、經緯分明,令人贊嘆不已。”[1]
其次是不同形式的對比、并置。以交響曲的創作為例,這一體裁在浪漫派后期有著兩條不同的發展線索,而這兩條線索又并不是在這一時期才出現的,它們的存在有著歷史的淵源關系。以“表現論”為其美學原則的浪漫主義精神,與在十九世紀仍然有影響的,以“形式論”為其美學原則的古典主義精神相互對立、并置。甚至在貝多芬之后最終決定了浪漫主義占優勢時,這種對立與并置仍然存在。當然,這時的古典主義并不是前一世紀此種風格“映象式”的重復,而是在新的時代,有著新的認識并在新的高度上的重復。因此, 可以認為這是一種“浪漫的古典主義”。與其相對應的, 對浪漫主義的一些特征加以“強化”的另一方面, 則是“浪漫的極端主義”。這種音樂風格的二元性特點, 也就使十九世紀歐洲交響音樂的發展出現了兩條線索。
馬勒出身在波西米亞的猶太家庭里,長期遭受奧匈帝國民族歧視和社會壓迫的折磨, 并受到陀斯妥夫耶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損害者”學說、唯心主義哲學和泛神論等思想的影響,因此,在自己的交響樂中力圖體現出矛盾的情感風暴,體現“歷史必然的要求和這一要求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沖突”恩格斯語。盡管馬勒的某些交響樂作品包含著一些標題性、甚至歌劇性的因素,但這種標題性并無損于古典形式的完整性,也不是以文學題材和“樂外概念”為其創作靈感的主要來源。馬勒的音樂具有一種“內向”的特點,音樂思路不斷變換,音樂的發展受思想、情感變化的支配,并常有著一種沉緬于主觀內省之中的情調。
當馬勒在交響樂領域中展示其才能時, 德國作曲家理查·斯特勞斯在交響音樂創作中卻選擇了另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他在相當長的創作時期,特別是在成熟時期, 處在德意志帝國從自然資本主義過渡到帝國主義,瘋狂對外掠奪的軍國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時代。因此,他的世界觀和創作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當時德國文化領域中盛行的自然主義運動和尼采主觀唯心主義哲學的影響。由于文化危機的形成和音樂中日趨嚴重的文體僵化的危險傾向,斯特勞斯感到在創作中應打破這種沉悶的空氣,運用新的創作方法來表現現實生活,并試圖通過對某一特定對象細致的描寫,來充分擴大音樂的表現功能。斯特勞斯的主要作品幾乎都是受文學、傳說、哲學詩等“ 樂外概念” 的啟示而寫的。
這時的歐洲,音樂的發展正處于一個十分微妙的階段,各種流派不斷派生出來。普切尼的逝世,預示著浪漫主義的盡頭。勛伯格的初期探索具有相當的號召力,從小受到十九世紀古典音樂的影響,同時又對新的音樂形式著迷。而理查·施特勞斯的音樂即非主流而又不是傳統,截然不同的音樂,激起了兩派的支持與批判。直到1949年施特勞斯逝世時,人們才逐漸發現他用現代手法描寫現實的作品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他那個時期的歷史的象征。人們用不同的理解冠以各異的稱謂,諸如:無調性大師、十二音列主義先驅、未來派、客觀主義、新古典主義等等。施特勞斯幾乎成了各種流派的代理。
下面我們以理查·施特勞斯的作品為例,以微觀的視角解讀幾個創作技術上的變化。
第一,龐大、編制精細的管弦樂隊。充分運用的固定低音、固定低音音型、持續音、模仿、增時模仿、減時模仿、卡農、半音音階等多種形式的對位技術,能夠制造出豐富的音響層次。“多聲部立體音準意識,使每件樂器的獨立精準演奏與積極配合意識,均達到了各小聲部的等同標準。”理查·施特勞斯的管弦樂配器技巧純熟靈巧、極具特色,探索各種配器技巧,偏愛各種樂器的極限音域,在宏大的音響中增加緊張度,追求接近于自然、真實的音響效果和表現某種象征的理性觀念。把管弦樂隊中的每件樂器發揮到極致,是理查德·施特勞斯為表達多元藝術需求的精到之舉。為豐富音響效果、擴充織體層次,作曲家慣以整體的有意識拆分規劃,形成了錯落有序、立體交叉的組合。
第二,復雜音調的銜接。這一問題論述的是復雜音調在音樂作品里的表現形式,例如,在原有調性中,通過臨時升降記號表示出來。固有調性與臨時調性不斷碰撞,形成難以確定的音響;少升降記號或無升降記號的曲調內,大量出現臨時升降記號、還原記號或重升降記號,演奏經常處于不穩定的游離調性感覺之中;或“調性中途轉換,逐個音符間因較為頻繁臨時變化,造成難以抓住規律的復雜音調。” [2]
第三,復雜節奏的銜接。以理查·施特勞斯為例,當時的復雜節奏通常有以下表現形式:其一,無規則可以循多樣化的節奏樣式,構成了與獨奏截然不同的焦點。其二,大量無規則的休止時值,參與在復雜音調的演奏之中。其三,小時值組合的各式樣的連音組合、附點、切分等復雜節奏的頻繁、無規則銜接。
第四,和聲特點。理查·施特勞斯作品中的和聲與調性處理盡管延續了晚期浪漫主義的風格,但頻繁的轉調、離調,多調性的并置,橫向聲部的高度半音化處理等等,使他的音樂常常充斥著不和諧音的嘈雜之音,這無疑將傳統的古典調性拉向二十世紀音樂的邊緣。施特勞斯熱衷于對比和并置, 在宏大的音響中增加緊張度,追求接近于自然、真實的音響效果和表現某種象征的理性觀念,使他深受啟發的是那些把滑稽的成分和重要深刻的東西融為一體的手法。為了表現這樣廣泛的情感范圍,施特勞斯創造了一種音樂語言,他意識到新世紀的音樂語言應該有意識的缺乏風格的一致性——這樣的語言反映了對歷史困境的關注,很可能它預示了20世紀晚期對風格觀念體系的分解。
在評論界,這一時期的音樂家們歷來有著多角度的不同評價,在他們的性格中通常充滿了十分復雜的因素。這些因素使得其對作品永無止境的創新。他們的音樂構建極為復雜,異常龐大;他們采用極端音程來描述情感的方方面面,從尖利的哀鳴到猛烈的咆哮幾乎包攬無遺;他們不顧一切的處理方式幾乎到了狂躁的地步;他們的作品中充滿了矛盾體,像一個個交錯上升的螺旋圈,不斷發展;我們也可以把這看成一種突破:一種對自我的不斷挑戰和突破,不同時代不同作曲家的創作理念、藝術構思、音樂語言和藝術效果在其作品中碰撞、疊置、交匯、融合,直至升華......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人類的歷史上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時代,它所帶來的影響波及政治、文化以及各個領域,音樂與歷史歷來就是不可分割的共同體,從歷史的角度剖析音樂的發展此時期則顯得尤為重要,有待專家學者給予更多的重視與研究。 (責任編輯:曉芳)
參考文獻:
[1]克勞澤.姜志高.理查·施特勞斯交響詩的標題[J].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1993(02)
[2]劉東.“詩意與戲劇性”的完美結合——論理查·斯特勞斯藝術歌曲的獨特風格[J]. 星海音樂學院學報, 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