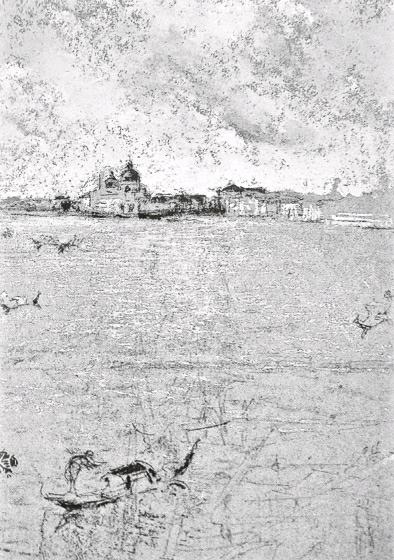回望夏塔
馬康健
說起昭蘇,自然就會想到夏塔,眼前或腦海里便呈現出一幅自然、原始、寧靜、純美的景象。其實,夏塔較早被人們認識還不是它的景觀,而是溫泉。
我最早慕名到夏塔是奔著溫泉去的。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昭蘇采訪時,聽說夏塔溫泉很有名,每年來這里治療關節風濕類病的患者很多,全疆各地的都有。當時旅游一詞還沒有被人們所認識,可能也沒有人被這里的景色所吸引。出于記者的職業習慣,我想去看個究竟,那里到底發生了什么,或者說正在發生什么。當時,通往夏塔溫泉的路還是自然形成的便道,小車行駛在上面東搖西晃,人很是受折磨。我坐在車里一邊隨車晃蕩,一邊想象著溫泉到底是個什么樣子,是個很大的如同旅游池一樣的泉嗎?或者是像小河一樣流著的水嗎?想了一路我也沒能想出個一二。在終于結束了備受折磨的旅程到達溫泉后,才發現一切都是那么簡單。溫泉緊挨著山,在每個泉眼處修有水泥池,由于每個泉眼的水溫度不同,便分別按泉水的溫度修建了一排小木屋。溫泉的水含有硫磺等多種礦物質和微量元素,據說對治療關節炎、風濕類病效果很好。我在采訪時發現,大多來這里治療的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每年都來,還有的是全家出動。問及泡溫泉的感受,多數人稱治療效果明顯。那晚我也泡了一次溫泉。好客的主人接二連三地敬酒,我很快就進入了微醉,不知是出于酒精度的緣故還是出于好奇,我在臨睡前暈暈乎乎的,下到了一個50度的泉水池里,剛下去皮膚有點受不了,但你堅持一會兒,就適應了水的溫度。讓我沒想到的是,在進泉水池時我的頭還暈得厲害,可泡了一會兒出來后,我頭不暈了,就像沒喝過酒似的。泡溫泉還有醒酒的功能,真是意料不到的事。夜靜靜的,似乎一切生命都停止在這一刻,望著遙遠的星空,感受著大自然的奇妙和神秘,我心里不由得升騰起一種敬畏之感。
要說夏塔被更多的文人和旅行者們認識,恐怕要數著名作家張承志了。他1993年寫的散文《夏臺之戀》(注:夏臺即夏塔),從景觀、歷史、民族和人文等方面對夏塔作了細致的詮釋。他寫道:“應該相信我,夏臺一線的一百多公里的天山北麓的藍松白雪,確是這個地球上最美的地帶……夏臺的美好,夏臺的安寧,夏臺的和平,不知為什么使人感傷。似乎真有一種無形的巨大神力創造了如此動人的和平,如此美好的夏臺。”“夏臺如同梅里美寫過的直布羅陀——每走十步就能聽見一種不同的聲音……。可是你可以去夏臺,至少可以去伊犁,去看看人交往的匯集點。”在此后的許多年里,我多次去過夏塔,一次次地體驗和感受夏塔的魅力,傾聽這里一棵樹一棵草甚至一塊石頭的聲音。可以說,在這里聽到的聲音比伊犁河谷任何一個地方聽到的聲音都古樸和真實。但不知什么緣故,夏塔溫泉仿佛一夜之間沒有人問津了,那一排破舊的小木屋,還孤零零地堅守在那里,似乎在等待著什么。眼前的情形讓我不禁回想起那年第一次與夏塔溫泉親密接觸的場景,那是一個多么美好的夜晚啊。睡在木板結構的屋里,聽著夏塔河的浪濤聲,有一種離開凡間置身于天庭的感覺。雖然溫泉廢棄讓我的心里多了一份思念,但夏塔原始森林里生長出的那些聲音,讓我永存一顆感恩之心。
我上世紀九十年代在昭蘇看草原石人時,那里的草足有一米多高,石人完全淹沒在草叢中。而現在草僅長到三四十公分高,為什么會這樣?我常常問著自己,和人有關嗎,和氣候變化有關嗎?找不出答案。于是當我每次往返夏塔時,在被這里古樸自然的景觀震憾時,內心深處會生出一絲的憂慮。但我又很快將這種憂慮壓制下去,把自己的身體調整到平靜狀態,等待著夏塔河的濤聲緩緩地流進心靈深處。
“我特別喜愛的,還不是夏臺領域中的那漫山遍野的天山腹地的美。久久體味著會覺得慢慢地被它攝去了心魂、并久久陶醉不已的,是那自然聚落的寧靜。”張承志這樣表述著內心的感受。的確,寧靜的夏塔,自然的夏塔才是我們所期望的;如果有一天破壞了這種寧靜和自然,夏塔也就不成其為夏塔了。
回望夏塔,激動和不安總是在我的心里起起落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