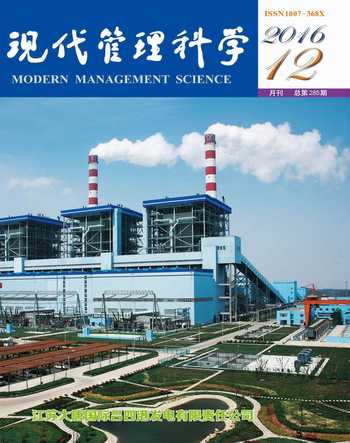城鎮化對金融杠桿的動態影響探析
李振 王曉煜
摘要:文章通過對124個國家1983年-2012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城鎮化和金融杠桿之間呈現出顯著的倒U型關系,即隨著城鎮化率的上升,金融杠桿水平會先上升后下降。具體而言,當城鎮化率達到56%~63%時,私人部門信貸/GDP可能出現拐點;當城鎮化率達到60%~63%時,M2/GDP可能出現拐點。文章根據最近5年中國城鎮化率的年均增速推算,預計中國的金融杠桿水平很可能在2019年-2021年進入拐點區域。
關鍵詞:城鎮化;金融杠桿;SYS-GMM
一、 引言與文獻回顧
城鎮化是維持經濟健康發展的強大動力,也是促進金融發展和創新的有力支撐,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國家現代化的發展程度。2013年11月,十八大三中全會做出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產業和城鎮融合發展,促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在2014年3月,正式推出《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明確了中國未來城鎮化的發展路徑、主要目標以及戰略任務。當前,中國正處在城鎮化加速推進、金融深層變革的關鍵階段,正確理解和處理城鎮化、金融發展兩者之間的動態聯系和規律,對于成功實現新型城鎮化和金融改革發展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國內外文獻就城鎮化與金融之間的關系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發展與金融創新對城鎮化進程的影響,而城鎮化進程對金融的影響則很少涉及。孫浦陽和武力超(2011),采用1995年~2008年120個國家的面板數據,使用2SLS估計方法分析了金融發展對全球各國城鎮化進程的影響,發現金融發展是影響城鎮化進程的重要因素。熊湘輝和徐璋勇(2015)通過對中國2004年~2013年31個省區使用空間面板模型進行分析發現,金融支持水平的提高對我國城鎮化發展具有促進作用。榮晨和葛蓉(2015)從市場和政府關系的視角檢驗了金融發展對城鎮化的支持效應,金融對城鎮化的支持在不同地區有明顯差異,而且,金融支持對政府干預、國有經濟所占比重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很多學者也認為城鎮化和金融發展之間存在一種互動機制。例如,賈洪文和胡殿萍(2013)認為,城鎮化和金融發展存在一種互動機制,通過擴大金融規模、適當提高金融效率和促進金融中介發展,能夠加快城鎮化進程;反過來,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也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金融發展。關于新型城鎮化建設中金融困境的成因,邱俊杰和邱兆祥(2013)認為有三方面的內容:一是金融生態環境亞健康阻礙了城鎮化的高速發展;二是資源配置失衡削弱了金融支持城鎮化發展的效率;三是農村居民的自我排斥傾向進一步削弱了金融支持城鎮化建設的力度。因此,金融發展和金融創新對于城鎮化進程的支持是有限的,需要其他條件的支持。Kim,Kyung-Hwan(1997),認為依靠良好的金融創新、政府治理以及政治承諾,持續的城鎮化進程可以產生巨大財富,以改善所有收入群體的住房和基本服務需求。
本文試圖通過跨國實證分析,對城鎮化和金融杠桿(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討論。本文其余部分結構如下:第二部分,實證分析城鎮化對金融杠桿的動態影響;第三部分,結合實證結論對中國的情況進行討論;最后本文進行總結并提出政策建議。
二、 實證分析
1. 研究樣本和模型設定。根據樣本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包括了124個國家1983年~2012年的面板數據。從經濟總量來看,該樣本國家的GDP總量超過全球GDP總量的90%,因而可以視為一個在全球范圍內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樣本。
關于模型設定,根據研究目標,本部分主要考察城鎮化對金融杠桿的動態影響。考慮到金融杠桿的觀測值隨國家和時間而變化,通常存在一定的序列相關性,因此考慮到各變量之間的潛在內生性,本文采用動態面板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根據Aer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一階差分GMM估計量,設立金融杠桿與城鎮化之間的動態關系模型,如下回歸方程表示:
從理論上看,雖然一階差分GMM估計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兼顧金融杠桿通常存在的序列相關性以及相關變量之間的內生性,但是一階差分GMM估計方法有局限性,當被解釋變量滯后項的系數較大時,被解釋變量會出現強烈的序列相關性;當個體效應的波動遠大于誤差項的波動時,模型也會表現欠佳。因此,采用Arellano和Bover(1995)、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的系統GMM估計量,對方程(1)進行實證分析。系統GMM估計可以分為一步GMM估計和兩步GMM估計,一步估計使用傳統異方差-序列相關穩健型估計量來計算標準誤,兩步估計使用Windmeijer(2005)糾偏估計量來計算標準誤。在有限的樣本情況下,兩步估計比一步估計能夠更好的解決自相關與異方差問題。

由于GMM估計量的一致有效性的前提條件是誤差項不存在序列相關性和工具變量過度識別的問題。因此,需要對誤差項進行序列相關性檢驗和過度識別條件檢驗。根據Arellano和Bond(1991),誤差項的一階滯后由于初始誤差項經過差分處理后,即使初始誤差項序列無關,仍可能會出現序列相關情況,因此,誤差項的二階滯后必須不存在序列相關,而誤差項的一階滯后可以存在序列相關。Arellano和Bond(1991)建議使用兩步估計給出的Sargan統計量進行過度識別條件檢驗。當不能拒絕上述兩個檢驗時,說明誤差項不存在序列相關,并且GMM估計量是一致有效的,可以認為模型設定是正確的。
2. 變量選擇。在模型變量的選擇方面,金融杠桿的替代變量主要使用兩個基本指標:一是私人部門信貸/GDP(記為Private),一般認為為私營部門提供的應償還金融資源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通常具有更高的金融杠桿;二是M2/GDP(記為Mtwo),由于其反映了宏觀經濟的貨幣化程度,因而成為衡量一國金融杠桿水平的重要參考指標。將城鎮人口/總人口(記為Urban)作為城鎮化率替代變量的基本指標,該指標越大,通常一國的城鎮化率越高。
在控制變量的選擇方面,部分地參考過往文獻,主要納入了四個不同層面的影響因素:一是宏觀經濟變量,具體使用的控制變量包括人均GDP、按GDP平減指數衡量的年通貨膨脹率;二是產業資本結構變量,具體使用的控制變量包括工業增加值/GDP、服務等附加值/GDP、資本形成總額/GDP;三是金融環境變量,具體使用的控制變量包括:存款利率、存款保險、資本賬戶開放度指數;四是社會人口變量,具體使用的控制變量包括:移動蜂窩式無線通訊系統的電話租用率、人口年增長率。各主要變量的表示形式、經濟含義和數據來源如表1所示。
基于研究樣本的可獲得性,本文共選擇了124個主要國家和地區1983年~2012年的相關數據。
3. 城鎮化進程中的金融杠桿變化。根據方程(1),針對城鎮化對私人部門信貸的動態影響,進行系統GMM估計。當被解釋變量為私人部門信貸/GDP時,從估計結果可以發現,以城鎮化率(記為Urban)和城鎮化率的平方項(記為Urban2)為核心解釋變量進行估計,Urban呈現顯著正效應,Urban2呈現顯著負效應,模型整體呈現“倒U型”,拐點大致位于56%~63%之間,說明隨著城鎮化的推進,金融杠桿水平呈現遞增趨勢,當城鎮化率達到某一區間時出現拐點。在越過拐點之后,隨著城鎮化的繼續推進,金融杠桿水平開始出現下降趨勢。
從估計結果可以發現,對一國私人部門信貸/GDP均產生顯著影響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人均GDP(記為Lgdp)、資本形成總額/GDP(記為Capital)、存款利率(記為Deposit)、人口年增長率(記為Pgrowth)。結合各變量的系數符號,可以得到以下基本結論:(1)人均GDP越高,私人部門信貸/GDP越高,說明金融杠桿水平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上升而提高;(2)資本形成總額/GDP越高,私人部門信貸/GDP越高,說明金融杠桿水平會隨著宏觀資本結構的改變而同向變化;(3)存款利率越高,私人部門信貸/GDP越低,說明存款利率升高會降低金融杠桿水平;(4)人口的年增長率越高,私人部門信貸/GDP越高,說明人口增長對金融杠桿水平的提升有正向促進作用。

當被解釋變量為另一個杠桿指標即M2/GDP時,從估計結果同樣可以發現,以城鎮化率(記為Urban)和城鎮化率的平方項(記為Urban2)為核心解釋變量進行估計,模型整體依然呈現出“倒U型”關系,拐點區間位于60%~63%之間。
從控制變量來看,對一國M2/GDP產生顯著影響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按GDP平減指數衡量的年通貨膨脹率(記為Ginf)、工業增加值/GDP(記為Industry)、資本形成總額/GDP(記為Capital)、存款利率(記為Deposit)、人口年增長率(記為Pgrowth)。考慮各變量的系數符號,可以獲得以下基本結論:(1)通貨膨脹率越高,M2/GDP越低,說明通貨膨脹會對金融杠桿水平產生負效應;(2)工業增加值/GDP越高,M2/GDP越低,說明金融杠桿水平會隨著第二產業比重的提高而降低;(3)資本形成總額/GDP越高,M2/GDP越高,說明金融杠桿水平會隨著投資的增長而上升;(4)存款利率越高,私人部門信貸/GDP越低,說明利率上升會抑制金融杠桿水平;(5)人口的年增長率越高,私人部門信貸/GDP越高,說明人口增長對金融杠桿水平的上升有推動作用。
三、 對中國情況的應用分析
基于上述實證結論,參照拐點區間的平均值和上限,并根據最近5年中國城鎮化率的年均增速推算,預計中國的金融杠桿水平可能在2019年~2021年進入拐點區域,如圖1所示,此后隨著城鎮化率的上升,金融杠桿將出現下降趨勢。
四、 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基于124個國家1983年~2012年的動態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城鎮化和金融杠桿之間呈現出顯著的“倒U型”關系,當城鎮化率達到56%~63%時,私人部門信貸/GDP可能出現拐點;當城鎮化率達到60%~63%時,M2/GDP可能出現拐點。此外,發現人均GDP、資本形成率、人口增長率、社會發展水平越高,通貨膨脹、存款利率、第二產業比重越低,金融杠桿水平越高;反之,金融杠桿水平越低。
上述實證分析結論對中國城鎮化的推進、金融杠桿的管理具有比較明確的政策啟示。城鎮化發展對金融杠桿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隨著城鎮化的加速推進,金融領域也會得到快速發展,金融風險日益增加,亟需通過加強金融監管措施和改革,為城鎮化中的金融穩定健康發展保駕護航。然而,當城鎮化率達到56%~63%時,金融杠桿水平達到拐點,此后將隨著城鎮化率的增大而降低。此時,為彌補金融支持城鎮化的不足,政府部門要主動引導城鎮化進程中的投融資機制,進一步支持城鎮化的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 熊湘輝,徐璋勇.中國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金融支持影響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5,(6).
[2] 孫浦陽,武力超.金融發展與城市化:基于政府治理差異的視角[J].當代經濟科學,2011,(2).
[3] 榮晨,葛蓉.我國新型城鎮化的金融支持——基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經驗證據[J].財經科學,2015,(3).
[4] 邱俊杰,邱兆祥.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的金融困境及其突破[J].理論探索,2013,(4).
[5] Demirgü -Kunt, A., and E.Detragiache,C- 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ies of systemic bank distress: a survey,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2005,192(1):68-83.
[6] Kim, Kyung-Hwan, Housing finance and urban infrastructure finance, Urban Studies,1997,34(10):1597-1620.
[7] 賈洪文,胡殿萍.中國金融發展與城鎮化相關性——基于1991-2011年數據的實證分析[J].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13,(4).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我國金融風險管理和監管問題研究”(項目號:11JJD790009)。
作者簡介:李振(1989-),男,漢族,山東省濟寧市人,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博士生,重陽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全球金融治理;王曉煜(1992-),男,漢族,山西省晉中市人,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金融風險管理。
收稿日期:2016-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