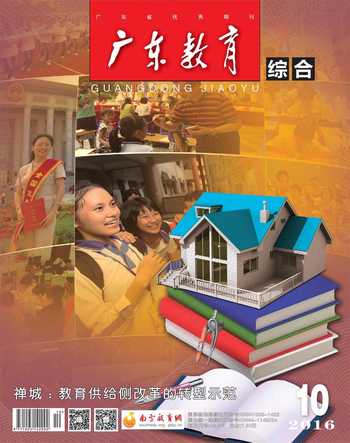敬畏課堂
楊正先
敬畏是一種價值追求,是一種人生態度,同時也是對人之所以為人的良知與德行的恪守。現代漢語詞典把“敬畏”解釋為“又敬重又畏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敬畏”是和“道德典范”聯系在一起的。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子所謂的“君子”就是有道德的人,“畏”就是敬畏,有道德的人是知道敬畏的。朱熹說:“君子之心,常懷敬畏。”溫家寶曾講過,天下之事成于懼而敗于忽,這里的“懼”就有敬畏的意思。馬云曾經感慨地說過,自己能走到今天,有兩點特別重要,一是感恩之心,二是敬畏之心。
教師的職業主陣地是課堂,實現人生價值的主要地方也是課堂。因此,敬畏課堂就是對職業的敬畏,這是教師最基本的職業道德。我們的前輩做出了光輝的榜樣。我大學的班主任彭允中教授是朱自清先生的得意門生,他在回憶自己的恩師時講過一件事:朱自清先生在西南聯大時,上課非常嚴肅認真,他總是把上課當成大事,再熟的內容課前都要重新準備,精心設計,還誠惶誠恐,生怕講不好。翻譯過《莎士比亞全集》的梁實秋先生盡管對莎士比亞的作品非常熟悉,但上課前還是要認真備課。一次,朋友問梁實秋:“你教了這么多年的英詩和莎士比亞,還要備課?”梁實秋回答:“這么多年,我上課前一晚都做準備,有時靠在椅子上,自個兒靜靜地想,說不定就會有新的了解,新的發現。”因為梁先生敬畏課堂,把課堂看得十分神圣。他認為在課堂上容不得馬虎,更不能應付,一旦上講臺,就要精彩的內容和飽滿的熱情,否則對不起學生和自己的名聲。北京大學著名教授、魯迅研究專家錢理群先生應邀回母校給學生講魯迅,為了三天的課,竟寫了七天教案,前后幾乎準備了一個多月,還擔心講不好,感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這些就是大師們的風范:謙虛、謹慎、敬業、認真,對課堂充滿敬畏。
敬畏課堂就是敬畏學生,尊重學生,對學生負責。一節課究竟講什么,怎么講,這是教師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前蘇聯著名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在《給教師的建議》講述了一件事:“一位有三十年教齡的歷史教師上了一節公開課……課上得非常出色,聽課的老師和視導員聽得入了迷,竟連做記錄也忘記了,完全被講課吸引住了。課后,鄰校的一位教師對這位教師說:‘您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傾注給自己的學生了。您的每一句話都具有巨大的感染力。不過,我想請教您,請問,您花了多少時間來備這堂課?歷史教師說:‘對這節課,我準備了一輩子。而且,總的來說,對每一節課,我都是用終身的時間來備課的……”這里的終身時間來備課,實際上指的是終身的讀書、學習,不斷地積累知識。這充分體現了這位老師的敬業精神。如果沒有對課堂的敬畏,這是難以想象的。
教師應該懷著對課堂的敬畏,以虔誠之心理,高度認真負責的態度,做好進入神圣的殿堂前的一切準備。首先,我們要明確教學目的。拿大學語文來講,教育部頒布的《大學語文教學大綱》明確指出:“充分發揮語文學科人文性和基礎性特點,適應當代人文學科與自然學科日益交叉滲透的發展趨勢,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養具有全面素質的高質量人才。”這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高素質人才的基本條件是專業知識和人文素質。因此,大學語文總的教學目的應該有兩個方面:一是培養和增強學生的語言使用能力,二是提高學生的人文修養。比如,余光中的《聽聽那冷雨》一文流露出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懷,備課時就要緊扣課文的關鍵語句深挖這方面的內容。文中的“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漢族的心靈他祖先的回憶和希望便有了寄托”,把漢字和的創造和使用漢字的民族歷史聯系起來。漢字是世界上最為獨特的文字,是華夏民族文明的見證,也是中華民族歷史的載體,融入了我們民族的血液,有著巨大的凝聚力。因此,“只要倉頡的靈感不滅,美麗的中文不老,那形象磁石般的向心力當必然長在。”在異國他鄉的中國人,不管來自哪個方言區,語言不通,民族不同,都可以憑著秀美如畫的方塊字找到自己的同胞,感受到祖國的溫暖。這些內容對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質是有意義的。
對講授同一門課程的教師來講,所講的內容總會有重復性。但我們千萬不要因為講過一遍甚至幾遍就掉以輕心,不再下功夫去鉆研。時代在前進,社會在發展,教師要與時俱進,不斷地學習新東西,同時,不斷地給我們所教授的內容注入新的東西,以適應時代的要求。如講授胡適的《容忍與自由》,就要結合現實,在引導學生辯證地理解“容忍與自由”的關系的同時,還可強調這兩者對建設和諧社會的意義。我到培正學院之后基本都是教大學語文課,應該說對所授的內容較為熟悉了,但每重講一遍都會有不同的體會,甚至同一學期上不同的班也會有不同的講法。因此,我的教案和課件常常處于修改中。對學科抱敬畏態度,對所講內容抱敬畏態度,對課堂抱敬畏態度,是一個合格的人民教師最基本的職業道德。
課堂是神圣的,不能容許任何有損于課堂的行為。對于教師來講,我們不僅自己要敬畏課堂,也要教育學生敬畏課堂。學生上課一定要心無旁騖,專心致志,認真聽講,做好筆記,而不能做其他的事情。然而,現在大學的課堂上,學生講小話、玩手機、干別的事情而不認真聽講等現象時有發生。對這些違反課堂紀律的現象,教師不能聽之任之、視而不見。一些教育發達的國家的做法值得借鑒,如英國議院通過了一條法規,大意是“允許教師在歷經勸告無效的情況下采取包括身體接觸在內的必要手段,迫使不遵守紀律的學生遵守紀律。”嚴格要求學生,是對學生負責的表現,同時也是課堂神圣性的體現。
敬畏課堂,凡是與課堂有關的事我們都要嚴肅對待,如教師的穿著儀表等。教師平時可以穿得隨便一些,但進入課堂就要穿著整潔,樸素大方。一次,著名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正在吃飯,學生登門求教。他說:“請您等一下!”說完,老先生放下碗筷,走到內室,出來時已把吃飯時穿的便裝換成了長袍。盡管面對的只是一個學生,但陳老在這些細節上仍是嚴格要求自己。20世紀80年代初,70多歲的林庚先生給學生“告別課”時,穿的是一身筆挺的衣服,滿頭銀發梳理得整整齊齊。我大學時的現代漢語教師馬忠(他主要是教授古漢語)是西南聯大時著名語言學家王力的同事,他每次上課都是穿著整潔的正裝,頭發梳得“一絲不茍”。半個世紀過去了,他上課的情景至今我還歷歷在目。此外,敬畏課堂還是一些細節的方面應該注意,如提前進教室,下課把黑板擦干凈,關閉多媒體設備和電扇、燈和門窗等。既然課堂是神圣的,那么這些看似“小事”的事也就不“小”了。
為人師表是教師的本分,也是教師應該具備的最基本的職業道德。教師對課堂的敬畏也會影響到學生對課堂的敬畏,是對學生最現實的教育。教師的言行舉止,教師嚴謹的教風和敬業的精神,會“潤物細無聲”地融入學生心靈,影響他們的學習乃至今后的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