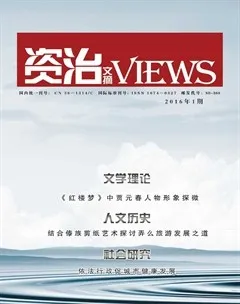淺析豪薩語歷史與現狀
【摘要】豪薩語是非洲三大語言(即北非的阿拉伯語、東非的斯瓦西里語、西非的豪薩語)之一。也是西部非洲地區主要民族語言之一。據不完全統計,使用豪薩語的約有6000萬人。主要流行于尼日利亞北部、尼日爾南部、乍得湖沿岸、喀麥隆北部、加納北部以及非洲薩瓦那地帶的西非其他各國。作為一門重要的商業用語,豪薩語并不被廣泛了解。本文就豪薩語的起源及在中國的傳播作一介紹。
【關鍵詞】豪薩語;歷史;現狀
一、“豪薩族”與“豪薩城邦”
“豪薩”(HAUSA)一詞由Hau和sa兩部分組成。“Hau”表示“騎”,“Sa”表示“牛”。因此,現在學術上比較傾向于關于豪薩人的起源是:豪薩人過去為游牧民族,而且常常帶著牛遷移,被稱為牛背上的民族。
公元前1000-1200年前后,豪薩族人陸續建立了一批小王國。位于中蘇丹西部,現今尼日利亞北部和尼日爾東南部的地區。這些城邦通常以其主要城市作為國名,各邦不相隸屬,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彼此之間常有戰事,只有在大敵當前才偶爾結成松散的聯盟。這些分散著的諸城邦,被稱作“豪薩蘭德”(Hausaland)也就是“豪薩地區”。關于豪薩地區的起源,有一個著名的傳說。相傳在道臘(Daura)城,有一口古井,井中盤踞著一條巨蛇,名叫Sarki(豪薩語“國王、酋長”之意),阻礙了居民的正常用水,百姓苦不堪言。一天,巴格達王子“巴耶杰達”(Bayajidda)勇士途徑此城,降服了巨蛇,為百姓除害。于是,道臘城的女王便與之成親。道臘女王與巴耶杰達誕下一子,取名為“蒙卡爾姆加里”即豪薩語“mun kamu jari”(我們占有城市)。他們的兒子又生了三對孿生子,后來分別成為卡諾(Kano)、道臘(Daura)、卡齊納(Katsina)、拉諾、戈比爾和扎扎烏——也稱作扎里亞(Zaria)城邦的始祖。“巴耶杰達”在前往道臘城之前,與博爾努的公主還誕有一子名叫“比拉姆”。這七個孩子分別成為所在七地的首領,形成了豪薩族的七個城邦,即“豪薩七邦”(Hausa Bakwai)。
“豪薩七邦”就這樣相互依存各自獨立地發展著。在傳說中,各城邦之間有明確分工,卡諾城和拉諾城專門負責染織,貿易主要集中在卡齊納和道臘城,戈比爾城負責保衛其它城市抵御外敵入侵,扎里亞則專門為其他各城邦提供奴隸,輸送勞力。最早分布在城邦內的是一個個小的農業村社,地位相當于現今的農村,豪薩語叫做“Kauye”(農村)。后來,各地出現了一些大的城市,豪薩語叫做“Gari”(城市),這些城市是類似國家的政治權利中心,有的在歷史中湮沒,有的存留下來成為未來國家的首府。
二、豪薩語的形成及轉變
到目前為止,豪薩語文字的起源尚無確切的考證。據現有的史料記載,最早的豪薩語在西非地區是以文學和商業的口頭用語形式被保存下來。直到伊斯蘭教的傳入,給豪薩語帶來的影響也慢慢地、平和地展現出來。
伊斯蘭教傳入豪薩地區是通過朝圣者、商人和馬拉姆(Malam)進行的。大約公元13世紀,隨著伊斯蘭教在豪薩地區的廣泛傳播,阿拉伯語中的許多詞匯也開始被豪薩人所采用。朝圣者為了成為一個虔誠的穆斯林,必須了解伊斯蘭教,并完成伊斯蘭教的各項功課。然而有關伊斯蘭教的各種詞匯,原來在豪薩語中并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自然而然,阿拉伯語中的宗教詞匯開始慢慢被豪薩穆斯林所借用,阿拉伯語中的宗教詞匯也開始慢慢進入到豪薩語中來。久而久之,這些阿拉伯語詞匯被豪薩人運用得習以為常,最后便成了豪薩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此同時,為了深入研究以及更好地傳播伊斯蘭教,許多有地位的豪薩人,如酋長、宗教領袖(Malam)等等,他們紛紛將自己的后代送到阿拉伯國家去留學深造。在那里,這些豪薩人又接觸了阿拉語中許多新鮮的政治詞匯,如議會、總理政治、共和國、世界等等。回國后,他們又將這些阿拉伯語中的政治詞匯不斷地運用到豪薩語中來。所以,直到現在,豪薩語中大量宗教及政治的詞匯,追根尋源都來源于阿拉伯語。這個時期的豪薩語是以阿拉伯文字形式存在,被稱為“阿賈米”(ajami)文字,此時文字記載的內容也大多是伊斯蘭教、法理以及詩歌。
三、豪薩語的近代發展
豪薩語涉及的國家眾多。但從“豪薩城邦”開始,使用豪薩語的地區大致為現今尼日利亞北部尼日爾東南部(原中蘇丹西部)。尼日利亞北部是豪薩族最早形成而且建立王國的地方。豪薩語是尼日利亞居第一位的民族語言。因此,本文以尼日利亞和尼日爾為例來探索和分析豪薩語的近代發展。
1900年1月1日,北尼日利亞總督英國委任盧加德勛爵為了有效統治北尼日利亞,一方面采取措施使當地的大小酋長能歸順他的統治,另一方面,他也積極招募當地人進入殖民政府工作。為使這些人學到西方的管理知識,盧加德勛爵在進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委派精通豪薩語的英藉德國人漢斯·菲舍爾創辦了第一所西式學校。目的是通過豪薩語教學,為當地培養新的師資力量,向酋長和他們的繼承者以及進入殖民政府部門工作的當地職員灌輸西方的行政管理知識。在這所學校里,豪薩語成為第一教學語言,而英語只是大家選修的一門外語。
由于當時豪薩語的教材極為短缺,在此情況下,1929年,英殖民政府在北尼利亞成立翻譯局。翻譯局成立的目的之一是將一些用英文和阿拉伯語編寫的教材譯成豪薩語,解決學校上課無教材、缺乏通俗出版物的問題。其二是編寫教科書。其三是幫助本國人自己出版小說等。翻譯局出版了很多書籍,其中絕大部分至今還有很高的使用價值,如《一千零一夜》、《豪薩人及其近鄰》、《古今故事傳》、《人類與世界》等等。1933年,翻譯局更名為尼日利亞國家文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委員會的工作重心也從原來的翻譯書籍轉到豪薩文的創作和出版上來。委員會約請本國人創作小說,并且給予很高的報酬,同時還開展創作競賽。這一措施引起了知識界的高度重視,他們紛紛向委員會投稿參加競賽。委員會的另一貢獻是發行了一份報紙,名為《尼日利亞北方報》,1933年改名為《真理報》(Gaskiya Ta Fi kwabo),用豪薩文、英文、阿拉伯文三種文字同時出版。該報紙一直發行至今,是尼日利亞豪薩文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該報紙用豪薩文刊登各種消息和評論,使它在讀者中有了很高的威望。
1953年,委員會改名為北方文化局(以下簡稱文化局)。主要任務是配合政府廣泛加強對成人教育、開展社會掃盲的需要。文化局不但出版了包括宗教、法律、科學、職業等內容的諸多小說還出版了包括《使女報》、《黎明報》在內的13種豪薩文報紙。文化局的成立以及鼓勵本國人積極創作的舉措,極大地促進了豪薩語語言的發展,擴大了豪薩語的傳播范圍。競賽中獲獎的作品也被編輯成書出版,成為現在研究豪薩民族文化的重要歷史依據。1945年,尼日利亞國家文學委員會在扎利里亞成立了真理出版公司,專門負責出版文學委員會編輯的大量書籍和報紙。
起初,尼日利亞北方政局對文化局特別重視,每年給予相當數量的資金幫助書籍出版,所以當時的豪薩文書報都可低價購買。到1959年,尼日利亞解放前,北方政局的重心轉移到政治運動上,對文化局的資金援助減少,經濟的困難,加上得不到政府的支持,文化局最終被迫解散。文化局雖然僅僅存在了30年,但它為發展豪薩語言文字以及掃盲工作中作出了巨大貢獻。
四、豪薩語在中國的傳播
中國與非洲的友誼源遠流長,基礎堅實。中國與非洲大陸有著相似的歷史遭遇。在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中始終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大批亞非國家相繼獨立。為發展中國與亞非國家的友好關系,周恩來總理從我國外交工作的長遠利益出發,指出在與亞非各國人民的交往中,為了尊重重新獲得獨立的亞非國家人民的民族感情,一定要重視非洲本民族的語言。1963年6月1日,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豪薩語廣播正式開播,每天向非洲播出節目3次,每次半小時,內容涉及中國政治、文化、經濟、社會等方面。在此背景下,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開始設置亞非語言專業。1964年成立了豪薩語專業。1965年,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也開設了豪薩語專業和祖魯語專業。豪薩語專業成立之初,生源都來自于其他語言專業的學生。北京外國語學院第一批豪薩語學生是從該校法語系遴選的政治和業務方面比較優秀的本科生。老師則聘請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國際部的尼日爾籍專家。通過法語教授豪薩語,查閱豪·法、豪·英詞典的形式進行教學。教學過程中,外籍專家還不時輔以肢體語言,來補充法語教學中難以意會的內容。北京廣播學院第一批豪薩語專業學生也是從其他專業的優秀本科生中選拔而來,白天他們跟著外籍專家學習豪薩語,晚上就趕到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播音,做節目。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培養出了程汝祥、王正龍等早期的豪薩語專業學生。后來成為中國國內豪薩語教學的優秀師資力量。程汝祥編寫的《簡明豪薩語語法》、王正龍和后來豪薩語專業的學生牛家昌編寫的《豪薩語》教材4冊,至今仍是豪薩語專業本科生的指定教材。
2000年10月以來,隨著中非政治和經貿關系的快速發展,國際媒體、西方智庫,以及學術界有關中非關系的報道和討論急劇升溫,中非關系迅速成為“顯學”。豪薩語等非洲本土語言的教學又開始被關注和重視。2000年,教育部設立了7個包括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中國傳媒大學在內的“國家外語非通用語本科人才培養基地”。豪薩語專業再次被納入高校招生計劃。而此時的師資和生源都有了明顯改善。目前,北京外國語大學仍然開設豪薩語本科課程。每四年或八年招生一次。
結語
在尼日利亞和尼日爾,豪薩語是法定官方語言。但在實際運用中,除了本民族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豪薩語外,幾乎所有官方文件,所有正式場合或者聚會,人們已經習慣使用英語或法語。使豪薩語的發展受到限制,語言詞匯得不到擴展,涉及當代科技發展的最新科技詞匯,豪薩語大部分需要英譯。作為非洲本土語言之一,豪薩語是西非地區豪薩民族文化的載體,這門語言應當得到更大的關注和重視,在尼日利亞民族構建中發揮它的作用。
注釋:陳利民:《騎在牛背上的民族語言——豪薩語》,《國際廣播》2002年3月陳紱:《豪薩城邦》載《西亞非洲》(雙月刊),1987年第2期Malam:豪薩語,意為“長者,老師”。也可以指在某個領域有突出地位的人。——譯者注黃澤全、董洪元:《豪薩語和豪薩文的發展演變》,載《西亞非洲》(雙月刊)1984年第3期孫曉萌:《中國的非洲本土語言教學五十年——使命與挑戰》,載《西亞非洲》2010年第5期同上孫曉萌:《中國的非洲本土語言教學五十年——使命與挑戰》,載《西亞非洲》2010年第5期祖魯語(Zulu),是南非第一大民族語言,屬尼日爾-剛果語系大西洋-剛果語族班圖語支,是南非最大的民族語言。——作者注孫曉萌:《中國的非洲本土語言教學五十年——使命與挑戰》,載《西亞非洲》2010年第5期
【參考文獻】
[1]賀文萍.《推倒高墻:論中非關系中的軟實力建設》[J].《西亞非洲》2009年第7期
[2]劉鴻武.《從部族社會到民族國家——尼日利亞國家發展史綱》[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0.3
[3]牛佳昌、王正龍.《豪薩語》[M].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作者簡介:武卉(1986—),女,浙江金華人,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研究實習員,豪薩語學士,非洲學碩士在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