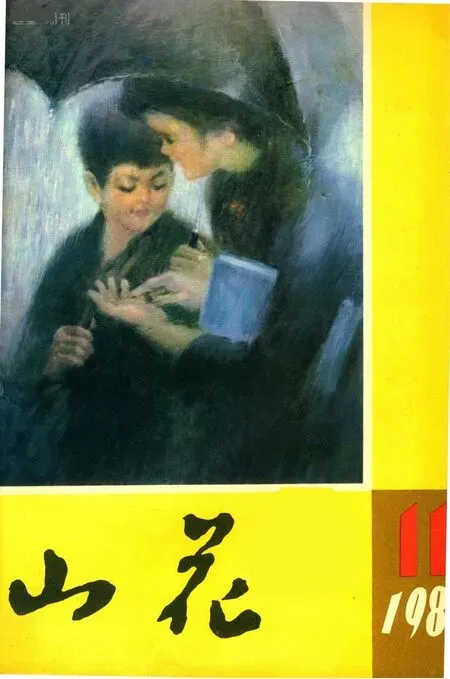和巴特勒先生見面
甫躍輝
第一次見到巴特勒先生,是8月12日,思南公館的講座。我坐第二排,身后是烏泱烏泱的人群。那時,巴特勒先生唯一翻譯成中文的小說集《奇山飄香》還沒幾個人看到,那么多人,大概是沖著“美國的創意寫作課程”這個講座題目來的吧?
在很大程度上,我也是沖著這題目來的。四年前,我從復旦大學首屆文學寫作專業畢業,不少媒體報道,很多都抱了質疑的態度。有一家媒體,時隔兩年再采訪我,仍然問,作家可以教嗎?我有些生氣,說這問題不是兩年前就問過了嗎?請問物理學家可以教嗎?化學家可以教嗎?這些“家”似乎都不是教出來的,但并不妨礙學校教物理教化學啊。同樣的道理,作家不是教出來的,但并不妨礙學校教寫作啊。后來,我開始思考,為什么我們談到寫作,那么抵觸“教”?我們為什么把寫作看得如此神秘莫測?
8月15日早上,我在華亭賓館和巴特勒先生會面,一開始就和他聊到這個。
說來也巧,那天在賓館里,很偶然地,遇到在二樓走道邊沙發上休息的巴特勒先生。他一個人坐在那兒,望著樓下大廳來往的人。我愣了一下,還沒到約定的時間,要不要上去跟他打招呼?最后,我還是硬著頭皮走上去,和他聊了幾句。他很驚訝,微笑著聽我的半吊子英語,給我隨身攜帶的《奇山飄香》簽名,認真簽下我的名字和日期。
有這鋪墊,當翻譯到來后,我們聊起來就很隨意了。
關于創意寫作課,他在講座中就說過:“創意寫作課程的確會教授寫作方面的一些小技巧,但創意寫作不能教出天才,而是教學生如何感受或者體會寫作的過程,引導人們審視自己的內心,傾聽自己的內心,選擇正確的創作路徑,盡量少走彎路。藝術來自你內心的真正想法,你可以擁有天賦,可以擁有寫作技巧,但是如果不認真思考,你永遠不會誕生偉大的作品,就像中國有句話叫做‘學而不思則罔’。”
在聊天中,巴特勒再次強調:智慧是不能夠被教授的,它需要領悟,一樣這個領悟,他作為寫作學教授,只能教授一個人如何去領悟。而寫作更重要的還在于,得有這個“智慧”,不然,空有領悟的辦法,也只能徒呼奈何。
問題在于,有沒有這個“智慧”是誰也不知道的,每個寫作者所能做的,只能是努力去找到打開智慧閥門的鑰匙。這把鑰匙長什么樣呢?通過和巴特勒先生聊天,我為這把神秘的“鑰匙”歸納出這么幾個特點:
首先,是看見,或者說觀察。
巴特勒先生說,“觀察細節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當你讀完一部小說以后,它應該像一部電影一樣呈現在你腦袋之中。”這是他第二次到中國(第一次去的天津),第一次到上海,他說,一到上海,他就注意觀察上海的行道樹是什么。而這正是我長久以來的習慣。
巴特勒先生如此有意地觀察細節,在越南時期就開始了。
《奇山飄香》這本小說集里的故事都是關于越南的。全書十七個小說,多數小說使用的都是第一人稱敘述。每一個“我”都是不同的越南人。巴特勒先生說,他最初出版這本書的時候,書里沒有他的照片的,之后的二十多年,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一個美國人,都以為他是越南人,人們知道他是美國人后,都非常非常吃驚。由此可見,他對越南人和越南生活的逼真、深刻的敘述。之所以有這樣的效果,小說里展現出來的豐沛細節至關重要。
巴特勒先生告訴我,到越南之前,對他來說,越南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他對越南所有的了解,都來自戰爭。戰爭開始之前,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越南只是一個法國殖民地。在他去參加戰爭前,部隊把他送去語言學校學了一年越南語,當他第一天來到越南,他已經可以說很流利的越南語了。在戰爭中,他做的最長時間的工作就是翻譯,先是為美國的外交部做翻譯,然后是到胡志明市。他盡可能地與越南當地的人打交道,想融入他們,了解他們。他發現,越南人是很熱情好客的,他不僅學習到了越南的文化,也看到了越南人的內心。這在很大程度上,使他走上了寫作的道路。
去越南之前,巴特勒讀的是戲劇研究生。那時候,他只想做一個戲劇家。在他看來,戲劇的寫作只是做一些人物的對話,讓這一切呈現在戲劇的舞臺上,而越南的這段經歷,讓他想把戲劇轉化成小說,“因為小說是創造整個世界的,而戲劇只是在舞臺上的表演。”
在越南期間,巴特勒就很有意地觀察細節,并且做了很詳細的筆記。越南戰爭結束后,他還曾四次回到越南。每一次,都會讓他看到新的細節。
他把這些細節的記憶分成兩大類,一個是“事實記憶”,一個是“感官記憶”。巴特勒認為,他寫的多半是感官方面的記憶,他并不是很擅長于真正的事實上的記憶。
其次,是準確,或者說不帶偏見。
我問巴特勒先生,他寫作《奇山飄香》的時候有沒有帶有某種偏見呢?比如說政治偏見。這些會不會影響到《奇山飄香》的創作。巴特勒先生對這一問題沒有回避,他認為,他寫這本書的時候,并沒帶有任何偏見。但他似乎又不是那么肯定,他說,就算有偏見,這種偏見可能是來自于文章作者“我”本身的偏見,“這種偏見是作為一個人類的正常的偏見,比如說情感上的偏見,但它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個整體,而這個整體就是人類體驗的中心的偏見。”
或許,正是這種不帶偏見的態度,讓巴特勒得以融入越南社會,對越南有如此多的了解。越南不少地方有著東方式的鬼怪傳說。《奇山飄香》中的《鬼故事》就很像《聊齋》中的某些篇目。談及此,巴特勒先生給我講了他在越南的一件真實遭際——他一再強調這事兒是真實的。他說,他在越南的時候,胡志明市的很多人都相信鬼的世界離他們是非常近的。他曾住在一間非常大的房子里面,那房子是1836年建的。每天晚上,都會有個鬼敲他的門。這不是您在做夢吧?我問他。巴特勒先生很認真地說,他把門打開了,看到屋里的東西在移動!這讓我想到《奇山飄香》中與書名相同的那篇小說。
敘述者是個快要過世的老人,他不斷看到早已過世的朋友胡志明來訪。胡志明似乎是在夢中,又似乎是真實的。巴特勒先生說,他的很多鬼故事都是從越南人那聽來的,而我所說的這篇小說中的胡志明是他的想象,他并不需要人們去判斷這個鬼是不是真的,這個小說里面的主人公,他所學到的生活中的課程才是最重要的事。
進而,我問巴特勒先生,《奇山飄香》十七篇小說里的多數人物是越南人,多數都是第一人稱敘述,您作為一個美國人,真的能確定“我”知道越南人是怎么想的嗎?
巴特勒先生稍微猶豫了一下,說,當你了解得夠多,寫得夠多,你最終會把這些經驗輸送到你的潛意識里面,當你的潛意識已經足夠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你就可以把這個人物的形象給它創造出來。此外,不管是關于性別也好、種族也好、信仰也好、文化也好、政治也好,都不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所有我們共同分享的意識,人類的意識。
最后,是遺忘,或者說貫通。
我在復旦讀文學寫作專業研究生時,上過美國寫作學教授開的課。那位教授叫做約翰·舒爾茨,他是哥倫比亞藝術學院的教授,他是中國作家嚴歌苓的寫作老師。我聽他講了十六節寫作課,在他的指導下,我寫了不少東西,當然,用的都是很簡單的英語。課程結束后,我把其中一篇翻譯并改寫成了短篇小說《初歲》,后來,這小說收錄進了我出版的第一本書《少年游》里。那段經歷,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事實上,巴特勒先生強調的很多寫作理念和舒爾茨教授所說的很像。我第一次讀到理查德·耶茨的小說集《十一種孤獨》,非常驚訝,覺得那個寫作方式太像舒爾茨教授教的了。查了一下理查德·耶茨的簡歷,才知道他上過美國的寫作課……這挺讓我擔心。
我把我的擔憂告訴了巴特勒先生:這樣一種寫作方式,這樣一種感知世界的方式,會不會讓寫作變得模式化呢?
巴特勒也認為,這是件危險的事,“因為在寫作的這個課程里面,他們會創作一種像方程式然后讓人去跟隨它,但這背離了寫作的初衷,寫作應該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流露方式。”怎么解決呢?巴特勒先生,他在講座里就提到過:小說家記憶力是最不好的。所以他覺得,寫作學課程教給的方式是好的,但當你學到后,要把它忘記,然后把它丟到垃圾箱里,讓所有技巧成為一個整體,把它徹底變成自己的東西,在寫作中,讓這一切自然而然地流露。
這正如莊子所說:“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
一個半小時過去了,要和巴特勒先生告別了。很多年以后,我仍然會記得這次會面吧。它讓我對寫作有了更多的認知,有了更多的信心,我會記住巴特勒先生在講座上講過的一句話:“一個作家在寫作時不應該過多擔憂作品將來的命運,有多少銷量,被多少人接受。假如我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幸存的人,照樣會寫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