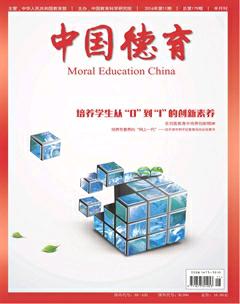老子的反向思維
老子的反向思維對后人影響很大。老子認為,事物均由正反兩方構成,正反兩方相反相成,形成一個既對立又統一的矛盾體。在此基礎上,老子進一步認為,正反兩方是相通的,事物的發展都是從一個方向向另一個方向轉化,卑小總會走向高大、柔弱總會走向雄強、生命總會走向死亡,反過來,就是新的一次輪回和轉化。
《老子》中,隨處可見這種思維,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強梁者不得其死”“勇于敢則殺”“堅強者死之徒”“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老子看穿了事物必將走向反面的不可逆性,積極利用物極必反的原理,將反向的視野和思路發揮到極致,以反求正,力圖使自身在萬物輪轉之中永遠立于不敗不衰之地,這就是老子遠遠高明于同時代其他哲學家之所在,也是他辯證思維的精髓所在。
反向思維在于主動地預見矛盾發展的方向,做矛盾的主人,而不是矛盾的奴隸,被動地等待矛盾發展的結果。最好的例子就是欲擒故縱之術,“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這種反向思維在《老子》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這里大致將其分為八種類型。
第一,守雌。我們說,老子是很喜歡女性的。“雌”代表柔和、讓步,代表寬容、慈愛。在《老子》第二十八章講“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雌雄各有各的作用,“雄”往往以力量取勝,“雌”則以柔、以靜來保身。一般人往往被雄強所吸引,不知道雌柔力量更大。老子希望人不要過度示強,這樣就會過早、過快走向終點。六十一章有“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天下之牝”是講希望大國扮演女性的角色,“牝常以靜勝牡”是講雌性能夠以她的安靜征服雄強。這是希望天下的人能夠寬容、慈愛。
第二,處下。《老子》六十六章有“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為什么江海能夠成為百谷之王呢?就是因為它甘居下游。如果統治者想要統治人民,就要向人民示弱、示卑,一定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人民之后,讓人民不感到有壓力,這樣人民才愿意臣服于你。《老子》中的“上德若谷”“為天下溪”也是這個意思。
第三,謙卑。說的是統治者如果想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必須忍辱負重,經得起挫折,經得起卑辱。《老子》三十九章有“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榖,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這就解答了一個現象,君主稱自己“朕”是秦以后的事,先秦時期都稱自己為“孤”“寡人”“不榖”,而這些詞都不是褒義詞。這就是刻意降低身段,謙卑示人。同時,作為一個謙卑者,你就可以看淡一切,寵辱不驚。十三章有“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老子看不上那些稍微有點得,就驚喜,稍微有點失,就驚慌失措、郁郁寡歡的人。這些人把虛榮看得太重,患得患失。所以要寵辱不驚。
第四,不爭。這個詞在《老子》中出現率很高。“爭”一般和災禍聯系在一起,所以老子講要不走極端,要留有余地,不爭才能避免災禍。第八章有“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樣,幫助萬物卻不與萬物爭勝,這是水的特性。八十一章有“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天之道是利人而不是害人,圣人之道,雖然有所作為卻不與人相爭。這就是老子所講的“無為”。“無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通過不爭來體現。六十三章講的“報怨以德”就是老子“不爭”的極致。如果一個人能夠忍受常人難以忍受的委屈,那他一定會有大的成就。
第五,知足。四十四章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人懂得知足,就不會有屈辱;懂得休止,就不會有危險,懂得適可而止,才能夠長久。相反,四十六章說“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最大的災禍是人的不知足,沒有比貪得無厭更大的罪過了;人只有懂得了滿足,才有永遠的富足。
第六,退身。第九章有“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這就是我們常講的功成身退。與其竭力保持盈滿,保持旺盛,不如早點放棄;與其抓住不放,追求圓滿,不如早些罷手。打磨得很鋒利的兵器容易被折斷,不能長久保持;家里面金玉滿堂,沒有誰能守得住;富貴驕橫,必然自取其禍。功成而不居,退回所有的名利,這符合天道的行為方式。
第七,守柔。七十八章有“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天下沒有比水更柔弱的東西,但在戰勝剛強的事物時,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比得上水,比如“水滴石穿”。做人如果能夠像水一樣的柔弱、卑下,甘于寂寞,甘于屈辱,但同時充滿生命力,就能遠離腐朽,遠離污染,無往而不勝。
以上這些特征,和“道”虛無的性質正相吻合。“道”之所以具有創造性,正是來源于其虛無、空靈、不盈,因而能夠不窒息、不阻塞,永遠創生出新的東西。與之相應,人也應該像“道”那樣,使自己永遠處于新生的、弱小的、生動的、充滿活力的一面。
第八,為之于未有。這時,老子就進入了無形的境界。他很講究用“無形”來把握“有形”,用“無名”來把握“有名”,用“未然”來把握“已然”,用“未有”來把握“有”。六十三章有“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是以圣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難做的事情,要從容易做的事情開始做起,大事要從小事做起,圣人始終在做小事,在做容易做的、瑣碎的事情,結果圣人反而能成就大事。六十四章有“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事物還安定的時候比較容易掌握,問題還沒有出現苗頭的時候,比較容易有對策;事物在比較脆弱的時候,問題容易化解,事物在微小的時候,矛盾容易消散。總之,事情在還沒有發生,矛盾還沒有出現之前,我們就要設法去解決它、處理它。所以,老子希望人們善于觀察、把握事物發展的征兆,要防微杜漸、居安思危,這樣才能夠避免招致更大的災禍。
從《老子》中可以找到大量的否定式說法,如不爭、不言、不美、不為、不武、不怒、不尚賢、無心、無知、無欲、無身、無事、勿驕、勿強、勿伐等等數十種,這些說法幾乎都指向老子的反向思維,以各種各樣的否定方式,體現出老子獨特的思維法則和行動法則。二十二章云“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說的是不依賴自己的見解,不拘泥于自己的視野,反而看得更分明;不自以為是,反而是非昭彰;不自我夸耀,反而能建功立業;不驕傲自滿,反而能成為領袖。否定“自見”,得到“明”,否定“自是”,得到“彰”,否定“自伐”,得到“功”,否定“自矜”,得到“長”。老子思維的高妙之處就在于是一種辯證思維,是一種否定之否定,最終要推向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發展階段,這個更高的階段就是“無不為”。所以我們講“無為”否定了“為”,“無不為”又否定了“無為”,“無不為”其實就是否定之否定。“無為而無不為”在《老子》中反復出現,但有時候調換表達方式,如第三章有類似的說法,即“為無為,則無不治。”
老子有時是一個冷酷的或悠閑的旁觀者,而有時又是一個真正的參與者,一個真正的高手。老子并非消極、退隱,而是與之相反,積極、進取。只不過不是單向的、直線的進取,而是迂回、漸進、不張揚、不過分的進取。表面的被動和消極,其實是為了爭取更大的主動和更好的效果。老子的反向思維運用得好,小可以消極避禍、明哲保身,大可以有所作為、建功立業。
總之,老子說“無”是為了說“有”,談“一”是為了談“多”,講“虛”是為了講“實”,談“無名”是為了落實到“有名”,講“無形”是為了引申到“有形”,闡發“柔弱”是為了戰勝“剛強”,倡揚“無為”是為了達到“無不為”,這也是老子反向思維流傳至今的原因。
【曹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張 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