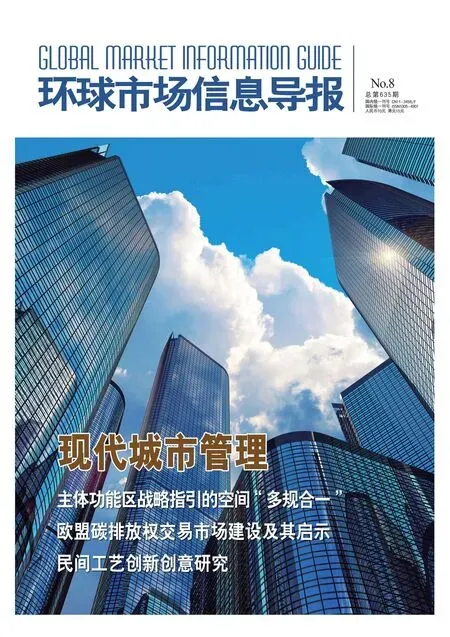夜讀札記
■文亦鳴/文
?
夜讀札記
■文亦鳴/文
“及第”和“落地”
晉代陳壽說:“讀書百遍,其義自見。”這是強調多讀書便于理解。唐代韓愈說:“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這是強調讀書要勤于思考。宋代陸游說:“讀書不放一字過,閉戶忽驚雙鬢秋。”這是強調讀書要認真。清代袁枚說:“讀書好處心先覺,立意深時道已傳。”這是強調讀書的收獲是在無意中增進的。清人說:“讀書猶樹木,不可求驟長。”這是強調讀書是一種知識的積累。
在科舉時代,大多數人讀書的目的是做官。一旦考中,所謂“進士及第”,就有了做官的資格。因此,“及第”兩字,是當時許多讀書人夢寐以求的。有這么一個笑話——
有個讀書人帶著書童,千里迢迢進京趕考。有一天,這位讀書人的帽子被風吹落于地,走在他身后的書童見此情景,大聲嚷道:“老爺,您的帽子落地了。”讀書人聽了很不開心,斥責道:“你以后再也不準對我說‘落第(地)’,說‘及地(第)’多好啊!”書童恍然大悟,責怪自己沒知識,不會說話。過了一會兒,書童即對主人道:“老爺,小的已將您的帽子縛好,永遠不會及地了!”這讀書人氣得怒火中燒,氣得不知說什么好。

上面說的只是一個笑話,并非實有其事。但在現實生活中,“落第”也好,“及第”也罷,絕不是討個口彩或避個忌諱那么簡單。不通過刻苦努力,就難免“落第”;認真讀書學習,就有可能“及第”。科舉時代的考試是如此,現代的考試又何嘗不是如此?當然,今天的讀書人,奮斗目標未必淺薄得只是為了做官,但無論干哪一行,哪一業,要想做出成績來,都必須掌握豐富的知識,否則怎么可能“行行出狀元”?
“讀書”與“下筆”
杜甫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因此,有人文章寫不出,總以為是自己書讀得太少,于是又去大批買書,埋頭硬啃。其實,這些人并沒有真正理解杜甫這兩句詩的意思。
所謂“讀書破萬卷”,無非就是要博覽群書,知識面開闊些。但是讀得多,并不等于就是“破”,如果只是圍著書本打轉,沒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和深入思考,哪怕讀得再多,也沒有用,根本談不上“破”。所以,“破萬卷”者,就是要能吸收,且要有自己的見解。
古代的一些收藏家、藏書家,雖家中蓄書無數,但真正成為有影響、有成就的思想家或文學家的,卻是寥寥無幾;相反,許多終身落魄,顛沛流離家不蓄書的人,因為曾經讀過那么一些書,卻都還能寫出一些東西來。
西漢文學家司馬相如去世后,漢景帝以為他家中一定藏有不少奇書珍籍,派人前去索取,結果一去,他妻子卓文君說他一本藏書也沒有,只有自己寫的一些文稿。東漢著名的唯物主義哲學家王充,《后漢書》說他“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直到晚年,他才退居鄉間潛心著書,寫了《論衡》八十五篇。明初前七子之一的徐禎卿,《明史》也記載他“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其詩“煉精警,為吳中詩人之冠,年雖不永,名滿士林。”
由此可見,作文的高下,雖與讀書有關,卻不在看書或藏書的多少,主要還在于對書的消化、吸收、見解的深淺和實際的運用上。
差別在于5%
曾經向幾位博覽群書的師友請教,讀書有何經驗?他們幾乎一致認為上下聯系、融會貫通是最重要的,也幾乎一致不承認自己的記憶力比一般人好。
這就怪了,我的讀書方法也跟他們差不多,為什么就不一樣呢?難道是自己不夠用心?
仔細想想,用心真的很重要。曾聽人說過一個小故事:有一天年輕的曾國藩在家讀書,反復對一篇文章高聲朗讀了不知道多少遍,很長時間還是沒能背下來。這時,他家進了一個賊,潛伏在屋檐下,希望等讀書人睡覺之后,可以入室行竊。可是在屋檐下等啊等,那曾國藩一點沒有睡覺的意思,只是聽見他翻來覆去地讀那篇文章。這賊實在等得不耐煩了,于是破門而入,指著曾國藩怒罵道:“你這么笨的人,還讀個什么書啊!”說完之后,他將那篇文章一字不漏地背誦了一遍,然后揚長而去。

這個賊的確很聰明,至少比曾國藩要聰明很多,但為什么這么“笨”的曾國藩,后來卻成為扶危救難的中興名臣、海納百川的一代儒宗呢?是否就是因為他讀得慢、特用心呢?他有兩句名言:“唯天下至誠能治天下至偽,唯天下至拙能勝天下至巧。”想想他的“笨”,信然。
不少人讀書,雖說融會了,但一直沒有貫通,讀到哪算哪。所以文章往往“言之成理而未徹,持之有故而未周”,且缺乏文思。《文心雕龍》稱之為“神思”的:“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然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讀書光是融會還是不夠,只有貫通了,才能神與物游,心為所動,情為所感,自是扣人心弦,才可能寫出自己獨特的文之思。
臺灣作家林清玄說:“百貨公司的香水,95%都是水,只有5%不同,那是各家秘方。人也是這樣,作為95%的東西其實是很像的,比較起來差別就是其中關鍵的5%。”也許,我們跟學富五車的學者的差別就在于這5%。而這5%就是讀書的用心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