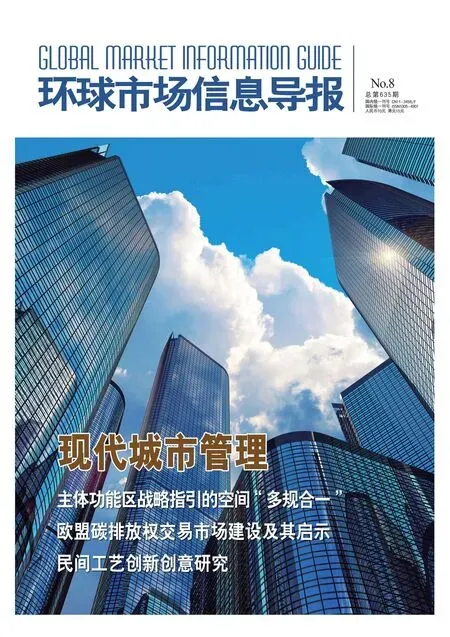請(qǐng)舍本逐末者戒
■劉 亭/文
?
請(qǐng)舍本逐末者戒
■劉 亭/文
越來越喜歡讀陸銘老師的博客了。
作為一個(gè)城市化研究的愛好者,不但早前讀過陸老師的文章,去年還有幸作為他新書《大國大城》推介會(huì)的點(diǎn)評(píng)嘉賓,和他有過一番當(dāng)面的交流。當(dāng)時(shí)給我留下的印象就是,此人之見地好生了得,句句咬木頭,一針便見血。
這不,在本月初見諸于財(cái)新網(wǎng)的《為留守兒童及其父母說幾句話》,就是這樣一篇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的好文章,實(shí)在值得那些舍本逐末的主事者們拿來認(rèn)真一讀。
事情是由國務(wù)院近期發(fā)布的《關(guān)于加強(qiáng)農(nóng)村留守兒童關(guān)愛保護(hù)工作的意見》引起的。我們當(dāng)然不會(huì)懷疑政府的好意和善心,也知道這件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這種文件多半是為了回應(yīng)公眾的關(guān)切,也只能是一個(gè)治標(biāo)不治本的“表態(tài)”。但是,如果追溯起來,自從上世紀(jì)九十年代民工潮破閘而出,本世紀(jì)初國家將城鎮(zhèn)化寫入“十五”計(jì)劃,特別是2013年黨中央專門召開“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zhèn)化工作會(huì)議以后,算算都已經(jīng)有幾十年時(shí)間過去了,何以就連這么一個(gè)小小的問題都解決不了?乃至延宕今天,還以如此一份連“亡羊補(bǔ)牢”都?jí)虿簧系奈募袚u過市?
于是,真的要信服春秋時(shí)的魯國鄉(xiāng)民曹劌說過一句穿越了兩千多年的時(shí)空,至今仍然余音裊裊的話:“肉食者鄙,未能遠(yuǎn)謀!”
關(guān)于城市化,總書記曾講過一句堪稱經(jīng)典的話,說它是一個(gè)“自然歷史的過程”。何謂自然?那就是“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逐利使然也;何謂歷史?那就是“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要循序漸進(jìn)。本來民工潮蓬勃興起是一件好事,大可以促成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下歷來種種反城市化的政策改弦更張。卻不料只來了一個(gè)“允許進(jìn)城打工”的態(tài)度,也就算完事大吉了。這說明了什么呢?說明政策制定者根本就沒有把這件事看作是一個(gè)規(guī)律的表達(dá),因而需要自覺地去順應(yīng)它,努力成其好事;也完全沒有把“人的城市化”當(dāng)作事物的本質(zhì),因而要以戶籍、土地和社保的相應(yīng)改革去配套,以求真正落實(shí)“以人為本”。
以后的演變,在實(shí)際生活中就完全變成為另外的一回事:農(nóng)民工是最便宜、最合算的勞動(dòng)力,不但同工可以不同酬,無需付給城里人相應(yīng)的工資收入;就連他們的教育、醫(yī)療、文化和居住等公共服務(wù)的開銷,也都是可以大打折扣甚至分文不付。于是,政府相應(yīng)的一系列“關(guān)愛保護(hù)”農(nóng)民工的政策文件出臺(tái)了,總理為農(nóng)民工討薪的事件,也傳為公眾津津樂道的佳話美談。記得當(dāng)時(shí)我曾撰文發(fā)問,如此這般把農(nóng)民工當(dāng)回事,難道我們真的要喊出“農(nóng)民工萬歲”?
這一質(zhì)疑,其實(shí)和陸老師文中的觀點(diǎn)是相通的:種種有失公平、令人不齒的社會(huì)現(xiàn)象,固然需要憐憫和救助,政府對(duì)此也無可推脫。但在討論相關(guān)問題的時(shí)候,“先要從政策和制度的背景來理清……問題產(chǎn)生的根本原因”。若是今天“留守兒童”,明天“空巢老人”,后天“臨時(shí)夫妻”,每天出個(gè)相應(yīng)加以“關(guān)愛保護(hù)”的文件,那我們的政府,是不是僅僅只有一個(gè)民政部門、而民政部門只有一個(gè)社會(huì)救助職能呢?這樣一來,干脆將政府改成“慈善總會(huì)”豈不是更好?
“好行小惠、言不及義”——這樣的“公器”,畢竟也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成不了什么大事的。在我來看,留守兒童不過是整個(gè)農(nóng)民工政策的一個(gè)組成。若是能從“政策和制度背景”來消滅“農(nóng)民工”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根源,“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那留守兒童問題難道還會(huì)是一個(gè)問題嗎?
繞開天底下的常識(shí)和經(jīng)驗(yàn),總是以所謂的“中國國情”做為擋箭牌,把一件本屬“天經(jīng)地義的事情”變得磨磨唧唧,又唧唧歪歪,這就是我們一些同志的本事。總書記強(qiáng)調(diào)“尊重城市發(fā)展規(guī)律”,其實(shí)就是告誡我們不要和規(guī)律對(duì)著干。明明是大多數(shù)農(nóng)村人口必然要隨著城市化進(jìn)程到城里穩(wěn)定地工作和生活,那我們?yōu)槭裁淳筒荒茏屴r(nóng)民家庭進(jìn)城變成一件順順當(dāng)當(dāng)?shù)暮檬履兀坎皇沁@頭土地的權(quán)益不能流轉(zhuǎn)、不能變現(xiàn),逼得農(nóng)民必須把根留住;就是那頭三等公民、門檻高筑,又逼得農(nóng)民實(shí)在難以扎根。無非一個(gè)是土地收益的確權(quán)和活化,另一個(gè)是基本公共服務(wù)的均等和共享,“從政策和制度”的層面真正辦成這兩件事,其它的事情,我看都好辦,亦均可由農(nóng)民自主選擇并經(jīng)由市場機(jī)制來完成。
外推的城市化似乎體現(xiàn)了政府的關(guān)愛和保護(hù),但這不過是類似當(dāng)年政府對(duì)國企的“父愛主義”,其結(jié)果總是事與愿違、適得其反。既然關(guān)于留守兒童的決策,都是每一個(gè)農(nóng)民工家庭,在統(tǒng)一的既定制度和政策背景下,基于各種利弊得失反復(fù)權(quán)衡得出的結(jié)果,那政府的責(zé)任,就是把那種作為“公器”無可推卸、也是無可替代的制度和政策調(diào)整到位。“人隨王法草隨風(fēng)”,隨后農(nóng)民自會(huì)作出理性的分散決策。
留守兒童的事是如此,其它有關(guān)農(nóng)民工和城市化的事都是如此,為此請(qǐng)舍本逐末者戒。
(成文于2016年3月19日)
◆背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