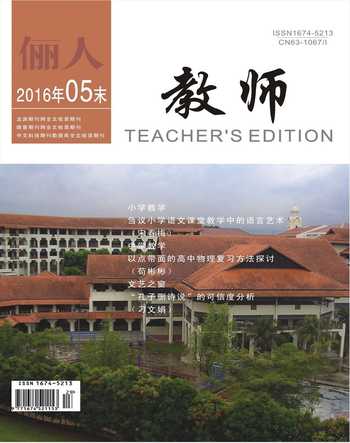人類的瘋狂與文化的救贖
歐陽若蘭
【摘要】回顧兩次世界大戰,人們大多將眼光放在經濟、軍事、政治等方面,而忽略了戰爭中慘絕人寰的殺戮與殘忍,沒有很好的從人文理性方面去看待戰爭。狂熱的人類需要中國文化的救贖,以中國古典文化中庸等思想去尋求拯救。
【關鍵詞】戰爭 殺戮 文化理性 救贖
讀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有人會關注其中烜赫一時的將帥,有人會關注決定大局的著名戰役,史書也大多將整章整章篇幅用以描述探討戰爭中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而戰爭本身所帶有的暴力的互相殘殺和血腥的自我屠戮則較少有學者關注。這樣殘忍血腥的屠戮是人類全體的恥辱,這個世界只要還有劍拔弩張、互相叫囂甚至以士兵性命相搏的爭端,只要還有以軍費和新式武器夸耀于世的政府,那么我們人類就還是野蠻的種族,所有的自相殘殺是人類永恒的恥辱。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20世紀初的一場人類浩劫,大戰使各國人民遭受空前災難,交戰雙方動員兵力共計7340余萬人 ,直接參戰部隊2900多萬人,死于戰場的約1000多萬人,受傷的約2000萬人,受戰禍波及的人口在13億以上,約占當時世界總人口的75%,戰爭造成的經濟損失達2700億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戰參戰的國家則有61個,交戰雙方所動員的總兵力超過1億1千萬,傷亡人數超過9千萬,投入的主要武器裝備為飛機80萬架,坦克35萬輛,用于戰場的汽車和各種牽引車44萬輛,戰場遍及三大洲(歐洲、亞洲、非洲)和四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北冰洋、印度洋),戰爭規模大大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災禍也大大的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這些就是人類所自我標榜的文明理性嗎?莎士比亞贊美人,說人是“萬物的靈長”1,我想這話至少在那些戰爭的年代是大謬不然的,在那種血腥的狂熱之中的人如主所說,是“罪孽深重的”(《圣經》)。人“異于禽獸者幾希”2,當人用子彈與另外一個同類交談的時候,已經是禽獸不如了。
狂熱的人類需要中國文化的救贖,而中國人在1949年以后親手扼殺了這可以供全世界安身立命的文化。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說“人類如果還要向前發展,就要回溯中國先賢的智慧,孔子的智慧”,這只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3(《論語》)。
辜鴻銘在德國以“The spirit of Chinese”為題演講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陰云籠罩在全世界的天空的時候,中國人“良民的信仰”在辜鴻銘看來是解決西方世界不斷陷入戰爭的靈丹妙藥。
二位先哲宿儒的觀察和論斷不能不引起世人深刻的思考。中國現存最早的兵書《孫子兵法》認為戰爭是最迫不得已的選擇,“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再次伐攻”4,戰爭在中國人看來是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最下策。在中國傳統的思想資源中,戰爭是不許懼怕的,也是不可倚恃的,《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國雖安亡戰必威”5。在中國先秦最偉大的軍事家和哲人眼中,軍事只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準備而已,中國民間有句俗語這好可以與司馬穰苴的這句名言相印證,那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此俚俗,可是真若如此那么天下就真的可以“垂拱而治”了。
中國文化中各種學說流派都可以共存,外來的宗教和學說也可以容納和吸收,中國不會有西方文化中的宗教戰爭,也不會因為教義之爭和宗教信仰的沖突而流血,中國人的思想深處是“天人合一”和“仁義”。“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6,中國文化是一種海納百川的文化,是包容的文化,而不是狹隘的文化。
中國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義”,“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5,中國這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6的“仁義”是可以使“天下運于掌”的。
中國文化在49年以后遭遇了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明代八股取士深重百倍的災難,這不僅僅是中國文化之厄運也是世界命運之厄運。中國文化在此半個多世紀的蹂躪之后,在此商品經濟“一切向錢看”的薄俗世風之中和“應試”新科舉體制下是否還有重新發芽生長甚至復興的可能,非我所敢妄下斷言,但今后世界文明的進步必待真正純之中國文化的注入,則是無可置疑的!
【參考文獻】
[1]莎士比亞:哈姆雷特[M].江蘇:譯林出版社,2013
[2]孟子:孟子.離婁下[M].北京:中華書局,2015
[3]孔子:論語.顏淵篇[M].北京:中華書局,2006
[4]孫臏:孫子兵法[M].北京:中華書局,2011
[5]司馬穰苴:司馬法[M].新疆:新疆少兒出版社,2006
[6]鄭玄:禮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5
[7]禮記.中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8]孟子:孟子.梁惠王[M].北京:中華書局,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