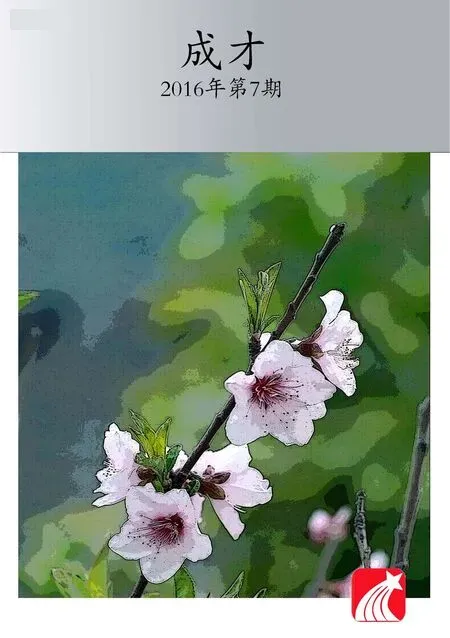長大后我成了你
■ 武漢市漢鐵初級中學 蔣必武
長大后我成了你
■武漢市漢鐵初級中學蔣必武

雅斯貝爾斯說:“教育的本質是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云推動另一朵云,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可見,教育是思想與思想的碰撞,是生命與生命的對話,是心靈與心靈的交流。所以說教育應該是溫暖的、理解的、助人的。
——題記
2002年的第一場雪,似乎來得比平常早一些。時光逆轉成白色的晨霧,在朦朧的蒼穹里,24年前的回憶卻變得清晰可聞。喂!你還記得嗎?我在心里對自己說。1978的自己,1978年冬季。
蔣必玉老師,我小學四年級到五年級的班主任兼語文教師。一至三年級都是在我家堂屋里上學,因為學生數不多。讀四年級時因為老師不夠,就將我們的校區即我家的“堂屋校區”撤掉了,合并到我們村的唯一一個正規的學校。在這里,一個很高挑但很瘦的女老師成了我們班的班主任,還教我們語文。她就是蔣老師。開始我也沒有覺得她有什么不同。直到那年冬季,雪下得很大,我們凍得無法上課,蔣老師就把自家的柴火拿到教室里來,生了一堆火,我們就圍著火開始讀書,雖然后來我們的家長都自己時不時地送柴到學校供我們生火取暖,當然把蔣老師的柴也還上了,但我們這些從村里來的小孩都第一次感覺到她的溫暖。
其實那個時侯我們基本上都只上半天課,下午,有時甚至是一整天都到各個生產隊去務農,如幫忙打核桃,打梧桐籽,瓣玉米,割麥子等,有時蔣老師帶著我們自己出去開荒,種芝麻,待到收割后,就賣掉給我們買本子,繳學費,還有一部分作為獎學金。特別是蔣老師家里殺年豬時幾乎都把我們班上的同學請到她家大吃一頓。總之,我們過著自給自足的學生生活,很快樂,似乎沒有什么學習上的麻煩。讓我真正見識她的“熱度”是我的一次不經意犯的一個錯誤。
記憶中好像是1979年的上半年,當時都在穿T恤之類的衣服。我的同桌是一個女孩,是當時我們村子里很富有的一個家庭的孩子。記得那天下午她穿著一件嶄新的紅色T恤。放學的時候,老師布置家庭作業時,我的鋼筆突然沒有墨水了,我就順手一甩,不小心,一行黑色的墨水剛好落在她的衣服上,頓時她哭喊著:“蔣必武,你賠我的衣服。唔、唔、唔。”我轉身一看,也驚呆了。怎么辦?我哪有錢給她買一件新的呢?現在怎么辦?她回家也要受批評啊。蔣老師就在講臺上,聽著那個女同學哭,我根本就不敢看她。我只在一個勁地向那個同學道歉。這么一件漂亮的衣服剛穿就這樣遭罪,她恐怕很心疼,她的家長說不定還會訓誡她,應該也很害怕吧。最后,我也無招了,慌亂中便大喊一聲“你脫下來我給你洗了。”這句話不說,也許事情會稍微緩解了,不想惹了更大的麻煩“老師,蔣必武耍流氓。”我自知惹大禍了。這時蔣老師才走到我們桌旁,先叫那個同學收好書包,說送她回家。然后再轉過身來說要我回家,她想辦法。我不知道蔣老師能想出什么辦法解決那么難的問題。令我驚訝的是、第二天那個女同學還給我了20元錢,她媽媽說我不是故意的,同學之間也就算了。我深深感激她的同時也迷糊了:“怎么她還我20元錢?”我不敢去問蔣老師是怎么回事兒。回家給我家長講了這件事之后,我母親要我父親給蔣老師送一背柴,算是謝謝蔣老師。但我知道那柴只是杯水車薪,我覺得欠蔣老師的情。而第二天蔣老師在走廊見到我時只說以后做事要小心一些。我怔在那里,心里很害怕,同時也被溫暖充盈著。直到我后來參加工作再遇見那個女同學,詢問當初的事,她才告訴我蔣老師說每次我父親給她送的柴她都稱一下,把錢一直留著,準備給我補貼學費。后來她就拿出來給我縫禍了。
一晃就到了我們去北斗坪參加小升初的考試。因為只有半天的考試時間,再加上我的家里實在是困難,也沒有為我準備干糧什么的。等到中午考試完畢,別的同學都拿出自家的饅頭、包子、飯等就迫不及待的吃起來。我卻什么也沒有,正準備去旁邊躲躲,然后一起回家,這時蔣老師走過來說:“蔣必武,這是你媽媽給你送來的饃饃,拿去,趕快吃,我們好一起回去。”我望望蔣老師,把一個大饃饃接過來,也許是太餓了,并沒有想蔣老師是怎么解決吃飯問題的,只是呆在一旁,悄無聲息地吃著,有點噎,但感覺暖暖的。
一眨眼,24年過去了。雪似乎下得越來越大,我走在武漢南京路的一個小巷子里。因為老家學校在準備搬遷,而我家里仍然特困,再加上我的母親一直處于臥床狀態,我看能否到武漢或者宜昌闖蕩一下,多掙點錢,好給母親治病。于是我請假來武漢的警予中學試講。白天還是有太陽,所以我也就沒有穿很多就坐車來到武漢。沒有想到一進武漢,到處都在下雪。我頓時感到無助。到達別林(蔣老師的大女兒)家,沒有想到蔣老師也在別林家里,我真是萬分驚喜。喊了一聲蔣老師,她沒來得及答應,就趕快跑進房里給我拿了一件毛衣遞給我,我立即穿上,頓覺無比溫暖。其實這次成行還是多虧蔣老師幫忙,不然,我怎么會知道武漢有一個警予中學呢?晚飯后,蔣老師要陪我去警予中學熟悉環境。雪還在下,走出房門,一陣陣寒意,我說蔣老師就別去了,太冷,她退休后身體也不怎么好。但她堅持要去,因為我剛來武漢,特別是又遇上下雪。走在街上,已是沒小腿的雪。走進校園,再看看了我第二天要講課的教室,我們就立刻回家。待回別林的屋坐定后,她又問那堂課的精彩處是什么?能否給校長及聽課的老師們留下深刻的印象?還有是否預備了如果警予中學錄用我,以后的困難有準備沒?我驀然發現,蔣老師還是22年前的那個蔣老師,我還是22年的那個有點小調皮的蔣必武。改變的是時空,沒有改變的仍然是蔣老師的溫暖。第二天我的講課非常成功。于是也就有后來我在武漢的立足、起步、發展。
所有的思緒沉淀,心底蘊藏的溫馨畫面徐徐展開。抑揚里漸忘了色彩,遲暮的年華,聲色的特寫,回歸年少時純白的指頭含苞。毫不過分地說,那個蒼白的冬日,那些大雪彌漫的冬天,城上破裂的云朵和不曾出現的朝陽,在我的記憶里卻撐起了整個夏天。
此刻,我想起當代教育家李鎮西的話:“教育就是讓孩子留下美好的記憶。教育就是喚醒孩子們一幕幕美好的記憶。”我又想起那晚武漢的雪,好厚,好厚,而我的班主任蔣老師依舊那么溫暖、溫暖……。
責任編輯成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