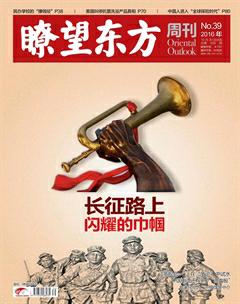民辦學校的“賺錢經”
王輝輝
以市場為導向還是以理想為導向?這一直是中國民辦教育面對的終極問題
2016年9月,陳飛(化名)離開了他供職一年多的某民辦高中。
為了壓縮師資成本,他所在的民辦高中每年通過招收新教師替換掉有經驗的老教師。而由于對招生的重視程度超過了教學質量,學校關心的只有如何保證在校學生不中途退學,以免學校受到經濟損失。
“說是辦教育,但賺錢卻被擺在第一位。想做一位好教師,在這里根本無法實現理想。”陳飛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表示。
先天不足
新中國成立之后,公辦學校曾一統天下,這種局面直到上世紀80年代開始才逐漸打破。
然而,無論是在教育經費獲得,還是在學校、學生及教師的社會認可度方面,民辦教育都無法獲得與公辦學校平等的地位。
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國家對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依法辦學,采取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加強管理的方針”。
之后,在一系列政策松綁及推動下,學歷性的民辦中小學及高校開始陸續成立。民辦教育整體發展環境逐漸好轉。
教育部數據顯示:截至2003年底,全國共有各級各類民辦學校7.02萬所,在校生1416.16萬人;而2015年,全國共有各級各類民辦學校16.27萬所,在校生達4570.42萬人。
“規模上去了,但包括教師等優質教育資源仍然集中于公立體系,因此,民辦教育的社會認可度仍然不高,在政策與環境的夾縫中生存,想真正實現教育的高尚理想,卻又迫于現實不得不在市場的洪流中搏擊。”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中國教育科學院教育發展與改革研究所所長吳霓感慨道。
雖然國家在民辦教育發展的宏觀政策中對民辦學校有優惠和獎勵措施,但具體的落地情況并不樂觀。
如一些登記為民辦非企業單位的學校,應該算是非營利的公益單位,按照國家有關法規,可以享受稅收優惠政策。但據一位要求匿名的專家介紹,真正能夠達到有關部門規定的財政優惠和稅收優惠標準的民辦學校很少。這使得民辦學校對成本極其敏感。
以市場為導向還是以理想為導向?這一直是中國民辦教育面對的終極問題。
招生、“維穩”比教學更重要
2015年9月研究生畢業的陳飛通過考試,進入某教育集團下的民辦學校,成為該校一名負責新聞宣傳的老師。
當年志氣滿滿地進入教育領域,而如今再提起他在這所學校短暫的一年經歷,陳飛的評價卻是“教育已經完全淪為賺錢的工具”。
在他看來,學校最大的問題就是教師流動過于頻繁,“最近一年集團K12學校的1800多名教師中,至少有40%的教師都是新進人員。”
實際上,這是學校控制師資成本的招數。
因為按照學校規定,教師第一年的工資很低,教學崗位的月薪為2500元,行政崗位的月薪則更少,只有1800元。而該教育集團所在省份的統計局2016年6月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省城鎮居民的平均月工資約為4000元。
雖然學校在招聘宣傳中稱,進校之后教師工資會逐年增加,但是據陳飛了解,在集團下轄的K12學校里,教齡真正能超過5年的教師很少。
陳飛認為,之所以教師流失率高,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學校對老師的管理過于企業化。
他介紹說,對于大部分教師,學校似乎不太關心其教學水平,而能不能招來更多學生、能不能穩定學生不讓其中途退學、能不能維護好學校資產不被破壞則成為更重要的考核和獎勵標準。
“很多真正喜歡教師這個行業人,很難長期待下去。”陳飛說。
最讓他難以忍受的,是學校對于資產的嚴苛管理。比如,教師或者學生損壞了貼在桌椅上的條形碼,要被罰款。甚至教師離開宿舍時,忘記拔掉空調等電器的插座,也要被罰款。
“這給人的感覺是,學校的資產比什么都重要,每件物品上貼的條形碼都要每天檢查,太牽扯精力了。”陳飛對學校諸如此類的管理制度頗為不滿。
教師流失率高對該校似乎從來都不會構成困擾,其應對之策就是大量招收當地高校畢業的應屆畢業生,因為這樣可以大幅壓低工資水平。
“我進去之后才知道,K12學校的大部分教師都是省內二本或者三本院校的畢業生。”陳飛說。
此外,每位老師還要承擔繁重的招生和“維穩”任務。
據陳飛介紹,無論是教學崗位還是行政崗位,K12學校的每位教師每年都有12~14人的招生任務。完成任務的,每招收到一名學生教師可獲得300~500元的現金獎勵,完不成任務的則要受到經濟處罰。
而班主任還要承擔“維穩”任務,即保證學生不發生中途退學的情況。
“班主任每月的工資中就包含有1000元的‘穩定費,學生不流失班主任才能領到這筆錢。”陳飛說。
高升學率如何煉成
與陳飛相同的是,賈麗(化名)也在入職河南某民辦高中一年后,選擇了離職。
“學校過于重視利益,而不太尊重知識和教學能力,好像不是學校應該有的樣子。”賈麗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比如學校一向引以為傲,被視為是招攬生源秘笈的高升學率,背后大有文章。
賈麗所在學校對外宣傳稱,2015年、2016年其重點大學升學率分別為11.4%和14.2%。而河南省招生辦公室的數據顯示:同期河南全省分別有5.49萬人和6.34萬人被重點高校錄取,錄取率為8.2%和9.05%。
如此高的升學率是怎么達到的?
據賈麗介紹,學校每年能考進好學校的“尖子生”都是從周邊地區以優厚的條件“挖”來的。
每年五六月份,學校都會將所有老師編成若干招生小組,每組2~3人,到學校周邊縣區的高中挖尖子生,“每組的任務是至少招到2人。”
招生老師一般會向學生家長承諾,孩子考上學校的尖子班之后,學校不收學費,還能享受到遠比公辦學校優越的學習環境。考上重點大學還可以獲得數額不等的現金獎勵。
“學校的硬件設施很好,收費也貴,如果不收學費3年下來就相當于省了7萬~8萬元,很多學生家長會為此動心。”賈麗說。
她認為,實際上,這些尖子生不管在哪所學校,考上好大學的幾率都很高。
對老師來說,如果誰招進來的學生能在入學后的第一次摸底考試中取得全校第一,該教師就可獲得10萬元的獎勵;如果學生能夠進全校前十,招生老師也可獲得上萬元的獎勵。
賈麗介紹稱,在該校超過4000名在校生中,有約20%的學生是這樣從周邊各個學校挖來的“尖子生”。而他們正是學校維持聲譽的保證。
剩下的學生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于當地的高收入家庭。這些孩子多半從小缺少家庭教育和管束,自制力不強、有各種不良習慣、學習成績差,難以進入公立教育體系,因此才會選擇高價民辦學校。
“對于這部分學生,學校的要求是保證穩定,只要他們不退學就行。”賈麗說。
而在學費定價中,學校的策略是抓住學生家長盲目攀比和“高價等于高質”的心理,每年都會上調學費。
賈麗透露,她所在學校總部,2016年秋季開學時,高中部的收費已經達到了每人每年3.3萬元,比2015學年的3.1萬元漲了2000元,而其他分校區的學費則每年上漲1000元。
“學費每年都上漲,社會就會認為我們發展得很好,底氣很足,不怕招不來學生。”賈麗告訴本刊記者,該校的一位管理者曾在教師會議上如是說。
學校的公開材料中稱,2015~2016學年,其旗下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的學費分別為1.6萬~3.25萬元、1.4萬~3.4萬元、1.2萬~3.35萬元、1.95萬~3.36萬元。
而全球著名咨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的數據顯示:2015~2016學年,中國民辦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的平均學費分別是3235元、2567元、3289元、7719元。
造富快車
近年來,中國民辦教育在市場上表現出了強勁發展勢頭。
2016年8月~9月19日,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先后有3家內地的民辦教育機構向港交所遞交了上市申請。而此前的1月,成實外教育已成功在香港上市。
以2016年9月遞交上市申請的宇華教育為例,公開資料顯示,這家成立于2001年的民辦教育機構,最初僅是一所以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河南分校名義運行的民辦學校。如今,不過是短短15年的發展,它就已成為覆蓋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民辦教育集團,包括24所K12學校和1所大學。2015~2016學年,該教育集團旗下25所學校中,共有超過4.8萬名在校生。
宇華教育遞交的上市申請材料顯示:截至2015年8月底的財年營收達6.98億元,比上年同期的5.99億元增加了9900萬元,增長率達16.4%;凈利潤達2.45億元。
“其毛利率已經超過了45%,凈利率也能夠達到35%。”一位業內人士告訴本刊記者。
在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民辦教育研究所所長王磊看來,這并非個案。“從公開數據看,近兩年,很多民辦學校都保持了較高的利潤率。”
2016年8月遞交上市申請的睿見教育在其申請材料中稱:2015年其營收為5.69億元,2014年時這一數字是4.51億元,年增長率超過了26%;而其2015年的凈利潤為1.82億元。
王磊告訴本刊記者,即便在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情況下,整個民辦教育的利潤率也普遍高于傳統行業,“我們估計應該能高出10個百分點左右。”
而教育行業垂直媒體鯨媒體援引咨詢機構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稱:2015年,中國民辦教育行業總營收達到2879億元,比2011年的1740億元增長了1139億元,年復合增長率超過16%。
但是,王磊也發現,真正辦得好的民辦學校,反而不那么容易掙到錢,利潤率一般也不會太高,“因為教育始終是一個高投入的產業。”
在王磊看來,民辦學校要辦出特色才能吸引生源。而特色要有優質的師資保障,還要引進好的教育理念,創新教學形式,探索好的治理結構,“這些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
他舉例稱,2015年北京市公辦中學的生均支出已經超過了2萬元,而北京普通民辦中學的收費多為1萬~2萬元,國際班或者中高端民辦學校的收費則在4萬~7萬元之間,所謂的貴族學校則要高得多。
“從學費收入和經費支出看,如果是普通民辦學校,很難實現高盈利。所以,到底要如何在保證自身生存和發展的情況下堅持教育理念,這對中國民辦教育來說是個生死攸關的問題。”王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