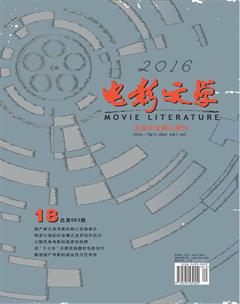英國黑色喜劇電影的藝術特征
[摘 要] 英國黑色喜劇電影以其獨特的喜劇性和文化性引領世界黑色電影的發展潮流。在后現代文化語境下,英國黑色喜劇電影大師丹尼·博伊爾、蓋·里奇等人沒有遵循傳統喜劇電影的創作慣例,通過非理性的敘事結構、顛覆性的人物塑造、游戲化的情節設置等黑色電影創作藝術,實現了對傳統電影審美標準、創作慣例的超越,以矛盾性、荒誕性、狂歡化的影視藝術特征在世界影壇獨樹一幟,值得認真研究。
[關鍵詞] 英國;黑色電影;敘事;審美
黑色喜劇電影作為后現代文化的產物,以喜劇藝術的張力映射著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如價值觀、身份認同等問題,讓很多影迷在令人捧腹的幽默情景中感受到絲絲酸楚。縱觀世界影壇,英國黑色喜劇電影因其悠久的英倫喜劇傳統及幽默的民族性格,成為世界黑色喜劇電影的典型代表,引領了世界黑色喜劇電影發展潮流。無論二戰時期的“伊林喜劇”還是20世紀80年代的《一條名叫旺達的魚》,抑或是黑色喜劇電影大師蓋·里奇90年代的《兩桿大煙槍》,都讓全世界見識到了英國黑色喜劇電影獨特的藝術魅力,更讓世界影壇開始關注和研究英國黑色喜劇電影的藝術特征。
一、英國黑色喜劇電影的敘事藝術
(一)非理性的敘事結構
英國黑色喜劇電影經常采用非理性的敘事結構,打破常規敘事時空,讓觀眾在許多意外、誤會和巧合等喜劇元素中尋覓故事的邏輯性和完整性,同時讓多線索交叉出現,營造敘事結構的碎片化和懸念化,保持故事的緊迫感和沖擊力。
碎片化的故事安排可讓多個故事同時呈現發展,增加故事的矛盾性和沖突性。例如《兩桿老煙槍》中,整個喜劇故事采用七個各自為戰的碎片交叉出現,每個故事既相互獨立,又相互交叉影響,直到最后匯聚在一起,爆發式地呈現給觀眾,營造意外的喜劇效果。再如導演蓋·里奇為增加故事的喜劇化效果,經常采用蒙太奇式的碎片化敘事展示沖突,在2005年的《轉輪手槍》中,導演就讓主人公通過國際象棋的規則與生活事件結合,讓象棋規則貫穿每一個故事中,在象棋規則總的敘事結構下各個故事網狀交叉融合,讓觀眾在不同的故事中會心一笑。英國黑色喜劇故事讓傳統線性的敘事順序被完全打亂,故事原有的時空縱深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復雜的關系和混亂的情節,讓毫無邏輯性的交叉結合產生一定的幽默感。另外,為增加對觀眾觀影心理的沖擊,影片將很多突發性的事件穿插在故事過程中,打破了故事僅存的邏輯性,同時偶然性的事件與原有敘事結構之間的碰撞和交錯,讓很多故事呈現出失控性的荒誕感和滑稽感。總之,英國黑色喜劇電影采用非理性的敘事結構主動地制造了很多巧合、意外和懸念,為電影的喜劇效果創造更多條件和機會。多線索、碎片化、偶發性事件的沖突、碰撞,并沒有遵循著觀眾的預測方向發展,而是以意外和刺激將故事推向高潮,讓故事在失控的邊緣爆發出最大程度的喜劇感和心理沖擊力。
(二)顛覆性的人物形象
英國黑色喜劇電影經常關注的是市井小人物的經歷,他們來自社會底層或社會的最邊緣,即使獲得機會躋身英國上層社會,也難以掩飾自身的陋習和粗俗。而且英國黑色喜劇電影充分利用了后現代藝術中解構、變形、扭曲等人物塑造手法,對傳統喜劇人物形象進行了顛覆性的設計,讓影片充滿了人性的思考及故事發展的不確定性。
例如,英國黑色喜劇電影中數量最多的強盜片一反傳統影片中強盜形象的表現方式,打破了西方影迷對某些所謂“飛天大盜”“亦盜亦俠”的心理崇拜。黑色喜劇電影以喜劇的視角將盜賊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本質展示給無數觀眾,非常具有幽默感和諷刺性。例如蓋·里奇1998年的《兩桿大煙槍》中,一對笨賊本想去搶偷毒販的大麻和錢物,但是卻被一位行將入土的老頭暗算,不僅一無所獲而且惹了諸多的麻煩。兩個笨賊在渾渾噩噩的搶劫中,笑料百出,滑稽和愚蠢被展露無遺。再如蓋·里奇《兩桿大煙槍》一片中懼內的殺手、《偷拐搶騙》中的“四指老法”等形象都對常規盜賊人物進行了顛覆和解構,讓觀眾心中原本身手敏捷、聰明機智的大盜成為可笑滑稽、智力低下的笨賊,這種與傳統相背離的人物塑造不僅創作出獨特的笑料和幽默效果,而且也讓黑色喜劇巧合沖突不斷,懸念迭生。除此之外,英國黑色喜劇電影還經常以小人物的笨拙和恐懼,展示人的弱小和善良,并引發觀眾的反思。例如,博伊爾1995年的作品《淺墳》用三位朋友在面對巨款時的笨手笨腳和恐懼引發觀眾的捧腹大笑,并讓觀眾在大笑之余反思人性的黑暗和貪婪。博伊爾用中國文化中“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黑色喜劇效果,以獨特的邊緣人物揭示真正的人性,讓喜劇充滿了思考。
(三)游戲化的故事情節
英國黑色喜劇電影中,博伊爾、蓋·里奇等導演以后現代娛樂精神抵消了傳統嚴肅電影的嚴肅性,以戲劇化、游戲化的故事情節表達更深層面的內涵。簡單說,英國黑色喜劇電影以刺激和快感委婉地展示著悲劇意識,讓人們在笑聲中接受某些稍顯沉重的道德元素。
英國大量黑色喜劇電影通過娛樂化、戲劇化的情節構建讓原本扣人心弦、緊張的情節充滿了喜劇效果。例如,在影片《一條名叫旺達的魚》中,導演通過游戲化的情節講述了以喬治為頭領的團伙為搶劫鉆石而引發的種種啼笑皆非的故事。影片為營造黑色喜劇的藝術效果,讓游戲態度貫徹整個搶劫故事情節,以游戲抵消觀眾對法律、秩序等傳統事物的認知,以游戲和社會認知的沖突引發觀眾的笑聲和思考。影片中老夫人被凱恩謀殺的情節,凱恩被奧特以薯條、水果、魚逼供的情節,旺達和里奇幽會的情節,都被導演以游戲式的精神予以戲劇化設計,讓每個故事的結局如同游戲一樣都最終呈現啼笑皆非的效果。在影片中盜賊凱恩不僅沒有受到制裁,反而不再口吃,成為司儀主持娛樂游戲;而奧特成為南非司法部長;旺達與里奇有情人終成眷屬。除此之外,英國黑色喜劇電影都采用非常規的情節編碼方式,以游戲化的態度讓觀眾嘲笑、接受、反思某些看似毫無關系的事物和結果,如友情、愛情、法律、婚姻、信仰都常常按照游戲化的夸張方式與故事情節融于一體。觀眾在隨心所欲或天馬行空的游戲情節中感受世界的張狂滑稽,一切都顯得可笑幽默。可以說,在后現代的文化語境中,黑色喜劇電影成為觀眾放縱自我的游戲世界,在游戲中關注及否定已經習慣和接受的現實,從新的、矛盾的、戲劇化的角度審視自我及整個社會,這也許正是英國黑色電影深受世界影迷喜愛的原因之一。
二、英國黑色喜劇電影的審美藝術特征
英國黑色喜劇電影為彰顯如“價值觀偏差、存在困境、身份迷失及情感焦慮”的黑色主題,故意在審美方面突破了觀眾的審美期待,以丑化的事物、故事及人物個性化地創造出了某種非理性的文化語境,讓觀眾在美和丑的對比中,發現更多的喜劇元素和黑色文化內涵。
不同于傳統喜劇電影將“美”當作人文關懷與影視表達的核心或重點,人性的美、感情的美以及情景的美都成為主流的審美話語,以美麗事物的渲染和表達來鞭撻、抵抗丑惡事物或現象。但是在英國,如博伊爾、蓋·里奇、拉布特等黑色電影導演在很多喜劇電影中故意以丑化的藝術形象和事物將影視審美的方法表現給觀眾,引導觀眾在主流審美標準和影視內容之間進行心理評判或選擇,以審美的失衡造就喜劇效果和黑色內涵效果。英國黑色喜劇電影以悖論的方式表現著對“美”的意識理解,沒有將創作主題或對象局限在“美”的事物,而是毫不避諱,甚至直接將丑的現象藝術化地夸大呈現出來,如“形象的丑陋、語言的低俗、性格的陰暗、環境之惡劣”都直觀地在大屏幕上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例如1996年博伊爾黑色喜劇電影巔峰之作《猜火車》中,導演對原作者威爾士筆下的主流審美標準和內容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編,在黑色幽默的劇情中直觀地展示了愛丁堡癮君子丑陋、低賤的生活現狀,真實地揭露了吸毒者的墮落和殘酷。雖然是喜劇電影,但是導演在影片中沒有回避吸毒和性愛等黑暗元素的展示,讓丑陋成為主流的審美標準,形成了極具矛盾性、悖論性的喜劇效果。英國黑色喜劇電影中類似這些對丑陋事物的表現讓影片基調具有矛盾性的氣息,讓觀影者在美和丑的強烈對比中發現喜劇元素,并在開懷大笑中形成對自我認知的主動性批判,修正自我的審美標準和思想。同時,黑色電影這種重視丑陋現實的審美藝術提高了觀影者的心理優越感,讓他們在喜劇情節中感受到自我價值的高度。盡管黑色喜劇電影中過度重視丑陋現實的揭露與主流審美標準大相徑庭,但這種審美的對立和不協調反而激發了劇情的喜劇感,為其劇情的發展奠定了邏輯基礎和發展基礎,從而讓一些悖論能串聯在一起,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故事內容和線索。英國黑色喜劇電影發展中,宏大的敘事之美、人物的道德之美、環境的唯美都被導演主觀地削弱或消除,取而代之以丑陋現象增加故事的荒誕性。雖然這種重視丑陋的審美藝術拉大了喜劇電影與現實生活的距離,但卻形成審美沖突和喜劇效果,也滿足了后現代文化語境中觀影者多元的心理需求和審美標準,讓觀眾的感情得到一定程度的認同或宣泄。
三、英國黑色喜劇電影的影視處理藝術
英國黑色喜劇電影作為西方商業性、娛樂性電影的重要形式之一,為吸引當代觀眾的眼球,在影視拍攝上也采取了極為個性化的手法,甚至讓很多藝術手法專門為其黑色喜劇效果服務。
英國黑色喜劇電影在影視處理方面,主要以滿足后現代文化主體的娛樂要求為目的,在拍攝中一方面沒有完全擺脫傳統喜劇電影的特性;另一方面,又沒有中規中矩,力求讓故事場景和氛圍顯得與眾不同。具體來說,英國黑色喜劇電影為吸引后現代青年觀眾的參與,在影視拍攝中經常將極具時尚性、后現代個性、心理沖擊性的拍攝手法運用其中。例如,英國黑色喜劇代表導演蓋·里奇為滿足后現代文化的要求,專門提出了“酷電影”這一新影視審美藝術概念,以快節奏、動感、新穎個性化的鏡頭轉換、音樂、畫面分割、畫中畫等藝術手法和肆無忌憚、天馬行空的劇情,增加喜劇效果,為當代觀眾帶來感官和心理的刺激和快感。雖然英國黑色喜劇電影在影視審美藝術方面,無論是剪輯還是攝影都沒有形成獨具風格的美學體系,但是基本上已經具有“動、活、快”的特點,為觀眾帶來了特殊的觀影感受和視覺沖擊力。例如,在黑色犯罪喜劇《偷拐搶騙》中,蓋·里奇在影片伊始采用靜音和順接技術將影片中主要人物進行依次介紹,這對于觀眾來說如同電子游戲,讓電影人物的出場具有明顯的黑色幽默特點。而在搶劫鉆石的故事情節中,蓋·里奇還借助監視器之間的鏡頭銜接主觀地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長鏡頭,并賦予旋轉鏡頭及簡介讓盜賊的搶劫顯得華麗而幽默,充分體現了英國黑色喜劇電影“動、活、快”的美學特點,同時還激發了觀眾對影片的觀影欲望,為后續參與故事線索的整合,理解故事黑色喜劇元素奠定了基礎。另外,英國黑色喜劇電影還非常善于采用剪輯來形成喜劇效果和黑色內涵效果,尤其影視后期剪輯中常常將影片故事設置為環形的結構,讓故事時間的線索被主觀打亂,形成與故事敘事的呼應,以混亂、跳躍的節奏感,營造喜劇高潮。
四、結 語
英國黑色喜劇電影亦莊亦諧,無論是在敘事、審美還是在影視制作上,都具有非常強烈的荒誕性和狂歡化的藝術特征。雖然英國黑色喜劇的藝術表現與主流電影存在較大的差異,但是其毫無疑問極大地拓展了喜劇電影的藝術張力和內涵深度,在后現代文化語境下滿足了觀眾對于娛樂性和思想性的雙重要求,也為后工業時代英國電影的發展指明了方向。與此同時,英國黑色喜劇電影藝術的發展讓我國影視藝術界開始認真思考如何以新的、個性化的電影藝術語言去解開文化性和娛樂性融合的這道難題,從這點上來說,英國黑色喜劇電影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學習。
[參考文獻]
[1] 許樂.黑色電影的兩種形態[J].當代電影,2015(04).
[2] 趙飛.丹尼·博伊爾電影的主題思想與黑色人物[J].電影文學,2015(19).
[3] 藍凡.后現代電影的敘事轉身[J].藝術百家,2015(04).
[4] 張晶.后現代視域下蓋·里奇電影的狂歡化敘事[J].電影文學,2016(01).
[作者簡介] 張明會(1979— ),女,河北孟村人,碩士,河北工程技術學院人文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