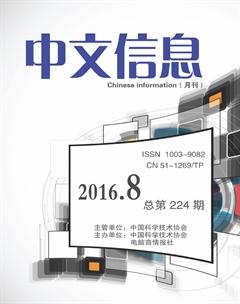探析丁玲小說中的出走模式
鄧錦麗
摘 要: “出走”作為一種現代的文學模式,它是集合了“家”、現代的戀愛觀念、出走人物的符號性以及文本的敘述聲音等因素的。并將它們聚集在一起使其發生現代性質變,一起表現著現代文學中的現代現象。丁玲向左轉型時期的“革命加戀愛”小說中的出走形象也頗值得研究。
關鍵詞:革命戀愛 出走 意識
中圖分類號:I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6)08-0375-01
出走作為一種文學模式多次被作家們提及,成為一個文學母題。以《莎菲女士的日記》震驚當時文壇的女作家丁玲,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采用這“革命加戀愛”的模式創作了《韋護》、《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之二)。這三篇小說標志著丁玲創作轉變的開始,是丁玲“向左轉”的過渡期作品。這些小說在依從革命戰勝戀愛的敘事原則的同時,又表現了轉型期青年知識分子在沖突、矛盾的革命與戀愛之間的痛苦抉擇,并且關注革命時代個體的生存狀況,探尋女性自我價值實現的途徑。而小說均以三位主人公的出走完結,其中充滿了矛盾和張力。
其實,細看在丁玲筆下曾多次談到主人公出走的情況,處女作《夢珂》,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中的夢珂和莎菲都是從“父親的家”出走的。而丁玲這三篇小說中的出走模式與以前的出走是有所區別的,這里的出走,更多強調的是“丈夫的家”,同時也更多地是在描摹革命與戀愛的不合調和的出走。然而搞清楚這一出走現象必不可少的要談論到當時“革命加戀愛”模式的潮流小說。
一、這三篇小說雖在出走這一大的主題上“革命與戀愛”是一致性的,但是細微之處也存在不同
縱觀三篇小說,丁玲受到左翼文學思想革命文學的影響,與之前創作的非常突出的“自我小說”或“心理小說”的風格相比,這三篇小說有著一種相當自覺地“歷史”意識。意在于描寫在新環境新條件下知識分子在革命和戀愛的轉變和苦悶。
雖然這三篇小說均是“光赤的公式”,然而作者毅然決然拋棄了以往只關注女性心理苦悶,欲望壓抑的狹小空間,邁入了更大的范圍,主人公有男性介入,在女性道路的選擇上也不是單一的,女性上不僅出現新女性形象,更有積極的革命女性和也有最后步入自我階級的舊式女性。例如《韋護》丁玲更多關注的是韋護這個知識分子的個人命運,不論是在未遇到麗嘉之前,沒有愛情牽絆,熱情關注革命文壇的韋護,還是遇到麗嘉陷入革命與戀愛中掙扎,而最后經過思想斗爭離家出走的韋護。這是革命者自覺地出走。在《1930年春上海》之一中丁玲關注的更多是女性的個人價值及個人選擇的問題。在之一中,美琳從開始對丈夫的崇拜,到接觸若泉的革命思想與外界的情況,到呼喊出:“你老把我當小孩”這是反抗的開始,她也知道:她一住在他這里,便失去了她在社會上的地位。“她要在社會上占一個地位,她要同其他的人,許許多多的人發生關系。在思想上開始轉變。”最終,“她是不甘再閑住了,她本能的需要活動,他要到人群中去,了解社會,為社會勞動,她生來就不是一個能幽居的人。”得到自我人生的價值和社會定位,成為一個全新的革命新女性。這是女性自覺走向革命,走向大眾的出走。
二、出走模式形成的原因
丁玲的創作風格因其始終未拋棄的政治理想而不斷變化,從早期作為滿懷五四精神的熱血青年關注女性解放,到30年代為了政治理想放棄女性立場,再到延安時期初期女性意識被壓抑后的強烈反彈,這是丁玲女性立場的最后堅持,最終她選擇了主流意識形態,放棄了女性立場,她的創作淡化了女性意識的自覺成份,張揚了女性意識的客觀成份,女性意識統一于情緒高揚的革命激情,進入了女性意識“無性化”的寫作時代。
1.意識形態特點的促成
1927 年大革命失敗,中國社會進入了以階級斗爭獲得社會解放的革命時代,“不僅人的思考中心發生轉移,思維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對人的價值,人生意義的思考轉向對社會性質、出路,發展趨向的探求。”1930年左右,左翼文學思想成為主潮流,“從文學的革命到革命的文學”,文壇上出現了一大批“戀愛+革命”主題的作品。丁玲緊跟時代步伐從無意識的寫作轉向有意識并且是階級意識的寫作的作家。她理念預設中依循革命戰勝愛情的敘事原則,然而潛意識里卻仍然保留了審視男性政治的性別化立場。韋護和美琳的留信出走,望微回信的訣別這種敘事模式都是革命者戰勝愛情的表現。而在同時麗嘉對革命者的態度:“你們有些同志太不仁愛了。你不知道他們仿佛懂得了一點新得學問,能說幾個異樣的名詞,他們也就變成只有名詞了,而且那么糊涂的自大著。”從女性的視角看她們不反對革命,然而革命也不僅僅是個空虛的名詞,是需要現實的基礎和實踐的魄力的。瑪麗的愿意回到自己的階級中仍舊過著自己原來享受的生活。這從兩位女性的語言中再次審視了男性和革命。
2.個人經歷的影響
丁玲在寫作剛剛陷入危機之時,也正是與她共同生活的胡也頻大量接觸馬克思主義并投身革命工作之時。此時她已從兩年前的無名的熱情詩人的妻子變成了革命者的妻子,不久之后又成了革命烈士的遺孀,在其受到丈夫思想的影響下,加上痛失丈夫的不幸,她更加看清社會現實,革命的重要性及其革命和愛情關系下的阻礙。要想獲得和諧美滿的愛情一定要獲得社會的解放,而要獲得生活的解放目前必須得壓制自己的愛情,于是就有了《韋護》中韋護為了革命而舍棄了愛自己和自己也愛的麗嘉。《1930年春上海之二》中望微對于瑪麗的決絕。
3.女性作家內在危機,探尋寫作出路的結果
直到1929年4月丁玲寫完《日》為止,丁玲描寫的女性走的是一條自我保護的反抗之路,此時其筆下主人公的處境,與丁玲有相似之處,毫無意識形態的庇護而是選擇孤獨來自我保護并進行反抗。從1929年底到1930年短短的時間內放棄女性為特點、為犧牲的筆觸,轉向時代大潮,變成一個客觀冷靜的左翼現實主義者。而這種女性的消失是與當時的社會情況,女性立場與大眾立場的如果不是相互對立,至少也是不可兼顧的相關聯的。這就要求作家們如果還依然立足與自己狹小的自我空間而不走出去的話,將很難立足。于是有了其筆下的革命者的出走。
參考文獻
[1]孟悅 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M]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北京 2004年7月第一版
[2]何滿倉《名家精品閱讀之旅丁玲小說》[]吉林外史出版社 長春 2006年6月第一版
[3]傅光明《感悟名家經典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京華出版社 北京 2005年7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