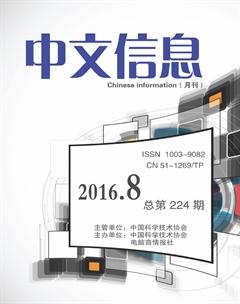《虎子》
摘 要: 《虎子》是托馬斯·沃爾夫晚年的作品,本文通過對該短篇小說的分析,揭露出其中反映的20世紀初美國社會上的種族問題,以及美國黑人在白人主導的社會中受壓迫以致最終走上毀滅之路的現實。作者用短短篇幅的筆墨,描繪了美國社會中隱藏的危機,和自己對于生活和生命的思考。
關鍵詞:《虎子》 托馬斯·沃爾夫 種族歧視 種族隔離
中圖分類號:I10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6)08-0390-01
一、引言
托馬斯·沃爾夫是20世紀前期活躍在美國文壇的著名小說家,他與福克納、菲茨杰拉德、海明威、辛克萊·劉易斯不分伯仲。沃爾夫的作品選材貼近生活,內容豐富、思想深刻,寫作風格樸實奔放、抒情色彩濃郁,常以象征和暗示的手法打動讀者。1938年沃爾夫去世后,福克納將他列為他們那一代中最好的作家,而將自己列在了沃爾夫的后面。福克納說:“我把沃爾夫列為第一,因為我們都失敗了,可是沃爾夫最能盡力而為,因此他的失敗最為杰出……我敬佩沃爾夫,因為他全力以赴,想把話都說了,甚至情愿把文體、連貫性以及所有精確的原則加以揚棄,而希望把人類心靈的所有經驗,原原本本地放在一個針頭上”。[1]
沃爾夫的短篇小說《虎子》(The Child by Tiger) 就是其寫作風格和獨特創作特點的完美展現。《虎子》主要講述了在美國一個小鎮中,一位平日里性情溫和、能力非凡的虔誠基督徒黑人迪克·普羅索突然變成一個瘋狂的殺人狂魔的故事。作者在短短的篇幅中巧妙地設計了許多意味深長之處,給這篇看似情節簡單的小說埋下了耐人琢磨的伏筆,讓讀者對這篇小說有了更豐富的解讀。
二、迪克·普羅索的悲劇
迪克·普羅索是謝波頓家的黑人奴隸,他精通各類工藝,平日里恭敬謙遜,在主人和孩子們眼中都是無所不能。但是,迪克并沒有因為自己的努力而真正得到白人社會的認可和接納。他被極度邊緣化,沒有人考慮他的感受,沒有人走近他的生活。后來,迪克發瘋后,白人們自然十分詫異,平日里恭敬虔誠的黑奴竟突然殺了那么多白人。白人社會的這般態度更加強烈地反映了社會的不公平和黑人們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他們被公認為是下等公民。
沃爾夫在小說中用許多筆墨描寫了迪克壓抑的生活。黑人必須居住在被白人稱之為“黑鬼之鄉”的特定區域;在與白人小孩子交往過程中,他不但稱呼自己主人的孩子為“先生”,更恭敬地稱呼所有白人孩子為“先生”,這一稱呼讓白人孩子們有一種“成熟和高高在上的感覺”;[2]迪克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但他卻因為膚色的原因而被禁止進入教堂,禮拜時他只能悄悄地在教堂的側門聆聽。即使在上帝面前,黑奴迪克也不能像白人一樣擁有平等的權利![3]迪克在開車送謝波頓去城里的路上與醉酒駕車的白人羅恩的車相撞,羅恩不但沒有道歉,反而借著酒勁猛擊迪克的臉部,致使迪克血流滿面。憑迪克的體格,收拾一個醉鬼應當是綽綽有余,但迪克只能將怒火壓抑在心中,他能表現的只有因憤怒而充血的眼睛和緊握的拳頭。在這樣一個等級森嚴、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肆虐的社會,迪克只能隱忍,而想要贏得白人的尊重無疑是難于登天。
迪克殺人的直接原因,小說中并未直接說明,但可以從情節推斷出是迪克與另一個已婚的黑人女仆潘茜·哈麗斯的男女私情引發了他與潘茜丈夫的沖突,最終導致了迪克的瘋狂。這件事情看似偶然,實則偶然中包含著不可逆轉的必然。即使沒有這件事情作為導火線,也會有其他別的事情導致迪克的爆發。迪克·普羅索的瘋狂殺人行為不僅是一種對自身所遭受的欺壓和凌辱的惡意報復,也是對白人社會和基督教勢力下黑人長期被壓榨和剝削現狀的反擊與抗爭,是對當時社會中存在的等級秩序和種族歧視的挑戰。
三、羔羊與猛虎
沃爾夫給這篇小說命名為“The Child by Tiger”,題目中的“child”和“tiger”都是對主人公迪克的象征性描述。一方面,迪克像猛虎一樣無所不能;而另一方面,迪克又像孩子,像羔羊一樣無助、弱小,需要保護。沃爾夫曾說:“我所感覺到的生命和藝術元素似乎是一堆的矛盾,在沒有找到一個事物的反面之前,我是無法明白它的。”[4]沃爾夫這種對事物兩方面特性的敏銳嗅覺,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現和貫徹。在《虎子》中,沃爾夫把極端對立的矛盾點放到了一個黑人身上,不僅表達了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對黑人的壓力,也想借此來表達自己對世界辯證性的思考。迪克,一個矛盾的結合體——羔羊與猛虎的結合,純真與邪惡的統一。正如沃爾夫在小說結尾寫的一樣:“他來自黑暗!他是黑夜的兒子,也是黑夜的伙伴,是人類奧妙心靈的另一方面的表征。是人類邪惡無知的一種象征,是人類神秘的一種象征,是人類莫測高深的品質的一種折射,一個朋友,一個弟兄,一個不共戴天的敵人,一個無名的惡魔,是兩個世界。”[2]
“他剛才在念《圣經》。有時候,他跟我們講話嗚嗚咽咽,幾乎成了哼唧,是一種唱贊美詩的吟誦,發自深不可測的、使他心曠神怡的精神陶醉。”[2]這樣一個淳樸、對上帝虔誠的人最終被迫走上了殺人狂魔的絕路,只能說明是社會環境、社會制度對人的高壓,使人異化。這種純真讓人陶醉,而由純真演變的所謂“邪惡”確實令人萬分痛心![4]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托馬斯·沃爾夫用自己獨特的視角觀察并描寫了當時美國社會繁榮外表之下的社會問題。在用小說將其揭露的同時,沃爾夫又加入了自己對世界和人類的辯證思考。他用羔羊和猛虎來象征純真和邪惡,并在黑人迪克的身上將二者完美結合。這篇小說已不僅僅是一篇簡單的短篇小說,而是一篇富有哲學深意的、能令人沉思良久的、給讀者無盡回味的文學佳作。
參考文獻
[1]孫英杰. 談托馬斯·沃爾夫作品的語言風格[J]. 杜丹江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2).
[2]Wolf. Thomas.“The Child by Tiger”.The Web and the Rock.[M].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39.
[3]王菲菲. 迪克·普洛瑟的悲劇——對短篇小說《虎種》的后殖民式解讀. 外國文學,2012(2).
[4]王蘭明,史吏. 《虎種》——純真與邪惡的完美統一. 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
作者簡介:唐夢(1993.5-),女,漢族,籍貫:寶雞,碩士研究生,單位:西安外國語大學研究生部,英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