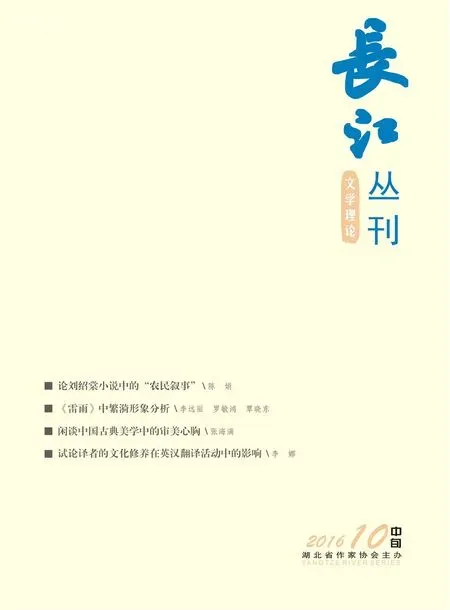從《喧嘩與騷動》來看福克納眼中的美國南方
侯晨茜
從《喧嘩與騷動》來看福克納眼中的美國南方
侯晨茜
美國獨立之后,南方地區長期以來游離于北方正統的資本主義經濟主流之外,雖然內戰后,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種植園經濟走向解體,但南方的怠惰與落后仍沒有太大的改變。經濟發展緩慢,種族矛盾與沖突不斷,下層人民命運悲慘,生活前景黯淡,這一切都在隨后的“美國南方文藝復興當中”深切地流露出來。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是當時文學的最主要特征,而其中的集大成者非福克納莫屬,雖然他的小說采用了現代主義的敘事技巧,晦澀難懂,但其小說的內涵卻深深扎根于南方的土壤,與南方古老的文化與歷史傳統密不可分;因此可以說理解福克納心中的南方世界便是理解他小說深刻內涵的基礎與前提,本文從其代表作《喧嘩與騷動》入手,具體來分析與揣摩在福克納眼中,美國南方的未來將何去何從。
美國南方 喧嘩與騷動 福克納
在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文學里,福克納的小說無疑是先鋒性與實驗性的代表,他以他卓越而無與倫比的現代派寫作技法,顛覆了時間與空間的合理順序,通過眾多人物零星,破碎的思維與敘述來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現了內戰后美國南方緩慢而飽經痛楚的發展歷程。作為土生土長的南方人,福克納對自己的家鄉,他所稱的“一塊郵票大小”的地方了如指掌。然而與之前馬克·吐溫對南方密西西比河流域細致描寫以揭示南方人民,尤其是黑人的艱辛生活不同,福克納的小說顯得更為隱晦,主題思想也愈加復雜多元。《喧嘩與騷動》是福克納早期最優秀的作品,作者在其中傾注了大量的個人情感與感悟,縱觀康普森家族的歷史,便已讓人隱隱看到了福克納家世的影子;因此以它為例,我們讀者若是能在這錯綜復雜的思路與線索中體會出作者內心對古老的南方的真實情感,那將會對我們之后理解他其它愈加艱澀的作品有很大幫助。
描寫家族興衰的題材在歐洲的現實主義作品中早已屢見不鮮,然而能像福克納這般賦予毫不起眼,平淡無奇的家庭瑣事以深刻、復雜而令人深省的社會與歷史文化意義的卻并不多見。全書分為四個部分,各自對應著一個不同的敘述者視角,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為了實現事件描繪真實性與客觀性的煞費苦心。雖然只有最后一部分運用了作者的全能視角來收束全文,但在前三部分的超然,碎片式的敘述中同樣暗含了作者無盡的喜怒哀樂。書中的班吉雖然是一個白癡,沒有任何理智思考的能力,但在全書中卻占有無與倫比的地位。班吉在書中雖然是白人,但卻被剝奪了幾乎任何白人所擁有的權利,甚至無法前往白人的禮堂做禮拜。他的兩個哥哥,昆丁與杰生都將他視為累贅,家庭的災難,唯有姐姐凱蒂和黑人女傭迪爾希像母親一般的愛護與照顧他。他敏感卻孤獨,寂寞,爐火和凱蒂意味著他的整個世界,他一次渴望與人溝通交流的嘗試卻為他帶來了去勢手術的厄運,由此可見,班吉書中所述的33年的生涯當中給人最大的感受便是深深的無奈與乏力,他最愛的牧場,他的姐姐一一從他身邊被剝離,他卻只能聽天由命,隨波逐流。在福克納對班吉所傾注的無限同情當中,班吉的形象毫無疑義地也打上了古老南方的深深烙印。內戰后的美國南方就像無助的班吉一樣,面對變革顯得麻木而遲鈍,只能任人擺布,眼睜睜地看著種種古老的傳統,不論是好的還是壞的,無一例外地分崩離析;雖然有著姐姐和迪爾希的無盡的愛護,班吉最終仍然被杰生像丟棄垃圾一樣地拋到了精神病院,由此可見,盡管福克納對南方的過去飽含眷戀,但卻依舊無法回避歷史的車輪將其碾碎、丟棄的殘酷過程。
凱蒂在文中作為內戰后思想解放的新女性形象,反映了作者對于內戰后社會倫理道德變遷的深深憂慮。作為本小說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凱蒂的形象充滿了矛盾,作者一方面描繪了她的活潑,善良,有同情心;另一方面卻又像詛咒一樣在她很小的時候就預言了她的“不可救藥的墮落”,作者之所以在敘述中表露出如此悲觀,甚至飽含惡意的觀點,就是因為在他的眼中,像凱蒂這樣的姑娘的人生之旅必然毫無出路。本來在原本內戰前的傳統南方,凱蒂這樣的大家閨秀必然會過著與世隔絕,單調乏味但卻安逸富足的日子。然而可惜的是,內戰后的南方雖然一定程度上把女性從家庭的重重束縛當中解放出來,但在整個女性地位低下的社會體系中,社會現狀并不能給她們一條自立自強,實現自我人生價值的正確出路,相反她們被迫被推上了復雜的社會交際當中,在叛逆當中拋棄了許多之前傳統道德的約束,追求無節制的自由,導致了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墮落。由此可見,凱蒂生活在這一時代新舊交替的陣痛期當中,她的茫然,她的熱烈而沖動的性格,導致了她的道德墮落具有相當程度上的必然性。凱蒂在被丈夫拋棄之后被母親徹底排除在家族之外,連自己的孩子都難以相見,她原本是一個如此善良、積極、熱心的姑娘,而今卻陷入了一個既為舊道德所不齒,卻又無法融入新興社會的尷尬而凄涼的境地,就這點而言,福克納的小說中也渲染了相當程度的自然主義色彩,無論是班吉還是凱蒂都逃不出固有命運安排。傳統被破壞,但新生力量卻飽受壓制而誤入歧途,福克納對南方未來的迷茫與悲觀可見一斑。在他看來,內戰給南方帶來了破壞,但卻并沒有帶來合理、公正的秩序,他們雖然解放了黑奴,但卻又帶來了新的,更進一步的壓迫方式。伴隨著種植園經濟的崩潰和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美國南方似乎已然變得更加殘忍,冷漠,人性在金錢與利益的侵蝕下泯滅殆盡。
杰生和小昆丁就是作者眼中的南方未來,他們與書中的昆丁三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昆丁三世執著而近乎癲狂地捍衛著家族最后僅存的榮譽,甚至在希望破滅之后投向了他久已迷戀的死亡,而恰恰相反,名譽在杰生眼中完全一文不名,作為純粹的拜金主義者,杰生心中所想的只是如何去攫取最大的利益,為此他不惜做出一切犧牲,甚至以小昆丁的身份來敲詐他的親生姐姐凱蒂。他并不為他所有的罪惡與倒行逆施而感到絲毫良心的譴責,卻還以此為榮,認為是自己,這個母親口中“具有巴斯康家族血脈”的“男子漢”撐起了養活一家老小的重擔;作者從旁觀者的角度客觀公正地“記錄”下了杰生的自我辯白,頗有維多利亞時代詩歌當中戲劇獨白的特點,在對其丑惡嘴臉的揭示當中折射出了作者對所謂的“新時代的南方”的極度不信任感。同樣的,小昆丁的悲慘命運則是凱蒂境遇的進一步惡化,從一生下來就備受杰生和康普森太太的雙重折磨,她在生活中孤獨,飽受屈辱,沒有尊嚴,這釀就了她的叛逆個性和破碎不堪的人生觀,對周圍所有的人,甚至是對她關愛有加的迪爾希都充滿敵意,她喪失了凱蒂的熱情與善良,卻完全繼承了杰生的惡劣品行;我們完全可以從作者對小昆丁墮落的描繪當中看出他的無奈與痛惜。
小昆丁的私奔標志著南方古老的“淑女教育”的徹底破產,但同時我們沒有從康普森新興一代當中看出任何光明與未來,籠罩全文的黑暗、沉重基調沒有絲毫的舒緩,全文中唯一的正面形象只有迪爾希,這位可敬的黑人女傭三十年如一日的在這所冷冰冰的宅子里無微不至地照顧著一家人的飲食起居,她的善良、熱忱和勇敢照耀了家中的每一個成員。由此可見,福克納本人對南方制度的新舊更迭充滿了迷茫,雖然明知道古老腐朽的南方體制已然無法為繼,但他對未來的資本主義化的南方仍舊充滿了厭惡,陌生感,甚至恐懼。迪爾希是全書中作者留下的唯一火種,這也似乎暗示著我們無論是在何等惡劣、險惡的生存環境下,都要堅守人道主義,堅守傳統的美德與熱忱,至于未來究竟如何,只能依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弗萊德里克·R·卡爾著,陳永國譯.福克納傳[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2]威廉·福克納著,李文俊譯.喧嘩與騷動[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作者單位:遼寧大學外國語學院)
本文系2013年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福克納作品與美國南方文化關系研究—兼論對遼寧特色文化發展的借鑒意義”(L13DWW015)。
侯晨茜(1996-),男,漢族,山西大同人,遼寧大學外國語學院,2015級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