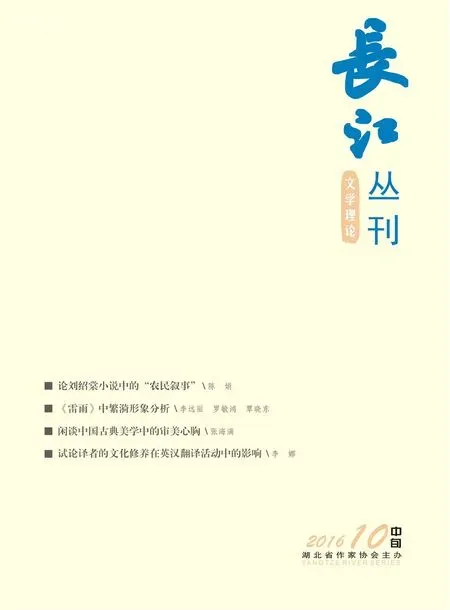昆曲唯美化特征與吳地關系分析
韓 勤
昆曲唯美化特征與吳地關系分析
韓 勤
昆曲作為吳文化典范,被世人稱為“一支幽香襲人的戲曲“蘭花”。它的唯美化特征與發祥地原生態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離開了吳地的原生態環境母體,昆曲之“雅”無從發端。
唯美化吳文化 吳地
法國著名文藝理論家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提到影響藝術發展的三種主要因素是環境、時代和種族。昆曲在它出生之初就充滿著“雅”的意蘊,首當其沖的原因就是原生態吳文化的發祥地:吳地。昆曲唯美化與吳地的吳文化密切相關。在吳文化的熏陶和滋養下,昆曲得以發生和發展。吳文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對于發祥于吳地的昆曲來說,吳文化當然指的就是指以蘇州為核心的吳地數千年來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稱。她不但在勾吳古國存在活力,即便在吳國消亡的二千年后依然保持生機,成為華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一、“斷發紋身”到魚米之鄉
《漢書·地理志》中也說:“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
以水磨調為腔的昆曲發祥于江南吳地核心蘇州,(昆曲發源和活動地昆山、太倉都隸屬于蘇州),江南多水,河網密布、雨水豐富。考察吳地的氣候及地理環境,多雨水、多湖泊河塘無疑是其最典型的特征。太湖周圍的高地一般也只有三至五米。以吳文化中心區域蘇州市為例,境內計有湖蕩323個,大小河港2萬余條,降水豐富,年平均降雨量達1240毫米左右。《史記·貨殖列傳》曰:“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即水耨,果隋嬴蛤,不待賈而足,地執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窳偷生,無積聚而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可見,吳地并不是從遠古一開始就是富庶豐腴之地。周太王之子泰伯奔吳時看到的是和當時以中原為中心的強勢文化具有明顯差別的“斷發紋身”的“蠻夷之地” 地廣人稀(到西漢時,江浙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也不到十人,何況周朝時期)加上當地土著原生態居民與中原相比,顯然是落后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決定著上層建筑。當時的原始土著居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同中原相比顯然是落后的。因此,泰伯奔吳并非僅僅直接帶來了中原較為先進的耕作方法,更為重要的是中原先進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并且也入鄉隨俗,所謂“文身斷發,以隨吳俗”。這樣一來,不僅提高了當地農業生產水平也使得原本以豐富水資源為基礎的稻作更加規范化、規模化,至成為日后百姓廣為流傳的“魚米之鄉”,同時也為吳國今后的經濟、文化發展提供了堅實的農業基礎后盾。
二、魚米之鄉與水磨昆曲
所謂“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魚米之鄉在經濟上的繁榮和昌盛,人民的安居樂業,使吳人有了安心讀書的良好環境,同時吸引了大量外地的文人墨客,形成了文人的聚集讀書風氣的興起。在崇文重教的同時,吳地重商的局面也同樣可觀,并一直延續至今。這樣的局面使得吳地經濟文化發展格局中具有這樣一個引人注意的地方:文化氛圍濃郁,不管是從商還是從政,士大夫還是貴族商賈他們都有相當的文化修養懂藝術、曉音律甚至自己會制文作曲。可以說,崇文重教使得具有經濟地位的上層人士具有相當高的文化藝術素養,而絕非有財無才暴發戶可類比。而同時,經濟的上升,又使得崇文重教這一風氣得到保障而流傳至今。當這些與下層有所區別的所謂上層人士介入昆曲藝術的欣賞與創作,經濟上的放開加上文化上的契合使得昆曲藝術得到了非其他戲劇可比的發展。用通俗的話說就是吳地社會經濟的迅速崛起,對于其文化有著相當大的促進作用。
如果說北方文化是以(黃)“土”為內核,而風格質樸、奔放、雄渾,一如她的秦腔、梆子等;那么南方文化當以“水”為其精魂,而格調細膩、婉約、纏綿。千百年來,江南一直是風調雨順、稻谷常熟四季分明而景色宜人,這里的人們不需要把精力過多用在耕種祈求溫飽的問題上。于是,他們也就有了比貧瘠土地上的人們更多的時間來觀景、來思考;更鮮活多汁的四景來激發想象,怡情悅趣。縱觀歷史,從南宋婉約詞、(宋元的勾欄瓦舍,書會藝人)南曲、明清小說傳奇到近現代的“海派”等都是在江南以“水”為內核的陰性文化的浸淫中滋生、成熟起來。而她們的共同處:或內容以表現纏綿、動人的故事為主;或語言以委婉動聽、優美如歌為勝;或打造意境悠麗纏綿、繾綣柔美、禁不住讓人浮想聯翩。
吳地的地理氣候環境導向了吳人從早期的尚武精神走向崇文。而尚武精神與崇文精神以其各自不同的面貌對吳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定型產生出不同的影響,使得吳文化得以博大精深。吳地的生態環境是昆曲唯美化的決定要素。
[1]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4:3270.
[2][東漢]班固.漢書·地理志[M].北京:中華書局,1962.
[3]趙嘩.吳越春秋[M].北京:中華書局,1985:16.
(作者單位:蘇州工業園區服務外包職業學院)
韓勤(1976-),女,蘇州人,蘇州工業園區服務外包職業學院,博士研究生,講師,研究方向:戲劇影視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