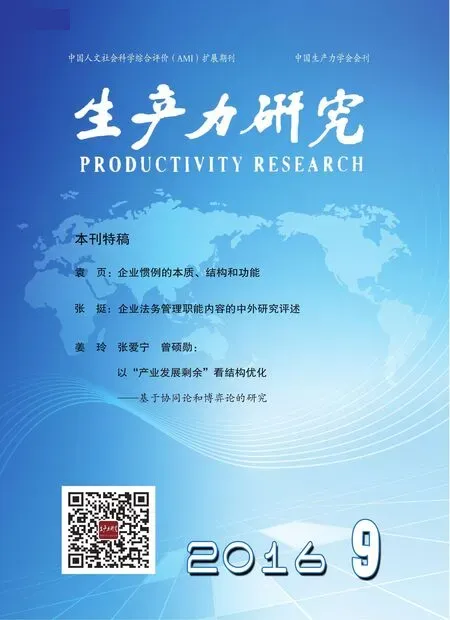秀“內涵”還是秀“外形”?匹配類型對企業家代言自我效應的影響
林 濤,熊小明,郭昱瑯
(1.武漢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2.江西師范大學 商學院,江西 南昌 330022;3.廣東財經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320)
秀“內涵”還是秀“外形”?匹配類型對企業家代言自我效應的影響
林 濤1,熊小明2,郭昱瑯3
(1.武漢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2.江西師范大學 商學院,江西 南昌 330022;3.廣東財經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320)
文章以企業家為他人企業品牌代言為研究背景,從品牌聯合視角探究企業家代言匹配類型對其自我品牌及其所在企業品牌的效應。文章通過兩個實驗研究發現:企業家基于不同的形象與代言品牌匹配時,其自我效應存在差異。基于吸引力匹配(“外形”一致)的企業家代言能正向影響消費者對企業家的態度,但不能影響消費者對其所在企業品牌的態度。而基于專業性匹配(“內涵”一致)的企業家代言不僅能影響消費者對企業家的態度,還能影響消費者對其所在企業品牌的態度。研究還發現,產品類別相關性能正向調節匹配類型對企業家態度以及其所在企業品牌態度的影響。
企業家代言;匹配類型;品牌聯合;自我效應
一、引言
企業家前臺化行為是企業家在公眾面前有選擇的展示行為,是影響消費者品牌態度和選擇的重要因素(朱麗婭等,2014)。隨著社會化媒體的迅猛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開始為他人品牌代言,如,萬達老總王健林為格力品牌代言、360老總周鴻祎為克萊斯勒汽車代言、新東方老總俞敏洪為漢王電紙書代言等。企業家代言作為一種前臺展示行為,以期成為企業快速提升品牌績效的新途徑。從20世紀70年代起,學者已指出企業家作為一種重要的代言人類型能正向影響消費者對廣告的態度和購買意向(Friedman,1977;Kerin&Barry,1981;Rubin et al.,1982)。相比娛樂明星展示“外形”,企業家穩定的個性、可靠的內在形象更能打動消費者、贏得消費者的信任。然而,以往文獻多聚焦在企業家代言自身品牌情境下的廣告效用,卻少有研究關注企業家為他人品牌代言對自身企業品牌績效的影響。事實上,名人代言是一種雙向互惠的轉移過程,既包括代言名人的特質可轉移到代言品牌上,又包括代言品牌的形象可轉移到代言人的個人品牌上(Halonen-Knight &Hurmerinta,2010)。而以往研究多關注的是被代言的品牌績效,代言人的效用極少被關注。代言品牌對代言人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Charbonneau&Garland,2010)。名人代言有助于傳播代言人個人品牌和強化消費者對代言人形象的感知(Seno&Lukas,2007)。尤其當代言人為企業家時,其代言行為會產生更為廣泛的效用(黃靜等,2015)。在2012年7月,360安全衛士董事長周鴻祎代言克萊斯勒的廣告不僅贏得了消費者對克萊斯勒的積極品牌態度,還提升消費者對周鴻祎個人創新能力的形象感知,更強化了消費者對360品牌理念(保護電腦安全)的認知。
名人代言現已被理解成一種品牌聯合,個人品牌與企業品牌的聯合(Seno&Lukas,2007)。由于聯合品牌的匹配類型會影響其聯合效用,因此,本研究以企業家代言(特指為他人品牌代言)為研究背景,從企業家代言匹配類型對其自我品牌及其所在企業品牌的效應。本研究的結論能有益補充名人代言和品牌聯合理論,并對企業家選擇何種類型的代言企業提供有效的實踐指導。
二、理論背景與假設推演
(一)名人代言
關于名人代言效用的研究,學界主要從以下三個視角展開了探討:信源可靠性、代言人-產品的匹配性以及代言傳播過程。代言人形象可作為一種信息線索影響消費者對廣告和代言產品的判斷(Erdogan,1999)。有吸引力的代言人憑借魅力的外在形象贏得消費者的喜愛,這種喜愛能轉移至代言品牌(Fleck,Korchia,Roy,2012;Kahle&Homer,1985)。吸引力形象不僅表現在外在的吸引力,高貴的身份、豐富的經歷、獨特的個性等方面也能體現吸引力(Singer,1983)。代言人的專業性和可信賴可通過增加感知的可靠性影響消費者對廣告的態度和購買意向,專業性主要體現在個人的專業知識、經驗和技能;可信賴表現在代言人的誠實、正直、可靠性等方面(Ohanian,1991)。Till& Busler(2000)基于關聯學習理論指出影響代言人與代言產品匹配性的兩個前置因素,即吸引力和專業性。這兩種匹配來源均會影響品牌態度、購買意向以及品牌信念,還指出相比基于吸引力的匹配性,基于專業性的匹配性對品牌態度的影響更大。認知和情感理論認為名人與代言品牌的一致性和名人的可愛性均會影響廣告態度,消費者對廣告的態度是先依據認知路徑對兩者的匹配性進行判斷,匹配性高的代言會激發消費者正面的情感,然后積極的情感反應會形成正面的品牌態度和廣告態度(Fleck,Korchia,Roy,2012)。企業家代言屬于名人代言中的一種類型(Newell& Shemwell,1995)。相比其他類型的代言人,企業家在消費者心中的形象是專業的、值得信賴的(Friedman,1977;Reidenbach &Pitts,1986)。產品類型會影響企業家的代言效用,當企業家選擇高風險產品代言,其代言效用會顯著高于其他類型的代言人;當其選擇低風險、低涉入度的產品代言時,有吸引力的名人代言的效用最佳(Maronick,2006)。從代言的傳播機制來看,企業家代言的作用機制也是相同的,消費者感知企業家的專業形象會轉移到代言品牌上,感知匹配的代言選擇會正向影響可靠性感知以及積極影響消費者對代言品牌的態度(McCracken,1989)。
先行文獻有兩點共性:其一,大量的文獻聚焦在影響代言品牌績效的前置因素:如,信源的可靠性、代言人與代言品牌的匹配性(Ohanian,1991;Till&Busler,2000);其二,探究名人代言效用的作用機制(McCracken,1989;Roy et al.,2012)。雖然已有文獻對代言品牌效用的前因和機制展開了詳實的探究,但基本缺失了對代言人效用的研究。名人代言的傳播過程是雙向互惠的(Halonen-Knight& Hurmerinta,2010)。消費者對代言品牌的態度會影響消費者對代言人的可靠性和專業性的評價,代言品牌的品牌資產也會影響消費者對代言人的評價(Doss,2011)。如果代言人為企業家時,那么代言效用還只是作用于代言品牌和企業家上嗎?企業家與企業品牌的緊密關聯是否能使企業家代言的溢出效用更加豐富呢?以及影響代言效用的前置因素和解釋機制能否適用于代言人效用嗎?針對這些問題,現有文獻都不能給出答案。因此,本研究認為以企業家代言為研究背景,尋找影響代言人效用產生的前因和繼續深入探討其他機制對豐富名人代言理論非常必要。
(二)品牌聯合
品牌聯合(co-branding)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獨立品牌在一段較長或較短的時間內的聯合或組合行動(Ruekert &Rao,1994)。品牌聯合能有助于提升各自的品牌資產、在同行的競爭能力以及降低企業新產品推廣的風險(Erevelles et al.,2008;Ahn et al.,2009;陸娟等,2009)。學界關于品牌聯合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聯合評價及其影響因素。品牌聯合的效用分為主效用(直接效應)和溢出效用(間接效應)(Helmig et al.,2008;范公廣等,2008)。主效用是指消費者對品牌聯合的評價(Helmig et al.,2008)。溢出效用是指品牌聯合戰略還能影響對合作品牌原有的態度(Simmon&Ruth,1998;Baumgarth,2004)。合作品牌的匹配性不僅會影響主效用而且還會影響溢出效應(Helmig et al.,2007,2008)。
盡管先行文獻已證實聯合匹配性對聯合品牌的作用,但不同模式的聯合,其聯合匹配性的內涵是不盡相同的。本研究是基于個人品牌與企業品牌的聯合模式,而且企業家個人品牌區別于企業品牌、慈善機構、贊助事件等,它是企業品牌形象與企業家個人形象的結合體。可見,以往文獻從品牌匹配和產品匹配不能有效解釋個人品牌與企業品牌的匹配類型對其聯合效應的影響。
(三)代言匹配類型與聯合效應的關系
盡管名人代言是雙向影響的觀點逐漸得到認同,但形象匹配性是互惠影響的前提(Halonen-Knight&Hurmerinta,2010)。形象匹配的廣告會正向影響消費者對代言品牌的態度(Lynch&Schuler,1994)。圖式理論表明形象匹配既可強化廣告記憶,又可增加消費者對名人特征的記憶(Misra &Beatty,1990)。Charbonneau&Garland(2011)以名人運動員代言煙草類產品為研究背景指出了名人代言的反向轉移過程,即代言產品形象會轉移到代言人(運動員)上。Seno&Lukas(2007)率先將名人代言理解為品牌聯合,并指出名人選擇代言的品牌形象會通過影響名人形象間接影響名人資產。名人資產的變化從品牌聯合視角來看屬于一種溢出效用,即名人代言的溢出效用。匹配性又是影響聯合溢出效用產生的前置因素。Till&Busler(1998,2000)整合了前人對名人代言匹配性的理解,提出兩種匹配方式:吸引力匹配指代言人基于個人吸引力特征與代言品牌的形象契合,即兩者“外形”是一致的;專業性匹配是指代言人基于個人專業性形象與代言品牌的形象契合,即兩者“內涵”是一致的。而且這兩種匹配方式都能正向影響品牌態度、購買意向以及品牌信念。本研究選用企業家為代言人,企業家外在的吸引力、個人身份、人格魅力、專業技能、成功經歷都可作為不同信息源契合代言品牌形象契合。匹配的企業家代言有助于強化消費者對其自身形象的記憶,進而提高消費者對企業家的態度。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1a:企業家代言吸引力匹配程度越高,消費者對企業家的態度越積極。
H1b:企業家代言專業性匹配程度越高,消費者對企業家的態度越積極。
消費者處理廣告信息通常采用兩種加工模式:認知處理和情感處理(Edell&Burke,1987),這兩種處理模式又稱冷系統和熱系統加工(Epstein,1994;Metcalfe&Mischel,1999)。認知處理是一種“冷”處理,是分析式、思考或理解式的處理方式;而情感處理是一種“熱”處理,是快速的、短暫的、情緒式的處理方式。不同的信息刺激會啟動消費者不同的處理模式,而信息處理模式又會影響個體對信息源的評價(Jeong,2008)。與認知系統響應相比,情感系統響應更容易獲得消費者積極的評價(Zhao,Hoeffler& Zauberman,2011)。但從信息加工努力程度來看,認知系統響應比情感系統響應影響消費者對信息的認知(理解、記憶)程度更深(Edell&Burke,1989)。代言人特質是一種信息線索。代言人的吸引力特質源于他(她)的身型、外貌、個性以及形象等,這些特質均會引發消費者正面的情感響應,如感知可愛性(Roy et al.,2012)。代言人的專業性形象來源于其經驗、知識以及專業技能等,這些特質較易引發消費者的認知系統響應,例如,專業性易引發消費者對代言人與代言品牌形象匹配性的分析(Fleck et al.,2012)。當企業家基于吸引力特質契合代言品牌的形象時,吸引力特質會激發消費者啟動情感加工,快速的情感反應會使消費者關注其個人特征。而基于專業性匹配的企業家代言會啟動消費者認知加工,理解式和分析式的認知反應會消費者投入更多的認知努力去思考代言動機和匹配性。鑒于企業家與自身企業品牌的獨特關聯,專業性匹配的廣告易啟動認知系統深入加工、處理企業家代言的廣告信息,由此專業性匹配的廣告效用能折射到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2a:企業家代言吸引力匹配程度越高,消費者對其所在企業品牌的態度無顯著變化。
H2b:企業家代言專業性匹配程度越高,消費者對其所在企業品牌的態度越積極。
現有研究大多以代言人形象與代言品牌形象的契合程度理解匹配性(Kirmani&Shiv,1998)。但企業家代言的匹配性僅憑借個人形象的契合是不夠的,企業家形象不僅與個人品質、魅力有關,還關聯到其企業的產品形象(何志毅、王廣福,2005)。本研究以企業家代言為研究背景,企業家的特殊身份有助于豐富對代言匹配性的理解,當企業家代言的產品與其自身企業產品的類別有關聯時,消費者可能感知的匹配性也越高。產品類別相關性表現在產品間的互補(相關)程度以及品類的一致性程度(Lanseng& Olsen,2012),而且能與品牌概念一致性共同作用于對品牌聯合的評價。企業家作為自身企業最佳的形象代言人,肩負著傳播企業品牌形象的使命(Zott&Huy,2007)。消費者對企業家形象有既定的認知,如果企業家的行為達到消費者的預期,感知的合理性會贏得消費者更多的積極評價(葛建華、馮云霞,2011)。企業家的代言選擇無論是基于吸引力匹配還是專業匹配,企業家的角色束縛了其代言選擇,只有合理管理個人行為才能獲得更積極的社會評價(Elsbach,1994)。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3a:當企業家代言產品與其所在企業產品的類別相關性越高時,企業家代言吸引力匹配程度越高(企業家代言專業匹配程度越高),消費者對企業家的態度越積極。
H3b:當企業家代言產品與其所在企業產品的類別相關性越低時,企業家代言吸引力匹配程度越高(企業家代言專業性匹配程度越高),消費者對企業家的態度無顯著變化。
企業家形象是個人形象和企業品牌形象的結合體(Bendisch et al.,2013)。企業家可以利用不同的形象面選擇代言企業,不同的形象來源可能產生的代言效用也會不同。Lanseng&Olsen(2012)發現品牌概念一致和產品類別一致對品牌聯合的評價機制是不一樣的,品牌概念一致的信息會啟動基于類別式的信息處理(category-based processing),而產品類別一致的信息是啟動基于漸進式的信息處理(piecemeal processing)。類別式處理是以主觀、抽象判斷為主、信息處理較淺;漸進式處理以客觀、具體信息為依據,信息處理程度更深度,需要更多的認知努力。企業家代言的匹配性無論從品牌聯合視角來看,還是企業家屬性,均包括了品牌形象層面和產品類別層面。當企業家代言企業與自身企業在產品類別關聯性較高時,漸進式的信息處理能使消費者投入更多的注意力關注到代言信息。其實,當兩者產品類別相關性較高時,無論是基于吸引力匹配還是專業性匹配,均會使消費者更加客觀、具體的處理廣告信息。這會有助于使廣告效用折射到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當企業家代言選擇產品類別的相關性較低時,消費者可能傾向選用類別式處理廣告信息,較淺層的信息處理導致消費者的注意力停留在代言人上。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4a:當企業家代言產品與其所在企業產品的類別相關性越高時,企業家代言吸引力匹配程度越高(企業家代言專業性匹配度越高),消費者對其所在企業品牌的態度越積極。
H4b:當企業家代言產品與其所在企業產品的類別相關性越低時,企業家代言吸引力匹配程度越高(企業家代言專業性匹配度越高),消費者對其所在企業品牌的態度無顯著變化。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模型與假設
三、實證研究
(一)預實驗1
1.預實驗目的。預實驗1的目的是挑選企業家形象與代言品牌形象匹配的實驗材料。該預實驗可以增加實驗的真實感,排除不匹配的實驗材料對正式實驗的干擾。
2.預實驗材料的選取。首先,收集企業家代言的真實素材,例如,王石為百年靈手表、大切諾基代言、俞敏洪為漢王電紙書代言、王健林為格力代言等;其次,對代言人的形象分類和挑選代言產品品類。結合代言人特質(Ohanian,1991)和企業家形象(Park&Berger,2004)的量表對廣告中的企業家形象進行分類以及確定代言產品的品類。這個環節主要通過營銷的3名教授、5名博士生以及6名碩士生對真實代言材料的反復討論。最后,確定代言人的人選和代言產品的品類。根據企業家形象特質和代言品牌形象特質選擇企業家和代言品牌形象。企業家分別為馬云、李彥宏、王石、周鴻祎、俞敏洪、王健林、李開復、江南春、任志強、馬化騰、雷軍和羅永浩。代言產品的品類分別是:電子產品、汽車、服裝、家電、手表、服務類。
3.操作過程。預實驗隨機挑選了50名在校生(以學術型研究生和MBA學員為主),男性28名,女性22名,年齡階段為18~40歲。要求他們根據自己的理解對企業家和企業家代言的品類的匹配性進行打分。每位被試需打分72次(12*6),按0~10分的標準打分,10分表示該企業家非常合適為該產品代言,0分表示非常不合適為該產品代言。
4.預實驗1的結果。50名被試分別對12名企業家代言的六類產品打分。72個代言選擇分別計算均值。結果顯示:得分最高的前五名分別是:王石代言汽車(8.59)、王石代言手表(8.55)、李彥宏代言電子產品(7.93)、周鴻祎代言汽車(7.91)、馬云代言電子產品(7.65)。鑒于匹配性的代言選擇的前十位結果中互聯網行業產品的企業家出現了八次。產品類別排在前十位中電子產品出現6次、手表和汽車出現4次。由此預實驗最終挑選互聯網行業的企業家作為正式實驗的代言人,并挑選手表和筆記本電腦作為代言產品。
(二)預實驗2
1.預實驗2的目的主要有三方面:其一,排除因測量問項的內容、措詞、形式、布局等問卷內容引起的測量誤差;其二,各測量量表的信效度檢驗(企業家態度、企業家所在企業的品牌態度等);其三,檢驗實驗情景設計的廣告內容(專業性匹配和吸引力匹配)是否能被消費者清晰的識別。
2.實驗素材的選取。首先,從各大門戶網站對企業家代言和名人代言廣告的介紹挑選實驗素材。其次,整理素材并確定實驗素材形式。材料整理和素材形式的確定是由5名營銷博士生共同完成。廣告形式主要由名人代言的介紹、代言人信息介紹以及代言產品或品牌的介紹三部分組成。再次,結合文獻以及現實廣告編寫實驗廣告內容。廣告內容主要涉及了代言公司的品牌知名度、品牌形象(品牌理念、品牌個性)、代言人形象特質(身材、外貌、個性、知名度)等信息。本研究的實驗情景主要依據了上述的信息內容和形式。在吸引力匹配的廣告材料中介紹了企業家的身材、外貌、個性、知名度和代言企業的品牌知名度、品牌形象(品牌理念、品牌個性)度等信息。在專業性匹配的代言廣告材料中展現企業家的教育背景、專業領域、專業成就、創業經歷和代言企業的品牌形象(品牌理念、品牌個性)等信息。
3.測量量表的確定。測量問卷項目的編制,本研究中對自變量、因變量的測量均采用成熟的量表。研究中所有量表均采用李克特7分量表。編制吸引力匹配和專業性匹配的量表主要依據Ohanian(1991)和Till&Busler(2000),根據本研究的情景對其量表進行了部分改編,最終形成了專業性匹配3個問項和吸引力匹配的3個問項。企業家態度和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態度主要依據MacKenzie&Lutz(1989)的量表,分別各有4個問項。
4.預實驗2的操作過程在預實驗2邀請了60名被試,其中男生32名,女生28名,年齡段為18~35歲。被試被告知這是一個廣告記憶的測試,要求他們閱讀一則廣告材料,然后回答問題。實驗開始前,首先詢問被試是否有接觸過企業家代言的廣告。如果被試沒有接觸過該類型的廣告的將不再進行下一步的調查。
5.預實驗2的結果。在60名被試中,有12名被試沒有接觸過企業家代言廣告信息,因此被剔除,剩余有效樣本數為48人。關于企業家態度和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態度的信度分析結果表明,其信度分別為0.796和0.809。信度結果說明該量表是可以接受的。由于量表是借鑒國外學者開發的成熟量表,因此具有較好的內容效度和聚合效度。關于“吸引力匹配”和“專業性匹配”的廣告信息操控檢驗。數據結果表明,當被試閱讀吸引力匹配的廣告材料時,M吸引力匹配=5.54,M專業性匹配=3.87(F=41.913,P<0.001);當被試閱讀專業性匹配的廣告材料時,M吸引力匹配=3.62,M專業性匹配=5.71(F=54.781,P<0.001)。由此可推斷,本研究所設計的實驗情景是能被消費者清晰的區分開。
(三)正式實驗1
實驗1的目的在于驗證企業家代言匹配類型與消費者對企業家的態度和其所在企業的品牌態度的關系,檢驗假設H1a、H1b和H2a、H2b。
1.實驗設計與被試。本實驗設計為兩個實驗組的組間因子設計。被試者對企業家吸引力匹配和專業性匹配的認知均通過實驗操控來實現。實驗1隨機邀請了50名消費者參加了本次實驗,回收有效問卷40份,有效率為80%。其中男性18名,占被試總數的45%,女性22名,占被試總數的55%。其中吸引力匹配問卷21份,專業性匹配組19份。為了排除被試對實驗目的迎合,被試并不知道實驗目的。被試被告知這是一次關于廣告記憶的消費者調查,實驗用時約8分鐘。
2.實驗操作過程。實驗將被試隨機分為兩組:“吸引力匹配”組,“專業性匹配”組。“吸引力匹配”組和“專業性匹配”組的被試分別閱讀一個企業家代言廣告的報道(虛擬的企業家名字)、企業家作為代言人的基本情況介紹以及代言企業品牌形象的介紹。隨后測量兩組被試對企業家代言匹配類型的判斷及對該企業家和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的評價。最后是人口統計學的問題。問卷中所有問項均來自成熟量表的改編。吸引力匹配、專業性匹配的問卷量表與預實驗相同,不再贅述。消費者對企業家的態度以及消費者對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的態度的測量,均采用MacKenzie &Lutz(1989)的量表,各4個問項。問項測量均采用李克特7級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
3.操控檢驗。通過對數據的分析,進一步證實了預實驗中對企業家代言匹配類型的分類。對于閱讀“吸引力匹配”材料的被試,方差分析的結果證明“吸引力匹配”組與“專業性匹配”組有明顯差異:M吸引力匹配=5.69,M專業性匹配= 3.98;F=52.211,P<0.001。對于閱讀“專業性匹配”材料的被試,分析的結果證明“吸引力匹配”組與“專業性匹配”組有明顯差異:M吸引力匹配=4.37,M專業性匹配=5.86;F=53.299,P<0.001。對問卷進行信度分析,測量變量吸引力匹配、專業性匹配、消費者對企業家的態度、消費者對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的態度的量表的Cronbach's ɑ系數分別為0.806、0.875、0.701、0.757,各變量的水平都非常高,說明數據結果可信。由于是借鑒國內外學者開發的成熟量表,且英文量表經過了雙盲翻譯,因此具有較好的內容效度和聚合效度。
4.假設檢驗。首先,我們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比較了消費者對基于不同匹配類型的廣告對企業家態度和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態度的評價。吸引力匹配和專業性匹配的廣告對消費者對評價企業家態度和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態度均有顯著性差異。詳細數據結果如下:當因變量為消費者對企業家態度的評價時,其均值分別為:M吸引力匹配=5.36,M專業性匹配=4.76(F=6.643,P<0.001),結果表明:消費者感知企業家不同匹配類型的代言對評價企業家的態度有顯著差異;當因變量為消費者對企業家自身企業品牌態度的評價時。均值分別為:M吸引力匹配=3.79,M專業性匹配=5.17(F=26.278,P<0.001),結果表明:消費者感知企業家不同匹配類型的代言對評價企業家自身企業品牌態度有顯著差異。然后,本研究采用回歸分析比較不同匹配類型的企業家廣告對影響消費者對企業家的態度與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的態度的影響。第一,將吸引力匹配和專業性匹配的得分作為自變量分別與消費者對企業家的態度進行回歸分析,數據結果如表1所示。第二,將吸引力匹配和專業性匹配作為自變量再分別與消費者對企業家所在企業的品牌態度進行回歸分析,數據結果如表2所示。
5.實驗1小結。實驗1的目的是檢驗消費者感知不同匹配類型的企業家代言對企業家態度以及企業家所在企業家品牌態度的影響。兩組實驗的數據表明,不同匹配類型企業家代言的溢出效果是有差異的。表1的兩個回歸分析結果表明:無論是企業家基于吸引力匹配還是基于專業性匹配都能顯著提升消費者對企業家態度的評價。表2的兩個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基于吸引力匹配的企業家代言對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態度并無顯著影響,而基于專業性匹配的企業家代言對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態度有顯著影響。由此可見,H1a、H1b、H2a、H2b假設均獲統計學意義上的支持。

表1 吸引力匹配、專業性匹配與企業家態度的回歸結果表

表2 吸引力匹配、專業性匹配與企業家自身企業品牌態度的回歸結果表
(四)正式實驗2
實驗2的目的在于驗證企業家代言的匹配類型和產品類別相關性的交互與消費者對企業家態度和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態度之間的關系。
1.實驗設計與被試。本實驗設計為2(企業家代言的匹配類型:基于吸引力匹配V.S.基于專業性匹配)×2(產品類別的關聯性:高V.S.低)四個實驗組的組間因子設計。被試對匹配類型、產品類別關聯性高、低均通過過操控來實現。實驗2邀請了90名MBA學員參加,其中男性53名,占被試總人數的58.8%;女性37名,占被試總人數的41.2%。被試被告知這是一次關于廣告記憶測試的問卷調查(廣告并未正式發行,代言人身份暫時不能對外公開,臉形模糊化處理),實驗用時約10分鐘。
2.實驗操作過程。實驗將被試隨機分為四組,“吸引力匹配、產品關聯度高”組,“吸引力匹配、產品關聯度低”組,“專業性匹配、產品關聯度高”組、“專業性匹配、產品關聯度高”組。被試分別閱讀一個企業家代言廣告的實驗材料(圖片見附錄),并附文字內容:企業家品牌代言介紹(虛擬的企業家名字:王總;虛擬的代言品牌:A公司)、企業家的外形基本介紹以及代言企業品牌的基本介紹(吸引力匹配:企業家的身高、外形、風格、知名度 /代言企業品牌的品牌理念、產品外型、產品使用者形象、品牌個性、品牌形象;專業性匹配:企業家的學歷、工作經驗、個人工作成就、職業經歷/代言企業品牌的品牌理念、產品技術特征、產品定位、品牌個性、品牌形象)。隨后測量四組被試對企業家代言匹配類型進行判斷及對該企業家和企業家自身企業品牌的態度進行評價。最后回答與被試人口統計特征的有關問題。
3.操控檢驗。通過對數據的分析,進一步證實了實驗一中對企業家代言匹配類型的分類。對于閱讀“吸引力匹配”材料的被試,方差分析的結果證明“吸引力匹配”組與“專業性匹配”組有明顯差異:M吸引力匹配=5.56,M專業性匹配=3.42;F=77.126,P<0.001。對于閱讀“專業性匹配”材料的被試,分析的結果證明“吸引力匹配”組與“專業性匹配”組有明顯差異:M吸引力匹配=3.21,M專業性匹配=5.54;F=140.779,P<0.001。對于閱讀“產品類別關聯性”(高 /低)材料的被試,方差分析的結果證明“產品類別關聯度高”組與“產品類別關聯度低”組有明顯差異:M高=5.17,M低=2.48;F=246.006,P<0.001。
4.假設檢驗。首先,我們采用雙因素方差分析檢驗匹配類型與產品類別關聯度的交互作用。企業家代言的匹配類型與產品類別關聯性的交互項對企業家態度和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態度的作用顯著。詳細結果如下:(a)消費者對企業家的評價。四組均值分別為M吸引力匹配-關聯高=5.29,M吸引力匹配-關聯度低=5.10,M專業性匹配-關聯高=4.67,M專業性匹配-關聯低=5.11,F=4.34,P=0.040,結果表明:企業家代言的匹配類型與產品類別關聯性的交互項對評價企業家的態度有顯著差異。(b)消費者對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態度的評價。四組均值分別為 M吸引力匹配-關聯高=5.06,M吸引力匹配-關聯度低=2.96,M專業性匹配-關聯高=4.69,M專業性匹配-關聯低=4.88,F= 53.988,P<0.001,結果表明:企業家代言的匹配類型與產品類別關聯性的交互項對評價企業家所在企業的品牌態度有顯著差異。其次,企業家代言的匹配類型和產品類別關聯度的交互項對消費者評價企業家態度和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態度有差異僅是驗證本研究假設的第一步,還須通過回歸分析探究交互項與企業家態度和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態度的相關關系。本研究繼續采用回歸分析驗證H3和H4的假設。產品類別關聯性調節吸引力匹配(專業性匹配)對企業家態度評價的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產品類別關聯性調節專業性匹配、吸引力匹配對企業家態度的回歸分析結果
回歸分析的結果表明吸引力匹配*產品類別關聯性交互項的回歸系數是顯著,而且其中模型1和模型2的R2改變的顯著性也分別0.000和0.015,由此可見產品關聯性調節吸引力匹配對企業家態度的影響是顯著的。專業性匹配*產品類別關聯性交互項的回歸系數也是顯著的,而且模型3和模型4的R2改變的顯著性也分別0.005和0.001,由此還可說明產品關聯性調節專業性匹配對企業家態度的影響是顯著的。本研究再通過不同調節水平下的簡單斜率點進行簡單斜率分析,斜率分析結果如圖2、圖3所示。

圖2 調節吸引力匹配對企業家態度的影響

圖3 調節專業性匹配對 企業家態度的影響
本研究繼續用回歸分析驗證產品類別關聯性調節吸引力匹配(專業性匹配)對企業家自身企業品牌態度的作用,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產品類別關聯性調節專業性匹配、吸引力匹配對企業家自身企業品牌態度的回歸分析結果
表4中模型1的吸引力匹配的主效應回歸分析并不顯著,P>0.05,該模型的R2改變的顯著性為0.193,但是模型2中的吸引力匹配*產品類別關聯性的交互項回歸系數,而且該模型的顯著R2改變的顯著性為0.001,則表明產品類別關聯性調節吸引力匹配對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態度的作用是顯著的。本研究再通過不同調節水平下簡單斜率點進行簡單斜率分析,斜率分析結果如圖4所示。模型3的專業性匹配的主效應系數是顯著的,專業性匹配*產品類別關聯性的交互項系數也是顯著的。而且模型3,4的R2改變的顯著性都小于0.05。由此可見,產品類別關聯性調節專業性匹配對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態度的影響是顯著的,簡單斜率分析結果如圖5所示。
5.實驗2小結。表3和表4的回歸結果表明,產品類別的關聯性分別正向調節吸引力匹配(專業性匹配)對企業家態度和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態度。當產品類別關聯性低的時候,吸引力匹配(專業性匹配)對企業家態度和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態度的影響均不顯著。由此可見,本研究的H3a、H3b、H4a和H4b均獲得驗證。

圖4 調節吸引力匹配對企業家自身企業品牌態度的影響

圖5 調節專業性匹配對企業家 自身企業品牌態度的影響
四、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以企業家為他人企業品牌代言為研究背景,從品牌聯合視角探究企業家代言匹配類型對其自我品牌及其所在企業品牌的效應。實驗1發現基于吸引力匹配的企業家代言能正向影響消費者對企業家態度的評價,但不能影響消費者對其自身企業品牌態度的評價,即“外形”一致的企業家代言選擇僅能產生“個人效用”;而基于專業性匹配的企業家代言不僅能正向影響消費者對企業家的態度,而且還能影響消費者對其自身企業品牌的態度,即“內涵”一致的企業家代言選擇不僅產生了“個人效用”,也對其所在企業品牌產生了“企業效用”;實驗2發現產品類別相關性能正向調節企業家代言匹配類型(吸引力匹配和專業性匹配)對企業家態度和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態度的影響。具體而言,當企業家代言產品與自身所在企業產品的類別相關性高時,基于吸引力匹配(專業性匹配)的企業家代言能正向影響消費者對企業家的態度以及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的態度;當企業家代言產品與自身所在企業產品的類別相關性低時,基于吸引力匹配(專業性匹配)的企業家代言對企業家的態度以及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的態度的影響均無顯著變化。研究結果表明,企業家代言的匹配類型、產品類別相關性能交互影響消費者對企業家的態度以及企業家所在企業品牌的態度。
(一)理論貢獻
1.發現了不同匹配類型的代言選擇對企業家代言自我效應的影響。本研究立足于代言行為對企業家的影響,探討了企業家與代言品牌的匹配類型對其個人以及所在企業品牌的影響。基于吸引力匹配的企業家代言僅能提升消費者對其個人的評價;基于專業性匹配的企業家代言不僅能提升消費者對其個人的評價而且還能提升消費者對其所在企業品牌的評價,其原因在于吸引力匹配會激發消費者啟動“熱”系統處理信息,這會引發他們較快地、感性地處理,導致廣告效用僅停留在代言人形象上;專業性匹配會激發消費者啟動“冷”系統處理信息,這會引發消費者分析式、理性地處理,因此積極的廣告態度不僅影響對個人形象的評價,而且還能折射出對其所在企業品牌的影響。
2.探明了產品類別關聯度與匹配類型的交互影響。代言匹配類型對企業家代言自我效應的影響受到了產品類別關聯度的調節作用。由于企業家為他人品牌代言區別于為自我品牌代言,所以本研究的結論能有益補充企業家前臺化行為和名人代言的相關研究,也為企業家為他人品牌代言的營銷實踐提供有用的啟示。
(二)管理啟示
1.企業家代言可遵循先“內涵”后“外形”的原則,即優先考慮專業匹配的代言選擇。由于企業家的專家身份最易關聯到其自身企業上。專家形象能引發消費者對其角色的聯想,間接引起對其企業品牌形象的聯想。而且以專家身份呈現的廣告更易激發消費者的認知系統響應,消費者會投入更多的認知資源處理專業性匹配的廣告,廣告效用會更豐富。可見,專業性匹配的企業家代言為其傳播品牌形象開辟了新的途徑。如果企業家僅憑個人知名度或有魅力外在形象選擇代言品牌時,那些吸引力特征較易引發消費者的情感反應。但這種情感響應是非常短暫的,導致廣告記憶只聚焦在代言人形象上。企業家是自身企業品牌的領導者,肩負傳播品牌理念的使命。因此,企業家應該優先選擇能突顯個人專家形象的品牌代言,再考慮與個人外在吸引力契合的品牌代言。盡管吸引力匹配也能宣傳企業家個人形象,但若能直接提升消費者對其所在企業品牌的態度那就更好,畢竟企業家代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2.企業家可以借助產品相關性拓寬代言選擇。消費者感知企業家形象的屬性包括企業家品質、企業家魅力和企業家與企業產品的關聯度。企業家與其企業產品是緊密關聯的。如果企業家選擇代言的產品與自身企業產品類別的相關性較高時,企業家的代言行為能激發消費者的認知系統響應。無論是吸引力匹配和專業性匹配的代言均能增加消費者對廣告信息的認知投入。信息加工程度越深越易強化消費者對廣告的記憶。企業家代言產品與自身企業產品類別越一致時,消費者會感知企業家代言的廣告也越可靠,積極的情感反應也會引發消費者對其自身企業品牌態度的正面評價。
(三)不足與未來研究方向
如所有實驗研究一樣,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處。(1)樣本選擇的問題。本研究的所選用的樣本量有限。本研究的外部效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2)實驗情景的問題。本研究以虛擬的代言人廣告為實驗素材,這與真實的代言評價可能存在部分差距,也可能與現實的廣告反應會有所差別。
盡管本文探究了匹配類型與溢出效用的關系,但在研究過程中并未詳細說明作用機制。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圍繞以下兩點進行深入探討:其一,探明企業家代言溢出效用的中介機制。盡管本研究依據信息處理中的認知和情感系統響應解釋企業家代言溢出效用差異的緣由,但是文中缺少數據證實解釋機制的合理性。其二,探討其他的調節變量。本研究從品牌聯合視角探究企業家代言的自我溢出效用,并發現了產品類別相關性的調節作用。在品牌聯合的文獻中,品牌關系、品牌知名度都會影響品牌聯合的溢出效用。可推測,企業家的知名度可能也會影響溢出效用。因此,在未來的研究可以繼續挖掘其他的調節變量豐富對企業家代言溢出效用的理解。
[1]Ahn S.,Kim,H.,Forney,J.A.Co-marketing Alliances Between Heterogeneous Industries:Examining Perceived Match-Up Effects in Product,Brand and Alliance Levels[J].Journal of Retailing&Consumer Services,2009,16(6).
[2]Ambroise,L.,Pantin-Sohier,G.,Valette-Florence,P.,Albert,N..From Endorsement to Celebrity Co-branding:Personality Transfer[J].Journal of Brand Management,2014,21(4):273-285.
[3]Bendisch,Larsen,Trueman.Fame And Fortune:A Conceptual Model Of CEO Brands[J].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2013,47(3/4):596-614.
[4]Charbonneau J.,Garland R..Product Effects on Endorser Image:The potential for reverse image Transfer [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2010,22(1):101-110.
[5]Doss,S..The Transference of Brand Attitude:The Effect on The Celebrity Endorser[J].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Research,2011,7(1):58-70.
[6]Edell,Julie,Marian Burke.The Impact of Feelings on Ad-Based Affect and Cognition[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87,26(2):69-83.
[7]Epstein S..Integration ofthe Cognitive and Psychodynamic Unconsciousness[J].American Psychologist,1994,49(8):709-724.
[8]Erdogan.Celebrity Endorsement:A Literature Review[J].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1999,15(4):291-314.
[9]Erevelles S.,Stevenson T.H.,Srinivasan S.,Fukawa N..An Analysis of B2B Ingredient Co-branding Relationships[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08,37(8).
[10]Friedman H.H.Endorser Effectiveness as A Function of Product Type[D].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77.
[11]Gwinner.A Model of Image Creation and Image Transfer in Event Sponsorship[J].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1997,14(3):145-158.
[12]Halonen-Knight E.,Hurmerinta L..Who Endorses Whom?Meanings Transfer in Celebrity Endorsement[J].Journal of Product&Brand Management,2010,19(6):452-460.
[13]Helmig B.,Huber J.-A.,Leeflang P..Explaining Behavioural Intentions toward Co-branded Products[J].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2007,23(3/4):285-304.
[14]Helmig B.,Huber J.-A.,Leeflang P.S.H..Co-Branding:The State of the Art[J].Schmalenbach Business Review,2008,60(4):359-377.
[15]Ilicic,Webster.Celebrity Co-branding Partners As Irrelevant Brand Information In Advertisement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3,66(7):941-947.
[16]Jeong S.H..Visual Metaphor in Advertising:is the Persuasive Effect Attributable to Visual Argumentation or Metaphorical Rhetoric?[J]. Journal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2008,14(1):59-73.
[17]Kahle L.R.,Homer P.M..Physical Attractiveness of the Celebrity Endorser:A Social Sdaptation Perspective[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1985,11(4):954-961.
[18]Kirmani A.,Shiv B..Effects of Source Congruity on Brand Attitudes and Beliefs:the Moderating Role of Issue-relevant Elaboration[J].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1998,7(1):25-47.
[19]Lanseng E.J.,Olsen L.E..Brand Alliances:the Role of Brand Concept Consistency[J].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2012,46(9):1108-1126.
[20]Lynch J.,Schuler D..The Matchup Effect of Spokesperson and Product Congruency:ASchemaTheoryInterpretation[J].Psychology&Marketing,1994,11(5):417-445.
[21]Maronick T.J..Celebrity Versus Company President as Endorsers of High Risk Products for Elderly Consumers[J].Journal of Promotion Management,2006,11(4):63-80.
[22]McCracken.Who Is The Celebrity Endorser?Cultural Foundations Of The Endorsement Process[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1989,16(3):310-321.
[23]Metcalfe J.,Mischel W..Hot/Cool-System Analysisof Delay of Gratification:Dynamics of Willpower[J].Psychological Review,1999,106(1):3-19.
[24]Misra S.,Beatty S.E..Celebrity Spokesperson and Brand Congruence:An Assessment of Recall and Affect[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1990,21(2):159-173.
[25]Newella,Shemwell.The CEOEndorser and Message Source Credibility: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J]. 1995,1(1):13-23.
[26]Ohanian R..The Impact of Celebrity Spokespersons'Perceived Image on Consumers'Intention to Purchase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of the Celebrity Endorser:A social adaptation perspective[J].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1991,31(1):46-54
[27]Park D.J.,Berger B.K.The Presentation of CEOs in the Press,1990-2000:Increasing Salience,Positive Valence and a Focus on Competencyand Personal Dimensions of Image[J].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2004,16(1):93-125.
[28]Rao A.R.,Qu L.,Ruekert R.W..Brand Alliances as Signals of Product Quality[J].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1994,36(1):87-97.
[29]Reidenbach R.E.,Pitts R.E..Not all CEOs are created Equal as AdvertisingSpokespersons:Evaluatingthe Effective CEO Spokesperson [J].Journal of Advertising,1986,15(1):30-46.
[30]Roy S.,Gammoh B.S.,Koh A.C.Predi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elebrity Endorsements Using the Balance Theory[J].Journal of Customer Behaviour,2012,11(1):33-52.
[31]Roy S.,Y.L.R.Moorthi.Investigating Endorser Personality Effects on Brand Personality:Causation and Reverse Causation in India[J]. Journal of Brand Strategy,2012,1(2):164-179.
[32]Seno D,Lukas B A.The equity effect of product endorsement by celebrities:A conceptual framework from a co-branding perspective [J].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2007,41(1/2):121-134.
[33]Simonin B.L.,Ruth J.A..Is a Company Known by the Company it Keeps?Assessing the SpilloverEffectsofBrand Alliances on Consumer Brand Attitudes[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98,35(1):30-42. [34]Singer B D.The Case for Using'Real People'in Advertising[J]. Business Quarterly,1983,48(4):32-37.
[35]Till B.D.,Busler M..Matching Products With Endorsers:Attractiveness versus Expertise[J].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1998,15(6):576-586.
[36]Till B.D.,Busler M..The Match-up Hypothesis:Physical Attractiveness,Expertise,and the Role of Fit on Brand attitude,Purchase Intent and Brand Beliefs[J].Journal of Advertising,2000,29(3):1-13.
[37]Zhao M.,Hoeffler S.,Zauberman G..Mental Simulation and Product Evaluation:The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Dimensionsof Process Versus Outcome Simulation[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2011,48(5):827-839.
[38]Zott C.,Huy Q.N..How Entrepreneurs Use Symbolic Management to Acquire Resource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7,52(1):70-105.
[39]范公廣,吳芳,周春元.品牌聯合匹配性與品牌聯合效應關系的調節因素研究[J].技術經濟,2008,27(10):108-113.
[40]葛建華,馮云霞.企業家公眾形象,媒體呈現與認知合法性——基于中國民營企業的探索性實證分析[J].經濟管理,2011,483(3):101-107.
[41]何志毅,王廣富.企業家形象與企業品牌形象的關系[J].經濟管理,2015,7(15):47-50.
[42]黃靜,熊小明,周南.企業家代言的自我效應影響因素研究[J].管理學報,2015,12(5):757-764.
[43]陸娟,邊雅靜,吳芳,2009.品牌聯合的消費者評價及其影響因素:基于二維結構的實證分析[J].管理世界(10):115-125.
[44]吳芳,陸娟.聯合匹配性對聯合品牌評價的影響研究[J].杭州:商業經濟與管理,2010,225(7):64-71.
[45]朱麗婭,黃靜,童澤林,2014.企業家前臺化行為對品牌的影響述評[J].中國軟科學(1):171-179.
(責任編輯:C 校對:R)
F713.55;F272.91
A
1004-2768(2016)09-0115-08
2016-06-20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1172207)
林濤(1973-),男,浙江泰順人,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品牌管理;熊小明(1986-),男,江西南昌人,博士,江西師范大學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品牌管理;郭昱瑯(1986-),男,湖南株洲人,博士,廣東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品牌管理。熊小明為通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