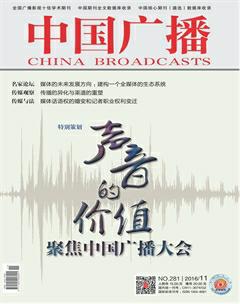扎實采訪 大膽創(chuàng)新 主題先行
王健
【摘要】第二十屆麥魯利奇獎(20th Prix Marulic)于2016年5月21日~ 27日在克羅地亞赫瓦爾島(Hvar)舉行。經(jīng)過初評,來自全球30多個國家的近50部作品殺入最終的評選環(huán)節(jié),在“短節(jié)目”“廣播特寫”和“廣播劇”三個類別中展開激烈競爭。本文從“扎實采訪”“大膽創(chuàng)新”和“主題先行”三個方面解析本屆入圍作品的特點和成功之道。
【關(guān)鍵詞】麥魯利奇獎 主題 古典再現(xiàn) 創(chuàng)新 新媒體 廣播品質(zhì)
【中圖分類號】G222 【文獻標(biāo)識碼】C
縱觀第二十屆麥魯利奇獎(以下簡稱“麥獎”)的入圍作品和最終獲獎作品的風(fēng)格和特點,“扎實采訪”“大膽創(chuàng)新”和“主題先行”成為了各國作品的共同交集,麥獎評委會在評選環(huán)節(jié)也高度重視作品中的這些元素。作為本屆麥魯利奇獎的評委會成員,本人將分別就這三個特點作出解析,為我國廣播節(jié)目創(chuàng)作者提供有益借鑒。
鼓勵扎實采訪
在“短節(jié)目”和“廣播特寫”類別中,“扎實采訪”成為參評作品一個突出的特點。許多創(chuàng)作者通過廣泛深入的挖掘,遍訪相關(guān)人員,占據(jù)豐富的材料。更有主創(chuàng)人員為了掌握細節(jié),長途跋涉、不辭辛勞,使廣播作品內(nèi)容和音響都極其豐富。
在廣播特寫中,內(nèi)容豐富詳實的作品大量涌現(xiàn)。例如:東道主克羅地亞選送的作品《久違的山堡》(The Long Lost Hillfort)中,記者千里迢迢趕赴一座荒廢多個世紀的城堡,在城堡中找尋失落的文明,探尋自然之美,暢想當(dāng)年城堡守軍走過的心路歷程。采訪過程中,原始森林的陰郁、毒蛇和蚊蟲的困擾、深一腳淺一腳的道路和幾個世紀來關(guān)于城堡的種種傳說,都成為記者采訪途中的攔路虎。整個節(jié)目時長約40分鐘,記錄了記者長途跋涉和探尋的過程,其中的甘苦讓人感動。
德國選送的作品《魔笛歸來——蒙古公路電影》(The Return of the Magic Flute – Mongolian Road Movie)記載了一位德國女士不遠萬里趕赴蒙古國尋找父母足跡的故事。這位女士的家中有一支用骨頭磨制的笛子。二戰(zhàn)期間,女士的父母在蒙古生活,艱辛卻快樂。時至今日,女士的父母都不在了,這位女士卻不斷追憶父母在蒙古生活的那段經(jīng)歷,希望能夠了解更多,同時希望找尋到笛子的主人。在一路探尋的過程中,記者與女士偕行,公路、鐵路、航班、馬車……一路走一路問,采訪的內(nèi)容扎實,音響極其豐富。
德國選送的另一部作品《摩洛哥:德國冬天的故事》(Morocco:A German Winters Tale),講述的是德國人到摩洛哥過冬的故事。每年冬天,大批德國人開車涌入摩洛哥,在這個北非小國度假。盡管在漫長的冬天里德國游客和他們所雇傭的摩洛哥仆人往往有著較好的關(guān)系,但西方人良好的自我感覺和高人一等的態(tài)度,依然在交流中很明顯地流露出來。作品中,記者通過大量采訪和原生態(tài)錄音,呈現(xiàn)了這種不平等關(guān)系。據(jù)了解,為了客觀呈現(xiàn)德國游客與摩洛哥人的真實交流,記者深入摩洛哥多地,與許多德國家庭交流溝通,甚至一起生活,掌握了第一手材料,讓最終的作品更具有說服力。
伊朗選送的作品《游牧歌手》(Ashiks),真實呈現(xiàn)了伊朗游牧歌手的生存形態(tài),反映了藝術(shù)源于生活的現(xiàn)實,介紹了一大批游牧歌手的生活現(xiàn)狀和心路歷程,也向世界介紹了伊朗游牧民歌這種古老的藝術(shù)形式。采訪中,記者驅(qū)車數(shù)百公里,采訪十幾位游牧民歌藝人,讓他們講述游牧民歌背后的故事、民間的傳說,讓他們現(xiàn)場表演,呈現(xiàn)伊朗民間歌曲的原生態(tài)。這些內(nèi)容有機結(jié)合,使節(jié)目產(chǎn)生極大的沖擊力。夾敘夾議、有說有唱的節(jié)目內(nèi)容,假若沒有大量采訪素材做支撐,很難取得良好效果。
扎實采訪不僅體現(xiàn)在“廣播特寫”的作品類別中,也體現(xiàn)在“短節(jié)目”甚至“廣播劇”類別中。扎實采訪的內(nèi)涵也不僅體現(xiàn)在創(chuàng)作者多次實地走訪,更體現(xiàn)在作品素材的廣泛挖掘上,許多作品都是創(chuàng)作者在占據(jù)了大量詳實資料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作而成的。如:克羅地亞選送作品《1914前》(1914 and beyond),捷克選送的作品《大地死寂》(Even the Ground was Dead),德國選送的作品《向著尚卡里——作曲家和大屠殺》(On the way to Chankiri – The Composer and the Genecide),反映的都是戰(zhàn)爭主題。無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還是種族屠殺,都已歷史久遠。作者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廣泛而深入地挖掘素材,尤其是聲音素材的挖掘難度極大,需要作者下苦工,廣泛找尋材料,遍訪歷史見證者和史學(xué)家。事實證明,每一滴汗水都會讓節(jié)目更豐富、音響更生動、效果更明顯,這三篇作品都取得了良好的收聽效果。這些成功的例子也從一個側(cè)面說明,廣播雖然是低成本運作,但創(chuàng)作者要盡可能貼近實際、廣泛尋找素材,最終的作品才能打動人。
鼓勵大膽創(chuàng)新
在本屆麥魯利奇獎的評選中,許多入圍作品都讓人眼前一亮、腦洞大開。
麥魯利奇獎的主題是“經(jīng)典再現(xiàn)”,因此出現(xiàn)了一大批闡釋經(jīng)典、回顧歷史的作品。但與此同時,這并不影響廣播作品的創(chuàng)新。一大批形式和內(nèi)容大膽創(chuàng)新的作品,得到各國評委的肯定。例如:加拿大參評作品《旗手四重奏》(The Bannerman Quartet),把廣播劇植入手機客戶端(App)。作品植根于加拿大一個城市公園,從A、B、C、D四個公園入口進入時,打開手機客戶端和定位,隨機走入相應(yīng)區(qū)域就會觸發(fā)播放相應(yīng)的廣播劇。這部作品獲得了評委們的一致好評。在新媒體沖擊下,廣播如何借助新媒體手段突破瓶頸是重要課題。四段廣播劇植入手機客戶端的想法雖然簡單,但卻將節(jié)目內(nèi)容與手機定位系統(tǒng)聯(lián)系起來,這是一種有益的嘗試。這個作品獲得了本屆麥魯利奇獎的特別成就獎,以鼓勵更多廣播人在新媒體領(lǐng)域的創(chuàng)新。
立陶宛參評作品《機器人為你讀詩》(Robots Reading VYDUNAS),把詩歌輸入電腦,并通過電腦語音編碼識別的方式讀出詩歌。這一創(chuàng)新嘗試盡管未能獲獎,但用機器表達詩歌中呈現(xiàn)的人類情感,卻是前人未有的一次嘗試,獲得各國評委的一致鼓勵。事實上,一首優(yōu)美的詩歌經(jīng)由機器編碼后再通過電腦讀出來,只是一組聲音的集合,未必能聽出編碼背后的含義,更談不上詩歌所能呈現(xiàn)的人類情感。但這不正是作者所要表達的“現(xiàn)代社會和信息時代導(dǎo)致人類情感日漸疏離”的主題嗎?當(dāng)下,當(dāng)人們探討社交軟件和智能手機一方面讓人遠距離交流成為現(xiàn)實,卻在另一方面讓面對面交流和溝通變得更加困難時,這樣的廣播作品無疑能夠引發(fā)人們更深層次的思考。
前文所提及的東道主克羅地亞送評作品《1914前》(1914 and beyond)也呈現(xiàn)出鮮明的創(chuàng)新品質(zhì)。主創(chuàng)人員把有關(guān)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素材加以搜集整理,并通過整合音響的方式大膽串聯(lián),以傳遞反戰(zhàn)主題。1914年距今超過了一個世紀,可以想見通過聲音去反映一個世紀前的歷史多么地困難。為了制作這部短作品,制作團隊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成本,才讓作品得以最終誕生。與此同時,毫不相干的聲音元素怎樣組織起來傳遞主題,依然是創(chuàng)作團隊頗為頭疼的問題。最終的作品以印象派的風(fēng)格呈現(xiàn),讓聽眾從聽覺感官中去感受一戰(zhàn)前后的情緒和令人震顫的氣氛,作品中時而雜亂的聲音交織在一起,時而沉重或刺耳的聲音出現(xiàn),時而出現(xiàn)人的聲音,各種聲音交織,呈現(xiàn)作者心中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印象。這部作品最終獲得了短節(jié)目的一等獎。
塞爾維亞送評作品《達達主義100年》(Dada 100)是一部探討達達主義究竟是什么的作品。整個作品自始至終貫穿“什么是達達”(What is Dada)的問題,但直至節(jié)目結(jié)束也未明確予以回答。然而當(dāng)聽眾聽完整個節(jié)目后,略加思索就能夠明白,達達主義本身就是一種略帶虛幻的無政府主義現(xiàn)象。整部作品以自身的風(fēng)格答復(fù)了疑問,這一新穎的闡釋主題的方式也獲得了評委的好評。
創(chuàng)新不僅體現(xiàn)在形式上,還廣泛存在于內(nèi)容層面,大膽的創(chuàng)新總能獲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和評委的好評。例如:澳大利亞選送的廣播劇《親愛的契訶夫》(Dear Dr. Chekhov),把生活在同一年代卻毫無交集的兩個人物——俄羅斯文學(xué)家契訶夫與澳大利亞女孩聯(lián)系在一起,以通信的方式讓兩人發(fā)生交集,闡釋生活永恒的主題。當(dāng)然,這樣的虛構(gòu)需要精心的策劃和細致的安排,只有契合兩人各自風(fēng)格的語言才會讓聽眾有代入感,也只有細致入微的刻畫才能讓兩人的性格完整呈現(xiàn)。為了制作這部作品,創(chuàng)作者做了大量案頭工作,同時大膽發(fā)揮想象力,讓作品成為引人入勝的廣播劇。
英國送評廣播劇《俄耳甫斯和歐律狄刻》(Orpheus and Eurydice),把古希臘神話中的愛情故事放到今天的時代背景下。作品中,俄耳浦斯不再是神話中的人物,而成為了一位屢出白金唱片的流行歌手。而他和歐律狄刻的愛情,卻受到大眾無孔不入的關(guān)注和干擾。這一大膽創(chuàng)新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最終獲得了廣播劇一等獎。
鼓勵主題先行
“主題先行”是本次麥魯利奇獎的參評作品的另一大特點。一部分作品契合了當(dāng)今世界“和平與發(fā)展”的主題。例如:2014年全球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100周年,各個類別中都有回顧和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作品。短節(jié)目類別中的一等獎,就是一部反映“一戰(zhàn)”主題的作品。與此同時,反映二戰(zhàn)主題的作品也不少。廣播特寫類別的一等獎,最終被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獲得。這部名為《失物招領(lǐng)法則——奧斯維辛小路上的佛教默想》(Laws of Lost and Found Objects)的作品,記錄了作者前往奧斯維辛集中營參加“見證靜修”之旅的經(jīng)歷。作者之所以前往集中營,是因為自己的母親作為一名猶太人曾經(jīng)在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輾轉(zhuǎn)幾大洲,最終逃離危險。盡管母親很少談及自己的經(jīng)歷,但女兒還是能夠感受到母親心中深藏的情感。在前往集中營探尋途中,女兒幾次給母親打電話,通過電話里的交流,母親漸漸打開心門,講述了自己的一些經(jīng)歷和感受。但唯有作者本人深入集中營,才深切地感受到母親內(nèi)心的不平靜和智慧的人生感悟。
和采訪普通人不同,采訪自己的母親既容易又艱難。之所以說“容易”是因為母親不會拒絕采訪;而說它“艱難”就在于盡管多年過去了,但再度提起傷心事,還是要揭傷疤。這篇作品最終之所以獲得一等獎,也是因為它獨特的采訪對象和真實情感的自然流露,以及作者從絕對私密的個人體驗中找尋到的極具普遍指導(dǎo)價值的人生哲理。可以想見,假若作品只是簡單介紹集中營參觀之旅,很難獲得廣播特寫的一等獎。
主題先行的第二個顯著特點在于,許多作品都深深扎根于歐洲的文化根基,深挖“文化元素”,在評委中引起較強的共鳴,例如:《達達主義100周年》《親愛的契訶夫》《弗洛伊德》等,都回過頭去解析文化人物或文化現(xiàn)象。盡管歐洲文化五彩斑斕,東西歐各有不同,南北歐各有差異,但畢竟同根同源,往往引發(fā)評委較強反響。而文化主題的探索正契合了麥獎“古典重現(xiàn)”的主題。
當(dāng)然,許多作品還圍繞人類共同關(guān)心的主題,深入挖掘種族歧視、殖民主義、親子關(guān)系、文明消逝、宗教傳播等話題。如伊朗選送的《游牧歌手》(Ashiks)、土耳其選送的《喉音》(Throat Airs)、克羅地亞選送的《游牧者之歌》(Travellers Singing)等,反應(yīng)了現(xiàn)代社會面臨的共同問題。
綜上所述,“扎實采訪”“大膽創(chuàng)新”和“主題先行”成為本屆麥魯利奇獎最鮮明的特色,這也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國際主流廣播獎的評選標(biāo)準(zhǔn)。事實上,這樣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同樣是我國廣播從業(yè)者所注重的。希望通過介紹,我國的廣播從業(yè)者能夠更多地了解麥魯利奇獎,了解國外廣播作品的現(xiàn)狀,取長補短,推動我國廣播節(jié)目質(zhì)量再上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