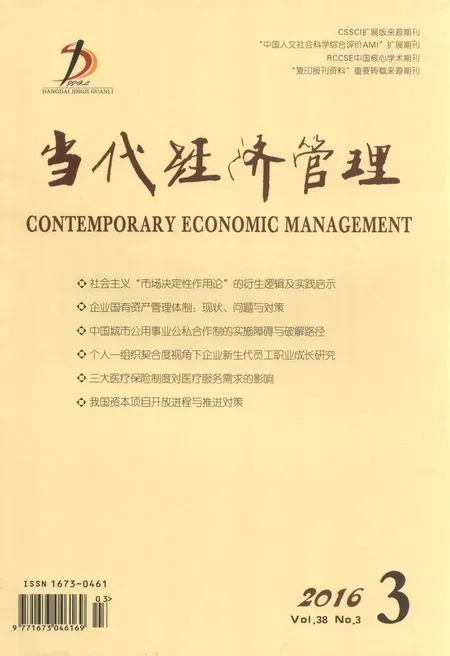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的衍生邏輯及實踐啟示
徐俊峰(1. 南京大學經濟學院,江蘇南京210093;2. 上海政法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201701)
?
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的衍生邏輯及實踐啟示
徐俊峰1,2
(1. 南京大學經濟學院,江蘇南京210093;2. 上海政法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201701)
[摘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理論突破,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的衍生。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淵源于馬克思的“無市場”、“近市場”、“親市場”等理論學說,生成了“反市場——近市場——親市場”邏輯路徑,歷經了政府模擬市場、政府聯姻市場、市場主導型、市場決定型等模式演進,積累了諸多經驗教訓,啟示我們必須兼顧社會主義與市場的二維創新與博弈層次;探索政府與市場互補結構;整合市場因素與非市場因素合力,豐富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邏輯溯源;實踐啟示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理論突破,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的衍生,預示了“市場決定性作用論”實踐的長期性、復雜性、挑戰性。因此,回溯社會主義探索“市場決定性作用”的理論淵源、循環邏輯、模式形態、借鑒啟示等,對我們探索“市場決定性作用論”的實踐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一、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衍生的理論淵源
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淵源于馬克思的“無市場、近市場、“親市場”等理論學說,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近市場、親市場、無市場”的屬性論述,是社會主義與市場博弈的邏輯淵源。
(一)社會主義“近市場”的本源屬性
馬克思“市場起源論”認為,社會主義擁有“近市場”的本源屬性,同時又具有“近市場”的制度屬性,是客觀性與本源性的統一。
1.社會主義與市場的天然互補性
社會主義與市場天然互補屬性蘊含在馬克思市場起源的理論判斷中。馬克思堅持市場起源于社會組織的“市場社會論”觀點,反對西方古典經濟學家的市場起源于人類交換傾向的“市場人性論”觀點。馬克思認為,最初的商品交換“不是在原始公社內部出現的,而是在它的盡頭,在它的邊界上,在它和其它公社接觸的少數地點出現的”。[1]即市場起源于社會制度的本源屬性,而不是由人的自然屬性產生并自然滿足社會發展的基本觀點,蘊含了市場可以與任何社會制度或社會組織進行結合的可能,自然也預示了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結合的本源屬性。同時馬克思也指明了市場與社會分工相互促進的積極作用。馬克思認為,“在商品生產者的社會里”,獨立生產者的勞動最終“發展成一個多支的體系,發展成社會分工”,進而不斷推動市場范圍的擴大;[2]肯定了市場與社會雙向互動功能。暗示了任何一個社會制度只要存在社會分工與剩余產品,市場交換生成的邏輯前提就存在;在社會分工存在并不斷拓展的情況下,產品交換的領域不斷擴大,交換的類型也不斷復雜化、精細化,只要市場對社會的促進屬性存在,其依附于社會的本源屬性就不會喪失。因此,具有先進制度屬性的社會主義同樣脫離不了社會分工的存在,自然擁有與市場結合的互補性。
2.社會主義與市場的客觀相容性
社會主義與市場的客觀相容性是由社會主義制度屬性所決定的。一方面,社會主義既具有一切社會制度的共同屬性,即必須建構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之上,同時又滿足人訴求的政治文化社會有機體,必然與市場促進社會有機體屬性具有相容性。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又具有獨特的制度屬性。按照馬克思的設想,社會主義是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物質生產力基礎之上,又在精神追求、社會公正、文化繁榮等方面超越資本主義的新型制度,在經濟層面與道義層面均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其核心價值目標是給人提供豐厚的物質基礎和豐足的精神財富,讓人類享有自然權利和社會權利的高度統一,最終實現“自由人聯合體”。因此,社會主義制度屬性決定其必然需要借助于一切能夠滿足其發展需求的機制,市場機制的優勢屬性能確保社會主義獲取未來發展的物質條件與精神追求,而其自身固有的優越屬性也為限制市場劣根性提供了屏障。因此,社會主義仍然擁有利用市場的客觀必然性,同時也擁有促進市場優化的天然優越性。
總之,馬克思關于市場起源與社會主義制度屬性的基本判斷表明,社會主義與市場具有本源的相容性,構成了社會主義探索“市場決定性作用”問題的邏輯源頭。
(二)社會主義“親市場”的內質屬性
1.未來社會“無市場”的理論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制度“無市場”的制度設計是共產主義社會,而這種共產主義社會是直接針對物質條件、精神財富高度發達的“高級階段的共產主義”,并非是“各方面尚未成熟”的共產主義低級階段。
馬克思在客觀分析市場起源、市場要素、市場機制、市場功能、市場分類等的基礎上,明確肯定了市場促進社會生產力的優勢功能;同時也對市場蘊含了劣勢屬性功能進行了深入的批判。馬克思繼承發展了空想社會主義的市場批判思想,透視市場與私有制結合等產生的社會不公、拜物教現象、不當競爭、市場失靈、市場滯后性等問題,揭示了市場與私有制、個人主義等客觀兼容性,看到了市場產生的人性異化、優勝劣汰、兩極分化、極端趨利性等,預測了未來社會是“無市場”的社會制度;但根據馬克思后來關于社會主義的論述可知,在其尚未實現高階段共產主義之前,社會主義必然不可避免帶有其原有社會的特征,甚至可以包括商品貨幣、銀行的、利息、利潤等。由此可知,“無市場”的未來制度必然是高級階段的共產主義社會。
2.社會主義“親市場”的必然性
在馬克思的理論視域中,社會主義“親市場”的屬性是暫時的,是其過渡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必要條件,社會主義必然會通過“去市場”的途徑實現“無市場”的未來社會制度。因為馬克思的設計要求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精神基礎、政治文明、社會素養等綜合的實踐條件。當社會主義社會具備了實現共產主義需求的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素養等,市場也就無需再發揮職能,或許會轉化為另外一種形態,市場就自然退出歷史舞臺,社會主義自然過渡到“無市場”的共產主義社會。當然,如果實踐中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具備“無市場”的制度條件,就應該保留其實踐中的市場制度屬性以不斷提升社會主義制度的綜合條件,為其向未來社會的過渡與發展創造條件。因此,實踐中的社會主義制度又具有“親市場”的應然屬性,否則就不能實現“無市場”的高級階段共產主義社會。
由此可知,馬克思的理論視域中既蘊含了社會主義“去市場”的應然性,又蘊含了社會主義“親市場”的必然性,只有等條件成熟的時候才能實現未來社會主義的“無市場”性。
二、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衍生的邏輯路徑
社會主義探索“市場決定性作用”問題歷經邏輯起點、邏輯展開、邏輯升華等階段,完成了“反市場——近市場——親市場”的邏輯循環,建構了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的理論實踐。
(一)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生成的邏輯起點
指早期社會主義的反市場實踐與市場理論矛盾徘徊,孕育了社會主義市場本位探索建構的實踐先兆。主要包括蘇聯及早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建構計劃經濟主導以排斥市場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
早期蘇東社會主義者對馬克思未來社會制度“無市場”目標設定的誤解,忽視了社會主義“去市場”條件,混淆了共產主義“廢市場”與社會主義“去市場”的根本區別,把“去市場”理論等同于“廢市場”理論,走向了“反市場”的社會實踐,衍生了社會主義排斥市場的通行模式。在實踐中主要以排斥市場為核心手段,建構了絕對公有制所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試圖建構替代市場經濟的實踐超越,進而衍生了與計劃經濟呼應的政治、文化社會體制等。但事實上該模式卻是在計劃經濟主導下的市場矛盾狀態。一方面,政府試圖運用行政手段取消市場以及與之相適應的運營機制,在理論意義上建構了排斥市場的形態,如列寧曾設想在“世界幾個大城市”的主要街道“用黃金修建公用廁所”的絕對反市場設計。[3]另一方面,在經濟實踐中又不得已采取保留部分市場的制度形態,如貨幣、經濟核算、價格信息、價值規律等,試圖借助貨幣實現“經濟計量的尺度、所得的分配和企業結賬的手段”、“支付個人及家庭生活費用,獲得消費資料及服務”等;尤其是在國際中必然借“黃金和美元”等國際貨幣在世界市場中進行“貿易交換和貿易結算”等,凸顯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的實踐不可分割性。[4]
因此,早期社會主義反市場的實踐范式驗證了馬克思“去市場”的正確性,為社會主義“近市場”屬性埋下了伏筆,預示了“市場決定性作用論”建構的理論起點。
(二)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生成的邏輯主體
主要是指20世紀50年代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開辟的“近市場”實踐探索,實現了社會主義與市場解構聯姻的理論突破,以南斯拉夫、匈牙利等為代表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率先揭開了探索與市場聯姻的兼容之路。
東歐傳統社會主義國家試圖回歸市場在社會主義應有的地位,但由于當時社會主義矛盾尚未充分實踐以及世界格局的制約影響,大多是設想在計劃經濟的框架中植入市場經濟的成分,實現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的結構聯姻,大大促進了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如南斯拉夫、匈牙利的實踐探索,東歐其他國家的理論探索等,曾被西方國家稱之為市場社會主義,對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是其重要的理論實踐奠基時期。
但由于其大多是在傳統社會主義框架內植入市場經濟的內核,但社會主義仍然是主導地位,恢復了社會主義“近市場”的自然屬性;但其未能真正調整市場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市場經濟在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也進一步激化了市場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如政府與市場的矛盾、企業與市場的矛盾、社會與市場的矛盾等問題凸顯,這些矛盾表面看是改革帶來的矛盾,實際卻是市場主體地位未能復歸衍生的必然矛盾,再加上蘇聯的強力壓迫等因素,這種探索并未真正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實踐探索由此而中斷。
(三)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生成的邏輯升華
主要是指20世紀90年代蘇東社會主義解體以來,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與左翼作家的探索設計;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實踐,尤其“市場在社會主義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提出,完成了社會主義與市場博弈的邏輯循環。
蘇東社會主義國家探索社會主義近市場的路徑中斷之后,社會主義市場本位問題的建構任務被歐美當代市場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承擔。當代市場社會主義主要以英美國家為主導,把市場作為主導機制引入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作為實現發展社會主義的主要目標。他們既堅持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價值理念,又堅持市場作為主導經濟手段的理論設想,借用市場經濟的微觀機制,建構了工人自治型、經濟民主型、經理經營型等社會主義模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在傳統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歷經市場與計劃共存、市場起基礎性作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等的路徑變遷,建構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實踐模式,標志著社會主義探索“市場決定性作用”問題的邏輯升華。
三、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的模式演進
社會主義市場本位理論建構的探索起始于西方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大辯論,產生了政府模擬市場、政府與市場分權、市場主導型、市場決定型等模式形態。
(一)政府模擬市場的競爭社會主義模式
該模式是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終結西方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大辯論而設計的模式,是市場本位社會主義建構問題探索的初始形態。其核心理念針對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社會主義無市場、無經濟核算、無信息等爭論焦點,“比照競爭市場上的均衡決定條件,通過“政府模擬市場”的設想,利用“試驗錯誤的方法”來解決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實現資源合理配置。
具體說來,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基礎上,由社會主義的中央計劃局模擬市場功能,通過價格制定來調整供需關系和收入分配等;企業必須按照政府制定的價格體系,以消費者的偏好確定生產問題,而不能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消費者個人根據自己的偏好自由選擇職業等,實現政府、企業、個人利益關系協調的實踐機制。蘭格認為,盡管社會主義國家不存在實際的市場,但政府可以根據歷史價格隨機抽取價格設定價格體系,通過不斷試驗錯誤的方法確定合理的價格體系以實現供需平衡,確保資源合理配置;同時政府嚴格按照政府偏好與消費者偏好統一的理念,借助計劃性和行政性手段以保證合理的分配和積累,實現社會均等化,滿足社會主義的實踐訴求,以政府模擬市場為中心的資源配置、生產消費、分配積累、個人需求等的合理化的社會形態形成。
總之,蘭格的政府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模式盡管沒有在實踐中實施,同時也存在諸多不合理性,如企業的市場性、政府的行政性等問題,但卻為社會主義探索“市場決定性作用”理論建構揭開了序幕。
(二)政府聯姻市場的分權社會主義模式
該模式是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為提高傳統社會主義經濟效率而嫁接市場的實踐理論模式探索。其核心理念是在傳統社會主義的制度內植入市場機制。包括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匈牙利的新經濟體制等實踐模式;布魯斯的“含有受控制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模式,奧塔·錫克的“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分配計劃”模式,科爾奈的“有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模式等,理論界稱之為傳統市場社會主義模式。該模式具有兩大基本特征。一是政府與市場聯姻;二是政府與市場分權。
所謂政府與市場聯姻主要是指傳統社會主義普遍利用市場機制作為提升經濟效率的手段,但并未關注社會主義與市場的內生性問題。如南斯拉夫與匈牙利的實踐模式中,都主張運用市場經濟,在價格機制、收入分配、企業生產、對外貿易等相關領域依靠市場調節,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同時把市場經濟局限在產品市場,而在“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等方面并沒有突破,這種“沒有資本市場的折中方案”,并不會帶來“人們期望發生的從行政協調到市場調節的變化”,更不能給“社會主義經濟效率低下問題提供”合理的答案。[5]
所謂政府與市場分權,主要是指政府行政權利與市場自由權利的“二元并存”關系,并沒關注政府與市場的交融共生,二者處于共存剝離現象。如奧塔錫克設計的政府宏觀計劃與企業微觀決策在生產、分配、信息、市場透明度等分權形態;科爾奈設計的行政協調與市場協調處理企業軟預算約束和社會保障等。盡管都從不同的視角看透了傳統社會主義面臨的問題,但由于分權嫁接的形態致使企業在“從屬行政和從屬市場”的“雙重從屬”糾葛不清,不能從根本上破除傳統企業存在軟預算約束、企業經理人機制不完善、社會人責任心不足等問題。
總之,盡管政府聯姻市場實踐并未徹底理清政府與市場的職能邊界等問題,但卻實踐了社會主義探索“市場決定性作用”問題的理論,從理論與實踐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三)市場主導型社會主義模式
該模式主要是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探索市場本位社會主義失敗解體后,西方歐美國家探索社會主義與市場兼容的理論設計,既有馬克思主義的堅守者,也有西方左翼理論家的探索。其核心理念是借助市場實現社會主義目標,試圖利用“某些資本主義成功微觀機制,設計出與發達資本義經濟一樣運行得有效率的社會主義機制來”。[6]主要包括工人自治型市場社會主義、經理經營型市場社會主義、經濟民主型市場社會主義等,理論界稱之為當代市場社會主義。
首先,該模式確立了市場的絕對主導地位,設想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的微觀市場機制建構新型的社會主義模式。如羅默的證券市場社會主義就是借助“股票”對初始財產進行平均分配,并借用“股票”參與利潤分紅,甚至死亡上交“股票”來平抑代際不公等設想,建構以“平等”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模式。而巴德漢的銀行中心市場社會主義則試圖借助主銀行、企業、分銀行等互相監督、互相管理等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其次,該模式借用了新自由主義的外殼。盡管當代市場社會主義宣稱堅守社會主義的目標,但其實質是試圖借用西方新自由主義的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運用“凱恩斯主義式的管理”,通過“更加間接的宏觀的”市場因素調控辦法,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及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4]最后,該模式關注了“非市場”因素的作用。為了確保市場充分發揮作用,該模式普遍借助了“非市場”因素的助推作用。如米勒的工人自治型市場社會主義等就非常關注工人的“自由、民主、一人一票”等權利,通過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等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等。而經理經營型市場社會主義則普遍關注職業經理人治理結構,通過對職業經理人的監督管理及物質刺激等手段,確保職業經理人不貪腐、發揮最大能動性等,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斯韋卡特、羅默等人則非常關注法治在市場經濟的保障作用,通過法治的手段監督企業、監督投資、甚至向民眾保證公平公開等手段,以確保市場經濟的導向性作用。
總之,盡管市場主導型社會主義具有一定的烏托邦特性,但卻設計了早期“市場主導性作用”的模式。
(四)市場決定型社會主義模式
主要是指新常態下當代中國政府致力打造的市場本位社會主義的新形態。核心理念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通過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最佳效應,建構政府、市場、社會等一體化的最優運行狀態。
首先,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市場決定型社會主義是中國在原有的計劃經濟架構基礎上,歷經社會主義與市場二元共存、三位一體、四位一體、五位一體的實踐建構,逐步恢復了市場經濟的本質定位。因此,市場決定型社會主義必須優先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其次,政府在市場調控中具有導向作用。市場決定性不代表“自由化”、“私有化”、“無序化”等,市場配置資源必須在政府宏觀調控的導向作用,堅持生產資料公有的社會主義性質,在政府宏觀導向下實現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處理好市場與企業、市場與政府、市場與社會等的核心關系,發揮政府在制定市場法規、市場監管、市場服務、市場協調等方面的導向功能等。再次,市場因素與非市場因素整合運行機制。市場決定性作用并不意味著市場唯一性因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發揮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同時,建構了融核心價值、法制保障、文化軟實力、社會公正等一體化的整合優勢功能,為市場決定型社會主義提供了良好的“合力機制”,回歸了市場經濟的本質和馬克思市場本位的邏輯本源。
總之,盡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探索市場決定性作用方面上尚面臨諸多困惑,但市場決定性方向的提出卻具有重大的創新作用。
四、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探索的借鑒啟示
盡管社會主義市場本位理論探索經歷了曲折,但其積累的實踐經驗以及教訓的總結必然能夠為新常態下市場本位探索問題提供一定的借鑒與啟示。
(一)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本體創新
社會主義是調控市場的重要制度載體;市場是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的重要手段。只有優先堅持社會主義的制度屬性不變,市場才能具有社會主義的制度屬性。這就要求實現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市場機制等的雙重創新,實現馬克思所指的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創新市場機制的社會主義制度屬性,真正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的強勢互補功能。社會主義探索市場本位的經驗教訓足以說明實現兩種載體創新的價值。
國外社會主義在處理社會主義與市場實踐中出現了嚴重的偏差。一是沒有正確認識和評價馬克思所示的社會主義的市場屬性內涵,忽視了馬克思市場本位思想的價值,在不符合實踐的條件下片面采取了廢除市場的極端舉動,背離了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實踐道路;但在實踐矛盾中退卻回溯的背景下又忽視了市場機制的實踐創新,限制了市場機制的優勢屬性發揮,窒息了社會主義與市場融合生成的力量。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實踐相結合,在中國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之上,逐步探索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的“二元并存”、“聯姻兼容”、“市場基礎型”、“市場決定型”等實踐,在堅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基礎上不斷優化市場機制的實踐屬性,建構了市場決定性社會主義新常態,實現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本質回歸,恢復了馬克思社會主義市場本源定位。
總之,盡管我們在探索社會主義與市場創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新常態下仍然面臨更加艱巨的任務。因此,必須堅守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雙重優化,使社會主義與市場逐步回歸本質性屬性。
(二)理清社會主義與市場博弈的邏輯層次
社會主義市場本位問題的實踐必須圍繞社會與市場、政府與市場、企業與市場等三重邏輯維度,才能真正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深層次融合,這是社會主義與市場博弈實踐得出的正確結論。
首先,關于社會與市場關系。社會與市場的關系是社會主義與市場博弈探索的宏觀層次,也是社會主義市場實踐中應該優先關注的問題。這要求社會主義在實踐市場時應該考慮社會主義的制度屬性,實現社會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社會制度等與市場的宏觀融合。早期蘇東社會主義因過分強調社會公平公正問題,避免市場交換機制衍生的收入和財產的不平等性,建構了以絕對公有制為基礎,以集權化的政治形態、文化形態等排斥市場的社會形態。但由于沒有擺正社會公平與市場的關系,導致了社會主義與市場關系層次的錯位與缺失,在效率低下的物質基礎上建構了“平均主義”傾向的社會形態。傳統市場社會主義卻又忽視了社會主義制度屬性與市場的融合,片面關注經濟機制的價值發揮,沒有看到社會組織、社會人、社會制度架構等對市場機制的同化影響作用,阻礙了市場與社會主義雙重優越性的發揮。而當代市場社會主義在重視市場的同時卻又忽視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性,建構在理想狀態的理論設計必然是烏托邦等。
其次,關于政府與市場關系。政府與市場關系是社會主義與市場博弈的中觀層面內容,也是社會主義與市場融合的關鍵。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市場機制優勢的發揮、市場因素與非市場因素的整合、企業及職工積極性發揮等均依賴于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處理。早期蘇東社會主義為了堅守社會主義價值目標選擇了排除市場的政府集權式模式,過分夸大政府的力量,限制了市場機制的發揮而最終促使社會主義效率低下問題。傳統市場社會主義為了克服社會主義與市場邏輯層次缺失錯位的實踐困境,努力探尋市場機制與社會主義結合。在堅持傳統的社會公平的宏觀導向下,著力于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為突破,建構了政府與市場聯姻分權的實踐形態。但由于未能理清政府職能邊界與市場功能邊界問題,使企業陷入了處理行政協調與市場協調雙重制約的窘境,最終未能擺脫窒息社會主義與市場機制功能的困境。如南斯拉夫廢除國家經濟職能的“無政府”狀態的企業自治形態;而匈牙利新經濟體制強勢政府造成的企業軟預算約束、管理人員缺乏活力等同樣導致政府管理失控與企業市場弱化等問題,造成了社會主義解體的根源。當代市場社會主義則選擇了堅持市場機制的背景下弱化政府宏觀調控或者試圖借助資本主義政府建構社會主義的夢想,必然陷入不切實際的幻想。
再次,關于企業與市場關系的微觀模型。企業與市場的關系是社會主義與市場融合的最終落腳點,是正確處理二者關系的微觀層次,也是最終檢驗社會主義與市場融合成效的關鍵點。早期社會主義因政府排斥市場而限制了企業與市場的運營機制,導致了傳統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平均主義、效率低下、工人積極性不高等弊端;傳統市場社會主義則因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難以擺正,并沒從根本上破除國有企業存在的弊端,企業也不能真正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參與競爭,最終難以擺脫破產的歷史宿命。當代市場社會主義者在深刻批判資本主義嚴重社會不公的基礎上,結合社會主義探索市場本位問題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以市場為核心,著力建構市場與企業關系為重點的轉型突破。如工人自治型市場社會主義借助“合作社”的市場載體,建構工人管理、市場機制、民主自由一體化的社會主義;經理經營型市場社會主義則重點通過“經理經營”,利用銀行、利率、股票等市場機制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兼顧社會主義效率與公平。經濟民主市場社會主義則綜合上述兩種模式的優勢,試圖實現市場與社會主義的完美結合等。但他們過分關注企業市場的關系而忽視社會與市場、政府與市場關系等的處理,致使這種模式陷入了烏托邦的嫌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探索市場本位的過程中同樣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恢復了馬克思市場本位社會主義思想傳統。但同樣也遭遇到關于社會主義市場關系邏輯層次混淆問題的困惑。
總之,社會主義在不斷探索社會主義與市場博弈的進程中,理清了二者博弈的邏輯層次,為我們新常態下建構新型社會主義提供諸多啟示。
(三)重視政府與市場的互補結構
政府與市場關系是辯證的統一體,不僅具有互相排斥、互相矛盾的對立關系,同時也存在優勢功能互補結構。社會主義市場本位問題的探索充分證實了政府與市場互補結構的重要性。
首先,強勢政府與弱勢市場的結合。東歐傳統市場社會主義就混淆忽視了政府與市場的互補結構,一直糾結于政府與市場孰重孰輕問題,最終在界定政府與市場邊界方面選取了強勢政府弱勢市場的邏輯范式;片面把市場經濟的機制植入了傳統社會主義的框架,但卻忽視了政府蘊含的政治文化社會等制度功能對市場的反制約作用,未能及時發現政府蘊含因素對市場發展的優勢作用,最終導致了二者的不可兼容性。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在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時,只關心政府與企業的權力邊界,而忽視了政府的其他功能結構屬性,比如社會與市場、人與市場的關系等,結果最終阻礙了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兼容。
其次,強勢市場與弱勢政府的兼容。當代市場社會主義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則同樣沒有避免這個問題,他們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時沒有關注二者的互補結構,他們則采取了強市場與弱政府兼容的模式,把重點轉移到關注企業與市場的關系,致力于微觀企業模型的建構,試圖通過企業模型利潤提升在資本主義國家體制中實現社會主義。但對于政府蘊含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會制度等的邏輯結構功能故意回避或者不甚重視,不僅忽視政府與市場的宏觀導向作用,更缺乏對政府內在結構的思考,沒考慮到資本主義的政府外殼能否自動實現社會主義的問題。這種設計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其烏托邦或改良變異的邏輯本質,也注定了這種社會主義性質的質疑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探索與市場兼容的改革中取得了系列成果,但同時也經歷著政府與市場關系處理的矛盾糾葛。因此,在新常態背景下我們必須認真研究政府與市場的互補結構,擺脫政府與市場的“強勢、弱勢”之怪圈,整合發揮政府的宏觀導向與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
(四)發揮市場因素與非市場因素的合力
市場優勢功能的發揮不僅依靠市場機制的優化,同樣離不開其依附制度屬性的熏陶,只有整合市場因素與非市場因素的合力機制,才能真正建構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市場本位結構。
首先,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理念導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具有雙重屬性,一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屬性;一是優化市場經濟的機制屬性。其制度屬性能夠確保社會主義有機體的科學性;其機制屬性能夠優化市場經濟的劣根性,確保市場有機體的屬性優化。社會主義市場本位問題探索的事實恰恰說明了這一點。不管是蘇東模式的傳統社會主義,抑或是市場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在探索市場本位問題的過程中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導向。為了堅守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目標,蘇東傳統社會主義模式不惜犧牲市場利益而滑向“平均主義”傾向;傳統市場社會主義則嫁接市場以提升效率促公平的實踐模式;當代市場社會主義引入市場主導的平等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試圖恢復市場決定型模式踐行公平效率目標等。盡管在探索社會主義市場本位的實踐中出現了或多或少的誤區,但社會主義公平公正的核心價值目標并未改變,并在此目標導向作用下,設計了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社會公正的實踐模式。
其次,完善社會主義市場與法治規范結構。法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保障,是調節政府與市場職能關系,規范企業運行、社會人市場活動等的基本約束體系。社會主義探索市場本位的實踐經驗教訓暗示了法治的重要價值。
傳統市場社會主義在實現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嫁接時,很大程度上沿襲了傳統社會主義的人治體系,忽視了法治作用對市場本位的重要價值。南斯拉夫市場社會主義解體根源于其民族分裂問題,而其民族分裂問題又淵源于國家職能的消失,在國家的經濟職能喪失的同時,其政治職能、文化職能、社會職能等同時也隨之消失;最終完全喪失運用法治對市場的控制權與主導權,以“勞動組織”自治的社會主義陷入了“無政府”的混亂狀態而步入窮途末路。當代市場社會主義非常關注這種這種實踐的教訓,其在模式設計的時候都充分考慮到法治的力量,一是借助資本主義的法制體系管控經濟與社會;二是依靠法治的手段管理企業與職工。米勒、羅默、斯韋卡特等都明確地提出運用法治監控銀行企業的方法和手段;其他市場社會主義者則明確制定了工人政治生活、民主生活的經濟管理化形式則,規定了工人參與管理、分配、收益、投資等的具體規章制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提出“市場決定性配置資源”之后,雖然提出“依法治國”的重大法治導向,以確保市場經濟的規范性發展,破解市場經濟帶來的腐敗、政府職能模糊、市場規則不健全、經濟人職能錯亂等問題,但完善市場與法治規范結構的任務勢在必行。
最后,實現“經濟人”與“社會人”融合。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不僅要在“道德上優越于資本主義”,同時要在“經濟上優越于資本主義”,二者是“比肩而立、相互補充”的。因此,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人將會替代經濟人是不對的”,未來社會必將是“二者融為一體”。社會主義市場本位問題探索的實踐基本秉承了馬克思的設想。
傳統市場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是建構在“社會人”導向較強的社會體系中,人們的物質意識、競爭意識、權利意識、規則意識、民主意識等大多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缺乏成熟的市場經濟需要的價值觀念、價值導向、市場心態、交往規則等,處于政府行政管控與市場治理的行政領導、職業經理、普通職工等很難做出正確的決策,最終直接反映在企業生產、銷售、分配等各個領域,從深層次制約限制市場經濟的完善與發展,嚴重影響了東歐傳統市場社會主義的發展。如南斯拉夫設想把國家職能交由“勞動組織”等所謂的群眾自我管理機構,讓民眾實現自由民主地管理國家生活,以避免傳統社會主義國家帶來的分配、交換、腐敗、利益糾葛等問題,但結果是原有政府存在的矛盾直接被轉移到了“勞動組織”內部,與傳統國家的矛盾并無差異。當代市場社會主義則借鑒了歷史的經驗與教訓,在理論設計中充分考慮到了經濟人與社會人的融合問題。如工人自治社會主義、經濟民主社會主義直接提出通過工人的一人一票制來決定企業的重大事項,參與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而經理經營型社會主義則聚焦于經理的經濟人社會人屬性,既通過各種法律、監督等手段制約其經濟人屬性,又通過激勵機制等促進其社會人屬性的發揮,以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面臨經濟人與社會人的屬性融合問題,公民的法制意識觀念淡薄、民主意識扭曲、規則意識不強、市場心態脆弱等新問題,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因此,整合經濟人與社會人屬性的融合,破解新常態社會主義市場本位問題建構的薄弱環節。
總之,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問題是馬克思市場批判理論的重大理論預示,也是社會主義百年實踐的艱辛探索之結晶。其蘊含的實踐經驗與失敗教訓必然能夠為我國社會主義的實踐提供理論啟示與實踐借鑒,豐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
[2]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6.
[3]列寧選集(第3版)(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4.
[4]伊藤誠.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M].尚晶晶,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34-35.
[5] W.布魯斯,K.拉斯基.從馬克思到市場: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探索[M].銀溫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39.
[6] Roemer John,Can There Be 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 [M]// Market Socialism:The Current Debate,Pranab Bardan,John Roemer,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責任編輯:張積慧)
The Derivative Logic and Practice Enlighten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Decisive Role Theory"
Xu Junfeng1,2
(1.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2.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701,China)
Abstract:A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it is propos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should be well handled,and market should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allocating resources",which is considered as a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The "socialist market decisive role theory" is originated from Marxist theory of "no market","near market" and "pro-market" and a logical route of "anti-market——near-market——pro-market" formed thereafter. The model of it experienced several rounds of evolution,including government simulating market,government allying with market,market dominating and market deciding,and many lessons and experiences have been accumulated during the process. All these reveal that we should that we must take the bi-dimensional innovation and game level of both socialism and market into account;explore the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integrate force of mar
ket factors and non-market factors;enrich and perfect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socialism;market decisive role theory;logic traceability;practice enlightenment
DOI:10.13253/j.cnki.ddjjgl.2016.03.002
[中圖分類號]F04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6)03-0001-07
作者簡介:徐俊峰(1971-),男,河南杞縣人,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后,上海政法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社會主義經濟運行與發展。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馬克思市場批判理論及其當代價值》(14YJA710033)中期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10-05
網絡出版網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160202.2118.002.html網絡出版時間:2016-2-2 21:1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