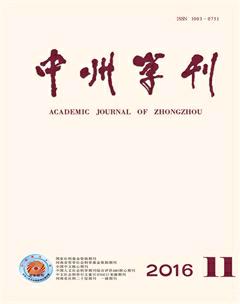生態主義“倫理”—“道德”形態的邏輯進路
牛慶燕
摘要:在人類文明的演化史上,生態主義倫理思想的發展經歷了一個關注生物個體—關愛生命整體—關懷生態實體的生命演進歷程。如果說,“生物中心主義”關注生物個體的生命權益,但由于缺乏普遍的“實體性”依托,最終處于“作惡的待發點上”,遭遇“倫理”—“道德”形態的分裂與對峙,那么,“生態中心主義”則將倫理關懷的中心由個體生命拓展到整個自然生態系統,但是“居留地”的可靠性遭遇“意志自由”的抽象普遍性,同樣無可避免地陷入“倫理”—“道德”形態的悖論與風險之中。人類生態覺悟的辯證運動繼續向前推進,未來社會應當建構接納、包容、整合甚至超越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多元對話的生態主義“倫理”—“道德”共生互動的價值生態和理論形態,這是生態時代人與世界關系的文明生態覺悟,也是一場世界觀的革命和“形態論”的理論自覺。
關鍵詞:生物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倫理”—“道德”形態;文明的生態
中圖分類號:B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6)11-0091-06
在人類文明的演化史上,生態主義倫理思想的發展經歷了一個關注生物個體—關愛生命整體—關懷生態實體的生命演進歷程,也是人類道德共同體的邊界不斷拓展、道德關懷的范圍不斷擴寬、道德知識和視野不斷豐富和開闊的過程。生態主義倫理思想的理論流派從彼此詰責對立到對話交流、溝通融合,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歷史進程,但是,如果沉浸在西方生態主義為我們設計的理性王國中并不斷進行“學派”和“流派”的碎片化式的解讀,那么,我們不僅無法走出不同生態學派和流派的理論沖突,而且容易遮蔽生態主義理論思想的“精神”內涵,因此,“入流”之后如何“出流”,并在“出入流派”之間進行生態主義的“形態論”的研究方法的革命和“倫理精神”的呈現成為可能的研究趨向。
從生態主義“倫理”—“道德”的分裂和對峙形態向生態主義“倫理”—“道德”辯證同一的價值生態方向的演進,是人類道德哲學發展的邏輯進路,也是人類文明的必然走向。如果說“生物中心主義”關注生物個體的生命權益,但由于缺乏普遍的“實體性”依托,最終處于“作惡的待發點上”,遭遇“倫理”—“道德”形態的分裂與對峙,那么,“生態中心主義”則將倫理關懷的中心由個體生命拓展到整個自然生態系統,但是“居留地”的可靠性遭遇“意志自由”的抽象普遍性,同樣無可避免地陷入“倫理”—“道德”形態的悖論與風險之中。然而,人類生態覺悟的辯證運動繼續向前推進,未來社會應當建構生態主義“倫—理—道—德”辯證互動的價值生態,這是生態時代人與世界關系的價值生態覺悟和文明生態覺悟,也是生態主義理論形態發展的精神自覺。
一、生物中心主義的“道德風險”
文藝復興以來,人類自由意志的覺醒和生命尊嚴的獲得相對于中世紀神權對人性的嚴酷壓制是歷
史的進步,但是,脫離了中世紀神權和上帝終極倫理實體的“羈絆”,當生命個體通過對“道”的主觀把握和形上理解,最終內化為主觀性和個體性的“德性”素養時,卻由于缺乏客觀性和普遍的“實體性”依托,最終處于“作惡的待發點上”,其中,“生物中心主義”在生態主義倫理思想發展史上遭遇了“倫理”—“道德”形態的分裂與對峙以及不可避免的“道德風險”。從彼得·辛格的“動物解放的倫理學”、湯姆·雷根的“動物權利論倫理學”到阿爾貝特·施韋澤的“敬畏生命的倫理學”與保爾·泰勒的“生物平等主義倫理學”,其理論軌跡逐漸鋪展開來,共同把人與人之外的所有生命個體納入人類的道德關懷范圍內,從而現實地將生態主義思想由原始蒙昧時期的“倫理形態”推進到“倫理”—“道德”對峙形態,這是西方倫理道德精神呈現的主要歷史哲學形態。
第一,動物解放論基于“功利主義”和“平等原則”,倡導拓展道德關懷范圍并增加動物福利。動物解放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澳大利亞著名哲學家彼得·辛格在《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一文中,以婦女和黑人要求平等權益的解放運動為切入點,認為解放運動的宗旨就是要拓展傳統倫理學道德身份的范圍,動物的解放是人類解放事業的延續,進而論證了所有動物擁有平等權益的正當性:“我們應當把大多數人都承認的那種適用于我們這個物種所有成員的平等原則擴展到其它物種身上去”;“人類的平等原則并不是對人們之間的所謂事實平等的一種描述,而是我們應如何對待他人的一種規范”。①受達爾文進化論思想的啟發,辛格認為各種動物之間感知能力、智力水平的差異并不能成為他們能否享有平等原則的依據,因為具有感知能力的動物和人一樣都能夠感受痛苦和快樂,因此應當平等地考慮人的利益和動物的利益,這是動物生命平等的倫理原則。由此,辛格認為人類與動物之間沒有嚴格的界限區分,他反對物種歧視,尤其反對用動物個體做實驗和殺戮動物,甚至認為人類食用動物也是不道德的行為,并基于功利主義的原則倡導增加動物的福利,杜絕一切對動物的傷害行為。辛格的動物解放論從人類自身特有的道德關懷出發,抨擊了“人類中心主義”和自我利益的狹隘視界,打破了傳統倫理學公認的關于道德等級劃分的界限,關注自然界中的所有動物個體,具有明確的“個體意識”和“主體意識”,第一次使道德關懷的范圍得到了拓展,使人們的倫理思考建立在理性的“道德反思”之上。
第二,動物權利論基于“道德義務論”提出動物的“天賦價值”“固有價值”,倡導尊重動物的“權利”并確立了動物的“生命主體”地位。動物權利論的代表美國哲學家湯姆·雷根從康德的道德義務論出發,認為某些動物和人一樣都擁有“天賦價值”或“固有價值”,它們自身就是終極目的,人類以外的所有動物都是“生命的載體”,作為平等的生命主體,動物和人一樣都有欲求、有記憶、有未來感、有思想,并同樣能夠感受快樂和痛苦,擁有與人類同樣的權利,因此,共同的生物學基礎決定了人類應當尊重動物的權利,并把動物權利運動看作是人權運動的一部分,在實踐上主張禁止動物實驗、取消動物的商業性飼養和純娛樂、消遣性的狩獵活動。圍繞當時社會蓬勃興起的人權運動和爭取自由、獨立與民主的社會運動,雷根倡導個體生命的道德權益與自由意志,并認為只有生命個體才享有權益,道德地位和權利只能賦予生命個體。然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平衡法則決定了在強調動物“內在價值”時也不能忽略“工具價值”。同時,如果說動物擁有“天賦權利”,那么,動物自身卻不能主張權力,當人類意志賦予動物權力概念時,便帶有強烈的“人類中心論”的思想意蘊;如果說權利和義務是對等的,那么,對于動物卻很難達到。因此,雷根的動物權利論以“同情心”的形式賦予動物以“生命主體”的道德關懷資格,但是卻帶有工具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思想傾向,雷根以“原子式”的思維方式解讀“動物權利”但并未上升到保護生物多樣性、基因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的“實體論”的高度,于是帶來簡單的集合并列,并潛隱著將人類個體生命權利凌駕于動物生命權利之上的“道德風險”。
第三,“敬畏生命”倫理觀將“愛”“同情”和“善”的倫理原則賦予所有生命個體,倡導尊重生命、愛護生命。法國人道主義者阿爾貝特·施韋澤基于對自然的情感體驗和倫理態度,認為倫理學是無界限的,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個體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有生命都是唯一的和神圣的,人以及自然界中所有的動物生命、植物生命都具有內在價值,人類對所有生命個體肩負著同等的道德責任和倫理使命。“善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價值。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②“在本質上,敬畏生命所命令的是與愛的倫理原則一致的。只是敬畏生命本身就包含著愛的命令和根據,并要求同情所有生物。”③由此,敬畏生命的倫理觀對傳統倫理觀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戰。施韋澤意識到局限于人與人之間的倫理學是褊狹的,應當把所有生命都納入人類道德關懷的范圍,進而打破了傳統倫理學固有的道德等級高下的觀念,并拓寬了自然界“生命”的概念。施韋澤認為人類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與所有生命存在緊密關聯,人類作為擁有道德理性思維能力的生命物種應當善待自然并對所有生命采取“敬畏”態度,依靠道德自覺力將其他生物的生命意志融入“我們”的生命意志,形成“共同”的生命體驗,進而將“愛”“同情”和“善”的倫理原則賦予所有生命存在。然而,當遭遇“道德律”與“自然律”的分歧與沖突時,“道德律”總是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自然律”,即人類可能會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而以犧牲其他生物的生命為代價,在道德的困境和沖突中如何固守“敬畏生命”的倫理原則成為必須思考的問題。
第四,“生物平等主義”倫理觀主張所有生命都具有固有價值,它源于生命存在本身的“善”,這種傳統的生命目的中心論最終確立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道德關系。美國哲學家保爾·泰勒的“生物平等主義”和“尊重自然”的倫理思想倡導“生命平等”并極力否定“人類優等論”,他認為人類作為地球生命共同體中的成員,與其他生物都是自然進化過程的結果,每一種生物個體都是生命目的中心,人類與自然界中的所有生命物種是相互依賴彼此聯系的統一體,人類并非天生比其他生物優越,因此應當尊重自然并心存“謙卑”和“敬畏”。同時,泰勒提出生物的“固有價值”概念,他認為生命至“善”,所有生物的生命本性決定了其擁有內在的“善”。“善是客觀的,它不依賴于任何人的信仰和觀點。這是一個可由生物學證據證明的論斷,是我們可以知道的東西。”④這種善源于生物的生命本性,成為每一個生命個體所具有的“固有價值”,如果對自然持有尊重態度,那么便承認所有生物自身的“固有價值”,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擁有絕對平等的天賦權利和道德價值。“應該賦予具有內在價值的物體以道德關注,所有的道德主體有責任尊重具有內在價值的物體的善。”⑤因此,人類有責任考慮其他生命形式的“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在“生物平等主義”的倫理關懷下,人類對于自身做出的傷害行為應當進行倫理補償和生態恢復,這是人類應當擔負的道德責任。
由此,“生物中心主義”各流派的理論思想雖然各具特色,但是不約而同地把立論的依據置于生命個體,只是關注生命個體的道德權益,而沒有考慮生命的過程性、生命個體和其所處的生態共同體的關系以及生物共同體的實體性,本質上是“生物個體主義”的哲學表達和理性反思基礎上的道德關切。伴隨著人類經濟理性和科技理性的迅猛推進,人類進入工業文明和技術文明時代,并在征服自然的“戰役”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勝利”。但是,當“勝利”的喜悅還未褪去且“伊甸園”的夢想尚未實現之時,卻遭到自然界無情的“懲罰”和“報復”。西方道德哲學傳統中萌生的“理智的德性”的基因催生了追求意志自由和道德自由的哲學傳統,但是,道德的“良心”以回避現實的方式確保內心的“圣潔”,由于缺乏生命“共同體”生活的原生經驗和實體性追問,便陷入自欺欺人式的抽象的“自我”中,這種“優美的靈魂”與“滿載著憂愁”的靈魂使“生物中心主義”各流派不能建構作為“整個的個體”的“倫”的精神基地,最終淪為缺乏“精神”的集合并列和缺失生態行動的道德說教。當生命的“居留地”和倫理的“實體”家園缺位時,便潛隱著難以預見的“道德風險”,進而遭遇現實世界的生態難題。因此,在西方生態主義倫理思想史上,這種關注生命個體的倫理情懷是對西方傳統倫理學相關理論和概念的移植和延伸,也是生物中心主義的“倫理”—“道德”對峙形態所遭遇的現實難題。
二、生態中心主義的“悲愴情愫”
20世紀30年代,生態中心主義思想開始在西方倫理學界呈現并引起廣泛關注,它以“實體性”的思維理念取代了“原子式”的思維方式,透過生命“共同體”的理論思想使“倫理”回歸,避免了人類“中心”論視野下主體性的過度張揚。黑格爾曾經以“悲愴情愫”表達個體向實體皈依的倫理情態,“在個體性那里實體是作為個體性的悲愴情愫出現的”,“實體這一悲愴情愫同時就是行為者的性格;倫理的個體性跟他的性格這個普遍性直接地自在地即是一個東西,它只存在于性格這個普遍性中”。⑥生態中心主義的“悲愴情愫”基于“共同體”的價值理念強調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和系統價值,把自然界的無機體、有機體及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生態過程和生態系統整體預設為道德的主體,超越了以關注生命個體權力和利益為核心的“生物中心主義”各流派思想,推翻了以關注人類利益為根本尺度的“人類中心論”,同時顛覆了生態主義理論世界中長期被人們普遍認同的價值理念,發展為可能的“生態整體主義”理論形態,因此是重要的哲學范式的轉換。“就生態的范圍而言,整個地球系統就是一個整體,必須從整體的角度考量,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問題。”⑦但是,倫理的回歸遭遇了道德的強勢,生態衷心主義陷入“倫理”—“道德”的悖論與風險之中。總體看來,生態中心主義包括以下三個流派:奧爾多·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阿倫·奈斯的“深層生態學”和霍爾姆斯·羅爾斯頓的“自然價值論”倫理學。
第一,“大地倫理學”以實體性的思維方式確立了“共同體”的核心理念,通過拓展道德共同體的邊界使生命個體向自然生態實體“歸依”。美國著名生態學家奧爾多·利奧波德將自然生態系統中所有生命個體預設為生態共同體中的成員,由此將倫理關懷的范圍從“人類”延伸到整個“大地”。“土地倫理只是擴大了這個共同體的界限,他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動物,或者把它們概括起來:土地。”⑧這一觀點使整體論的倫理觀念與生態主義理論思想相結合,并完成了對道德共同體邊界的擴展。大地倫理學認為,“當一件事情有助于保護生命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的時候,它就是正確的;當它走向反面時,就是錯誤的”⑨。由此,整個生物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麗是宇宙中最高的善,人類只是生物共同體和“大地”上的普通一員。“土地倫理是要把人類在共同體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的角色,變成這個共同體中的平等的一員和公民。它暗含著對每個成員的尊重,也包括對這個共同體本身的尊重。”⑩人類要學會“像山一樣思考”,這是生態實體論的思維模式,也是人類對自然的重要的情感體驗和精神感悟。“土地倫理進化是一個意識的,同時也是一個情感發展的過程。”人類不應當僅僅從工具價值和經濟價值的角度丈量“土地”,內在價值與系統價值應當成為生態整體主義視野中的價值尺度。
第二,“深層生態學”通過確立“自我實現論”與“生物圈平等主義”的倫理原則倡導實體論思維視角下的主體性自覺。挪威著名哲學家阿倫·奈斯將深沉的哲學思考與實踐生活的體驗完美地結合起來,并開創了進行生態哲學思考的新范式。奈斯的“自我實現論”極力克服個體自由意志的覺醒所造就的理性的“自我”,他認為真正意義上的自我實現應當是由“小我”提升為“大我”,“大我”是人類生命主體與自然融為一體的“自我”,是生命“個體”向自然倫理“實體”的歸依,也是人類自我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相同一之后的“整個的個體”。因此,在西方生態思想史上,奈斯的“自我實現論”是深層生態學的重要的理論表達,是人類自我認同對象范圍的不斷拓展過程,同時也是人類生命潛能的呈現。“自我實現論”是“生物圈平等主義”的理論前提,生態系統的復雜性、多樣性與共生和諧能夠最大限度地促進“自我實現”,這是所有生命形式的最大程度的展現和最大程度的“共生”。自然界中所有生命物種對于整個生物圈的平衡、穩定與持續性存在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通過“自我實現”,人類應當發現自然界中的“美”與“力量”,進而實現對自然生態世界的倫理“認同”,推進人與自然的生態和諧,這是人類內在的“善”和“良知”,也是實體論思維模式下的主體性自覺。
第三,“自然價值論”以生命共同體的倫理思維論證了自然的“內在價值”和“系統價值”,為人類善待自然生態系統提供了道德依據。美國環境哲學家霍爾姆斯·羅爾斯頓認為“價值”的產生不依人的意識為轉移,包孕萬有、化生萬物的自然生命系統因其博大的創造力而成為價值誕生的源泉。“在我們發現價值之前,價值就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很久了,它們的存在先于我們對它們的認識”;“大自然既是推動價值產生的力量,也是價值產生的源泉”。億萬年的生命進化歷程使自然生命物種更加多樣化、精致化和復雜化,從而維系著地球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因此,在整個地球生態共同體中,自然生態系統擁有本身固有的純粹目的和與生俱來的內在目的,所以具有最高的“系統價值”和最大的“內在價值”,不僅人類生命主體,而且所有動植物應當擁有“內在價值”。羅爾斯頓以“實體性”的系統論思維方式取代了“原子式”的集合并列分析方法,將價值主體無條件地擴展到自然世界的一切生命,乃至自然生命系統本身。他認為“內在價值”的主體是包括人、動物、植物、有機物、生物圈等一切具有自控調節功能的個體、整體及其生態系統,否認人類是唯一的“內在價值”主體和絕對的生命主體。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來說,“自然價值論”思想的提出不僅是生命共同體的“精神”表達,而且也是一種倫理覺悟。
戴斯·賈丁斯認為:“一個完整的倫理學必須給非生命的自然物體(比如河流和山川)和生態系統予以道德關注”,“生態倫理學應當體現‘整體性,比如物種和生態系統以及存在于自然客體間的關系等生態‘總體應當受到倫理上的關注”。由此,生態中心主義的思維路向以整體共生性原則和系統優化原則為邏輯起點,體現了人與自然的系統整體性和協同進化的動態過程,它將倫理關懷的范圍由人與生物擴展到人與自然的關系,以人類發自內心的自覺行為和“實體性”覺悟來促進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是人類理性精神覺解的轉折點。但是,仔細思考不難發現,以人與自然關系為取向的生態覺悟,同樣遭遇“實體性”思維理想與“個體性”自由的現實之間的悖論,由“自然生態”概念引發的生命“共同體”思想存在現實的理論困惑和道德風險。如果說古典倫理學追求的至善目標是“幸福”,那么,當代實踐論哲學追求的至善理念是“自由”,“理性主義”催生的西方近代道德哲學過度癡迷“意志自由”和“規則契約”意識,人類在不斷地追問自由的理性個體之間以及理性的生命個體與現實的生態主義世界“如何在一起”的問題,然而卻遭遇“個體”與“共同體”、正義論與德性論、倫理認同與道德自由、道德與幸福之間的難以調和的矛盾和沖突。因為,自恃“聰慧”的人類,或者會隱匿在自然生命共同體的庇護下,完全不見人類的生命主體性;或者會脫離自然生命共同體,甚至使“個體”與“實體”相分離,成為沒有任何規定性的“人”,這是黑格爾所言的“悲愴情愫”所遭遇的“倫理”—“道德”悖論。由此,人類如何在彰顯道德“自由”的同時又獲得自然生命共同體所帶來的“安全感”,成為當代人類必須認真思考的現實難題。如果說道德的生命個體與不倫理的自然生命實體是生命個體的實踐理性,那么,倫理的自然生命實體與不道德的生命個體就是生命“共同體”的精神體認。因此,生態中心主義似乎無法走出“倫理”—“道德”的悖論怪圈,陷入了“倫理”—“道德”形態的對峙與混合狀態。生態中心主義本質上仍是一種狹隘并且具有致命缺陷的生態“理性”,最終沒有逃脫人類“中心”的樊籬,生態理念在“他者”的凱歌行進中最終深陷“為我”的泥沼,因而只能是不夠徹底的生態智慧以及倫理與道德之間的“臨界”狀態,也不可能使生態融入文明,并成就“生態文明”。
三、多元對話的生態主義“倫理”—“道德”的
價值生態如果說生物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難以擺脫“倫理”—“道德”的分裂與對峙的命運,那么,未來生態主義倫理思想的理論旨歸應當是建構接納、包容、整合甚至超越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包括生物中心論、生命中心論與生態中心論)的多元對話的生態主義“倫理”—“道德”共生互動的理論形態和價值生態,這是生態主義倫理思想諸理論流派多元整合的生態發展趨向,也是一場世界觀的革命和“形態論”的理論自覺。
第一,生態主義“倫理”—“道德”的價值生態是由“人—自然—社會”交織起來的自然生態、精神生態與文明生態的平衡態。在人類半個多世紀的生態覺悟進程中,人們逐漸明確,自然生態環境惡化的深層根源是人類的“精神危機”與人格生態危機,外部的自然生態危機與內部的人格精神危機的迅速累積將會導致人類文明“倫理”—“道德”的價值生態鏈條的斷裂,從而帶來嚴峻的道德危機甚至是不可逆性的“文明危機”,這將是人類社會最大的文明災難。因此,“生態”應當走出“自然”科學,并走進由人、自然、社會交織起來的系統生態整體,不僅是“自然生態”“環境生態”,更是“經濟生態”“政治生態”“文化生態”和“文明生態”,不僅是純粹思辨和抽象的哲學概念,更是價值理念、道德精神、倫理精神、生態智慧和文明智慧,這是“自然生態”向“文明生態”的轉換和躍遷,是自然生態平衡、精神生態平衡與人類文明的價值生態的平衡,同時也是“生態哲學”和“生態理性”的文化覺悟和文明覺悟。
第二,生態主義“倫理”—“道德”的價值生態是“倫理認同”與“道德自由”辯證互動的生態鏈條。如果說西方道德哲學是追求“道德自由”和“理智德性”的理性主義傳統,那么,中國道德文明則是道德自由強勢背景下,倫理與道德共生、倫理優先的“精神”傳統;如果說,西方社會遭遇了個體道德自由和倫理實體認同的矛盾和沖突,以及“倫理德性”與“理智德性”的對峙與分離,從而使社會至善的倫理訴求缺乏個體至善的可靠根基,那么,中國社會則經歷了倫理訴求與道德追求的分離和矛盾,甚至“倫理”—“道德”精神鏈條的斷裂,進而使個體生命至善的德性追求難以帶來社會至善的倫理訴求。然而,在整個中西方道德文明演化史上,在綿長的“倫理”—“道德”形態的分裂、對峙之后,人類精神文明的演進趨向卻是在道德自由的強勢話語背后對“倫理精神認同”和“倫理同一性”的價值追求,是“倫理認同”與“道德自由”辯證互動的生態鏈條,是生態主義“倫理”—“道德”的價值生態。
第三,生態主義“倫理”—“道德”的價值生態是“倫—理—道—德”辯證互動的“精神”脈絡。在經濟理性充斥的當今時代,應當對接“倫—理—道—德”的價值生態鏈條,個體道德自由應當體現人類文明的“精神”內涵和“共同體”的倫理前景,人類個體能夠向自然生命“實體”皈依,成為具有“精神”的“整個的個體”和“道德的主體”;倫理的精神認同應當是在“實體性”反思的基礎上寬容并盡可能包容不同生命主體的“道德多樣性”和“類”的多樣性,在承認意志自由和理性反思的歷史進步性的基礎上,使現代人類更多地思考人與自然共生和諧的“生態”底蘊。因此,生態主義“倫理”—“道德”的價值生態是人類倫理“精神”的覺醒,是對全球范圍內日益突出的生態環境問題的憂思,也是對整個人類未來生存和發展空間的憂慮與警醒,從而成為人類倫理思想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當環境難題日益成為影響社會發展進程的關鍵性因素的時候,生態主義理論形態的精神內涵必須獲得生命“共同體”的精神認同以及現代意義上人類主體間的生態認同與自我認同,在不同的社會制度、文化傳統與文明秩序的碰撞和沖突中尋求相互包容與理解,當生態主義思想的精神氣質和理論特質慢慢彰顯,其流派所具有的“形態”氣質也便呈現出來,進而構建生態主義“倫理”—“道德”的“中國形態”。
注釋
①[澳大利亞]彼得·辛格:《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江婭譯,《哲學譯叢》1994年第5期。②[法]阿爾貝特·施韋澤:《對生命的敬畏——阿爾貝特·施韋澤自述》,陳澤環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第129頁。③[法]阿爾貝特·施韋澤:《敬畏生命》,陳澤環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9頁。④Paul W. Taylor. Respect for Nature: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Princeton univercity press, 1986, p.61.⑤Michael E. Zimmerman, J. Baird Callicott, Englewood Cliffs N. J.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Prentice-Hall, Inc, 1993, pp.73-86.⑥[德]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下卷,賀麟、王玖興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27頁。⑦徐嵩齡:《環境倫理學進展:評論與闡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221頁。⑧⑨⑩ [美]奧爾多·利奧波德:《沙鄉年鑒》,侯文蕙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3、213、194、214頁。[美]霍爾姆斯·羅爾斯頓:《環境倫理學—大自然的價值以及人對大自然的義務》,楊通進譯,許廣明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2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