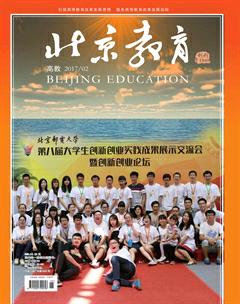微媒體對大學生積極認知與積極行為的影響
劉天舒 唐平
摘 要:文章聚焦于思想政治教育,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對國內的微信內容傳播對個體積極認知與積極行為的影響進行分析,并試圖了解社交媒體發揮作用的方式。研究選取了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156名本科生作為被試者,分三次收取縱向數據。采用回歸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微信內容的傳播所導致的結果,擴展了對于社交媒體對人們的影響的理論研究并具有實踐意義,也為高校運營思想政治教育類微信公眾平臺提出了有效建議。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微信;積極認知;積極行為
微信等社交網站和應用用戶的爆發增長,早就引起了關注。研究者的關注點特別集中在了臉書(facebook)和相關類似的平臺如何提供社會支持尋求的機會[1],但并沒有進一步延伸到其對積極認知與積極行為,如生命意義感和網絡利他行為的產出方面。通過微信公眾平臺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尚缺乏研究支持。本研究提取了思政教育類微信公眾平臺推送內容的若干有代表性的類別,通過問卷調查的方法,以自我報告的形式,考察了被試者對各類推送內容的參與意愿。隨后的追蹤調查中,我們又對學生的生命意義感、社會支持感、網絡利他行為、社交自我效能等變量進行了測量,并通過回歸分析的方法,探索不同的微信內容是如何影響學生的認知和行為。
研究方法
1.研究樣本。本研究以自愿的方式征集了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156名本科生參與研究,分3次收集縱向數據,共得到有效數據98個。其中,男性48名,女性50名,平均年齡為19.65歲(最大24歲,最小17歲,標準差為1.63)。
2.研究工具。我們收集分析了北京大學多個學生工作部門、機關、院系、學生團體和個人建立的微信平臺,以及《新京報》《南方周刊》等主流媒體的官方微信平臺,總結了常見的五類微信平臺內容,并分別抽取兩個例子。其中,我們考察了下列類別的新聞:院校正面新聞,如“吳虹教授談‘堅持與堅韌不拔”“事業、理想與責任—優秀校友司徒惠芬的事跡”;學業生涯信息,如“學術筆記:人類膚色演化的遺傳機制”“畢業生專題—生科人的畢業去向”;個人正面新聞,如“有幸獲得了學術十杰的獎勵,非常開心,感謝我的導師,也謝謝陪伴我的你們!”“今天院足球隊在北大杯比賽上進了決賽,創下歷史最好成績,為我的兄弟們點贊”;生活服務信息,如“北大選課專用APP上線,隨時隨地能刷課”“農園三層推出校內外賣服務,足不出戶吃大餐”;社會負面新聞,如“抽樣調查30家外賣餐廳,僅一半有資質!”“探訪空巢村:老人寂寞守空村”。請被試者根據示例內容評價觀看意愿和點贊或評論意愿兩個方面分別進行0分~4分李克特5點量表評分(0表示“沒有意愿”,4表示“意愿非常強烈”)。研究還測量了以下內容:一是生命意義感。采用劉思斯等修訂的生命意義感量表“生命意義擁有”維度測量生命意義感,該維度包括5個條目。例如:“我明白我生命的意義”“我的生活有清晰的目標”,采用7點計分(1=完全不符,7=完全符合),分數越高代表生命意義感越高。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88[2]。二是社交自我效能感。采用劉遜(2004)編制的人際交往自我效能感量表。本量表有29個自評項目。本量表采用李克特5點計分,得分越高,表明參與者人際交往自我效能感越高。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89[3]。三是網絡利他行為。采用由鄭顯亮等人(2011)編制的網絡利他行為量表。本量表有26個自評項目。本量表采用李克特4點計分,得分越高,表明參與者網絡利他行為出現頻率越高。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95[4]。四是社會支持感。采用由姜乾金根據布盧門撒爾(Blumenthal)等人(1987)介紹的齊梅特(Zimet)的領悟社會支持量表修訂的領悟社會支持量表,包括12個自評項目。本量表采用李克特7點計分,得分越高,表明參與者社會支持感越高。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95[5]。
3.研究步驟。本研究采取縱向追蹤的研究方法,在一學期內分3次收取本研究數據。其中,第一次問卷測量學生對于5種類型微信內容的參與意愿,第二次問卷測量被試的生命意義感和社會支持感,第三次問卷測量學生的網絡利他行為和社交自我效能感。
研究結果
1.描述性統計。表1中呈現了研究中所涉及到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內部一致性系數α和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
2.學生對思政教育微信內容的參與興趣。根據表1中五類微信內容的參與興趣平均值可以看出,學生對于個體正面新聞的參與興趣最高,其次為學業生涯信息和生活信息,再次為院校正面新聞和社會負面新聞。
3.思政教育微信內容對大學生積極認知與積極行為的影響。我們采用回歸驗證思政教育微信內容對大學生積極認知與行為的直接作用,以院校正面新聞為預測變量,以網絡利他行為為結果變量。結果顯示:院校正面新聞能夠顯著正向預測網絡利他行為(β=.39,t=4.07,p<.001,R=.39,R2=.15,adj.R2=.14)。以個體正面新聞為預測變量,以生命意義感為結果變量。結果顯示:個體正面新聞能夠顯著正向預測生命意義感(β=.28,t=2.81,p=.006,R=.28,R2=.078,adj.R2=.068)。以個體正面新聞為預測變量,以社交自我效能感為結果變量。結果顯示:個體正面新聞能夠顯著正向預測社交自我效能感(β=.32,t=3.26,p=.002,R=.32,R2=.10,adj.R2=.093)。以學業生涯信息為預測變量,以生命意義感為結果變量。結果顯示:學業生涯信息能夠顯著正向預測生命意義感(β=.26,t=2.61,p=.011,R=.261,R2=.068,adj.R2=.058)。以生活信息為預測變量,以社會支持感為結果變量。結果顯示:生活信息能夠顯著正向預測社會支持感(β=.34,t=3.45,p=.001,R=.339,R2=.115,adj.R2=.105)。以生活信息為預測變量,以網絡利他行為為結果變量。結果顯示:生活信息能夠顯著正向預測網絡利他行為(β=.41,t=4.26,p<.001,R=.41,R2=.17,adj.R2=.16)。此外,我們發現,以社會負面新聞為預測變量,以網絡利他行為為結果變量,結果顯示:社會負面新聞也能夠顯著正向預測網絡利他行為(β=.44,t=4.67,p<.001,R=.44,R2=.19,adj.R2=.18)。
研究分析
高校微信公眾平臺的運用,使教育內容更加形象化,以圖文聲并茂的動態體現取代單一講述,使教育內容立體化、情景化。微信是大學生日常使用頻率較高的社交媒體,利用微信向學生傳播教育內容是易于被看到的,在學生群體中有較高曝光率的。微信對教育內容的表達是易于大學生接受的,增加了受教過程的娛樂性。本研究發現:學生對于個體正面新聞的參與興趣最高,其次為學業生涯信息和生活信息,再次為院校正面新聞和社會負面新聞。據全永麗的調查結果顯示:77%的大學生關注學校微信號是為了關注學校熱點,51%的大學生為了獲取學習資源,20%的大學生為了參加優惠活動,23%的大學生是由于其他原因[6]。該研究結果與我們的研究結果類似,可以得出結論,大學生主要關注點集中在校園熱點和獲取資訊上,這使以微信公眾平臺傳遞思政教育理念成為可能。
本研究對于不同的思政教育微信內容能夠對學生的積極認知與積極行為產生的影響進行了縱向分析。結果表明:關注和參與校內的正面新聞和社會負面新聞都將導致更多的網絡利他行為。這可能是由于正面新聞和負面新聞都能喚起學生的社會責任感,讓學生更愿意參與到利他和助人的行動當中。關注與個人有關的正面新聞可以提高學生的社交自我效能感和生命意義感,與同學有關的正面新聞的傳播使得學生更關注身邊的同學,在微信中相互交流點贊有利于促進學生社交,發生在同學身上的正面事跡也有利于提高生命意義感。關注學業信息和職業生涯有關信息的學生也表現出更高的生命意義感,這可能是由于此類信息讓學生看到了未來可能的發展路徑,能夠想象到將來能夠在學術和職業領域為他人和社會作出的貢獻,因而提高了自我價值感和意義感。對于生活類資訊的關注可以提高學生的社會支持感和網絡利他行為,這可能是由于此類信息能夠對個人和他人都帶來實際的幫助,閱讀和分享此類信息,本身就是一種互相支持、互相幫助的行為。
根據這些研究結果,我們可以對思政教育微信公眾平臺的內容提出以下建議:一方面,對于公益類組織或社團的公眾平臺,如青年志愿者協會、紅十字會等,可以推送社會和校內的正面、負面新聞類消息和生活類資訊,喚起關注者的利他行為,以鼓勵學生更多參與到公益服務類活動中。另一方面,根據李旭和盧勤的研究結果,大學生生命意義感與心理健康水平正相關[7],提高學生的生命意義感,其心理健康水平也會得到提高。因此,我們建議心理健康教育類微信平臺可以更多地推送有關個人的正面新聞、學業信息和職業生涯相關信息,以提高學生的生命意義感,從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減少因為生命意義感缺失導致的心理問題。院系、社團等團體則可以通過推送更多的個人正面新聞和生活資訊類信息,來提高學生的社交自我效能感和社會支持感,使學生們更樂于融入集體和結交朋友,從而提高組織的凝聚力。
盡管本文有上述發現,但是由于時間和精力有限,仍然存在不少需要改進的地方。主要包括以下幾點:第一,模型設定方面的限制。第二,本文所進行的追蹤研究的時間過短,未來需要將追蹤時間延長,以覆蓋足夠長的時間,來反映本研究所需要的自變量和因變量的改變趨勢。第三,本次問卷調查的每輪時間間隔僅為兩周,兩周的時間對樣本個體產生的心理變化的顯著性有待提高,因此造成了變量間的因果關系不能被充分反映出來。第四,本文限于樣本量過少,未對研究結果進行充分的穩健性分析,對人口學相關因素在問卷中的呈現并不完善。接下來需要擴大樣本量并進行部分量表的重新修訂,對測量結果在不同性別及其他維度進行進一步的檢驗,以期取得更好的效果。
本文系2015年度首都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支持課題
參考文獻:
[1]Bender,J.L., Jimenez-Marroquin, M.C., Jadad, A.R. (2011). Seeking support on Facebook: a content analysis of breast cancer groups[J].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2013(13):135-142.
[2]劉思斯,甘怡群.生命意義感量表中文版在大學生群體中的信效度[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10(6):478-482.
[3]劉遜.青少年人際交往自我效能感及其影響因素研究[D].重慶:西南師范大學,2004.
[4]鄭顯亮,祝春蘭,顧海根.大學生網絡利他行為量表的編制[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11(5):606-608.
[5]汪向東,王希林,馬弘.心理衛生評定量表手冊(增訂版)[M].北京:中國心理衛生雜志社,1999:131-133.
[6]全永麗.以微信為載體加強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15.
[7]李旭,盧勤.大學新生生命意義感與心理健康狀況的相關研究[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0(10).
(作者單位:劉天舒,北京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 唐平,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責任編輯:陳 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