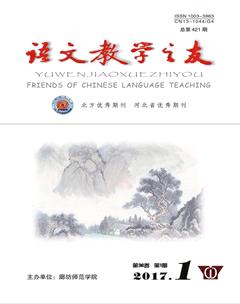以意逆志與語文教學的闡釋學前提
摘要:孟子“以意逆志”的主張雖然對中國傳統闡釋學的構成意義重大,但因為后世學人片面強調“讀者”的重要性,脫離了文本,在闡釋的實踐中留下許多遺憾與困擾。同時,以意逆志雖為語文教學提供了必要的闡釋學前提,卻仍無法滿足語文教學的需要。就語文教學的現狀而言,或許對文本的細讀,進而披文入情、緣景明情才更值得提倡。
關鍵詞:以意逆志;語文教學;闡釋學前提;文本細讀
一
“以意逆志”出自《孟子·萬章上》: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孟子與弟子的話題本是道德倫理,因為其中涉及《詩經》詩句的解讀,后世遂取“以意逆志”一語作為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主要方法論原則之一。然而究竟如何理解“以意逆志”,卻因為批評界歷來對“文”“辭”“意”“志”等這些基本概念缺乏清晰、準確的界定而眾說紛紜。最普遍的一種意見是,“以意逆志”的“意”即讀者之意,“志”即作者之志。這種說法始自漢代趙歧的《孟子注疏》:“意,學者之心意也。”又說:“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也。”[1]該解釋被后世大多學人接受。宋代朱熹和近現代王國維、朱自清等均持此論[2],李澤厚也說:“意是讀詩者主觀方面所具有的東西,所謂以意逆志,就是根據自己對作品的主觀感受,通過想象、體驗、理解的活動,去把握詩人在作品中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3]
可見,作為傳統文論的核心話語和基礎命題,以意逆志意義重大且影響深遠。但在具體的解讀操作中,以己之意逆作者之志的結果卻往往令人憂喜參半,得失參差。最典型的是《毛詩序》對《詩經》中大部分詩歌作品主題的判定。其對《詩經》作出的意識形態誤讀,也早已為文學及批評史所詬病。[4]
甚至有學者通過研究指出,在解讀實踐中,孟子自己也并未能嚴格遵循這一原則。如孟子曾以《詩經·大雅·公劉》和《詩經·大雅·綿》來諷勸齊宣王勿以好貨好色為借口而拒絕施行仁政。孟子分別概括兩首詩的主題為“公劉好貨”“太王好色”,以此來回應齊宣王“寡人好貨”“寡人好色”的搪塞。而后世學者則普遍認為,《詩經·大雅·公劉》敘述的是周的始祖公劉為遷徙作準備的事情,而《詩經·大雅·綿》寫的是太王率氏族由豳遷歧的情況,這兩首詩講述的都是周的歷史,周的由來,與“好貨”“好色”毫無關系。[5]
顯然,讀者之意說縱容了主觀臆斷,不僅使漢儒炮制出“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社會功能主張,將一首首細膩婉轉的抒情詩歌生生改造成了一篇篇了無情趣的道德說教,而且,后世所有泛政治的、泛意識形態的解讀幾乎都有讀者之意的觀念在作怪。甚至對中國文學批評史也產生了誤解,以為中國文學批評是主張并寬容多元解讀的。事實上,中國文學批評史雖然也主張 “詩無達詁”,但似乎更反對“異端邪說”,雖然提倡“見仁見智”,但出于對儒家經典權威性的捍衛維護,所謂“仁”和“智”也往往是儒家堅持的正統思想。
顧彬謹慎地將“意”理解為“心”,即一種思維活動,認為“以意逆志”即“盡量用心揣摩作者的意圖”。但顧彬對這一理解并不確定,在列舉了產生的重大分歧后,顧彬表示,將“意”解釋為人們研讀作品后自己的理解,雖然“可能更符合現代解讀文本的習慣,但是通過上下文可以發現,孟子所講的并非詩的這種分析方法,這種方法對于他來說或許過于主觀了。”[6]
二
其實讀者之意說的最大弊端在于它脫離了文本。閱讀當然是讀者與作者之間的對話,但閱讀是讀者通過文本與作者的對話。沒有文本,那不叫閱讀,那就叫對話。即使圍繞文本,讀者之意說仍受限于具體讀者的年齡、閱歷等因素。也就是說,以讀者之意逆作者之志的實現,必然發生在理想讀者與理想作者關于文本的對話中。
這種種弊端歷代學者并非都沒有意識到,他們或者仍堅持讀者之意說,但對此觀點努力作或多或少的修正,以應對解讀中產生的困惑與不足。如朱自清沿襲陳說,定義“以意逆志”的“意”為讀者之意,但隨后他立即補充道:“逆志必得靠文辭。文辭就是字句。‘以文害辭,以辭害志固然不成,但離開字句而猜全篇的意義也是不成的。”[7]或者重置問題情境,提出新說。如清人吳淇就說:“漢、宋諸儒以一志字屬古人,而意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說之,其賢于蒙(指咸丘蒙)之見也幾何矣。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為輿,載志而游,或有方,或無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詩論詩,猶之以人治人也。”所以他主張“志,古人之志,而意,古人之意”。[8]吳淇意在通過重新定義“意”與“志”來解決闡釋學的疑難。但古人之意尚不是文本之意,較之己意,古人之意更顯得難以琢磨。當代也有人在梳理中國文學批評史時給出略同于吳淇的新的解讀,如敏澤就認為“只有從作品全局著眼,去探索作者的意圖,從而分析作品的內容,才是正確的批評方法”。甚至有人進一步意識到,閱讀應該是作者、讀者、文本三方的對話,文本意義的產生既離不開作者,也離不開讀者,更離不開文本。于是調和派給出第三種意見,以期解決前兩種意見各自暴露出來的問題。如顧易生、蔣凡認為,“意”可以一字兼三任:“作家作品之意與評者自己之意的結合”。然而調和派的意見看似合理,實則與邏輯不符,因為它既缺乏對概念的澄清,更不能回到話語的原初語境,它解決的只是另一個問題。
從趙歧的“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到當代的“必需領會全篇的精神實質,加上自己切身的體會,去探索作者的志趣傾向”,“以意逆志”在傳統闡釋學的長河中逐漸成熟而富于內涵。也不斷地被附加以很難說是內于或外于《孟子》的眾多信息,而這些信息又不斷地被用來應對闡釋的實踐亂象。傳統闡釋學作者——作品——讀者的系統,也因為這個原因變為時代——作者——作品——讀者的多元系統。面對牽強附會的嚴厲指責,后世只好提供其他方法論可能,如既通過讀者的主觀臆測又進行時代鉤考,或既進行文本細讀又進行時代鉤考,以及既通過讀者臆測又通過文本細讀,同時進行時代鉤考。但還存在一些問題:一是作者之志的分歧問題仍然沒能解決。如果的確有這樣一種東西的話,詩人之本意即志究竟是什么呢?二是基于以上緣由,對作者的寫作意圖的把握反而是不可能的了。
三
拋開對以意逆志的歷史建構,孟子的這段話,就中國文學批評史來說,仍然意義重大。一方面,它確定了閱讀的目地在于把握作者的寫作意圖,即“志”;另一方面,它認為這種把握是可以實現的,即“逆”。而這兩點,正是當前語文教學的闡釋學前提。
語文教學的闡釋學前提,除上文概括的作者寫作是有一定意圖的,讀者可以通過一系列努力去把握作者的寫作意圖之外,還包括兩個方面:作者的寫作意圖往往是單純明確的;讀者是可以培養的。
因而對“以意逆志”的當代解讀,即對文本的依賴與細讀,不是文學史和批評史選擇的結果,而是語文教學選擇的結果。對語文教學尤其是閱讀教學而言,作品是有主旨的,且主旨是明確的,這個主旨學生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把握。當然,這種努力有實現的可能,因為多年的語文教學就是這樣訓練學生的。所以,語文教學可以對學生閱讀提供有效的幫助。多年的語文教學也是這樣告訴學生并使學生相信的。怎么去做?當然單純地向作者、向時代要答案肯定不行,單純從自己的經歷經驗出發也不行,還是要回歸文本、細讀文本。教學的結果是學生讀懂作品了,而且會讀作品了——雖然實際上這可能僅僅是一種幻覺:學生們只是像我們希望的那樣做了。
一方面,傳統的闡釋學理論過于陳舊,而且無法應對時代的質詢,另一方面,新課標鼓勵個性化解讀和多元解讀,將更多的批評方法批評視角引入語文教學,如新批評、心理分析、存在主義、現象學、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等,也不是沒有可能,但就目前的閱讀課堂來說,似乎更應強調文本細讀,多做點披文入情、緣景明情的工作。也不妨將“以意逆志”之“意”理解為作品之意。畢竟科學主義的進程還沒有結束,真相目前似乎只有一個。當高考真正能夠接受不同答案之時,我們或可從容說起讀者之意。
注釋:
[1][4]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253.
[2]王國維.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87:169.
[3]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194.
[5]尚永亮,王蕾.論“以意逆志”說之內涵、價值及其對接受主體的遮蔽[J].文藝研究,2004,(6).
[6]顧彬.中國的美學和文學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46.
[7]朱自清.詩言志辨[M].上海:開明書店,1947:77.
[8]吳淇.六朝選詩定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6.
作者簡介:常寶華(1971—),男,甘肅省金塔縣中學一級教師,主研方向為高中語文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