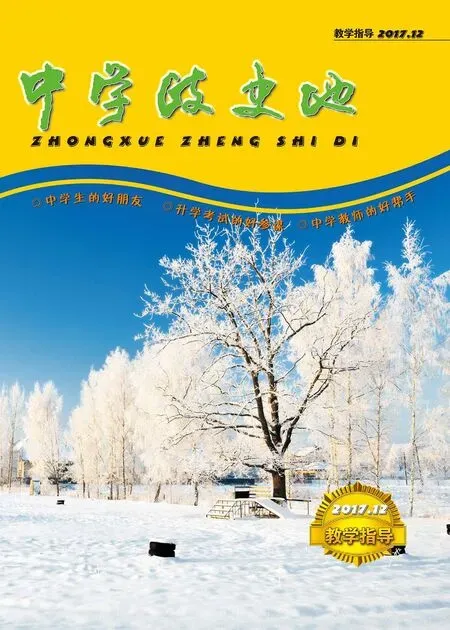試析甲午戰(zhàn)敗之后張謇職業(yè)轉(zhuǎn)型的原因
●
試析甲午戰(zhàn)敗之后張謇職業(yè)轉(zhuǎn)型的原因
●江蘇省如東高級(jí)中學(xué)陸賽楠
張謇,字季直,晚年號(hào)嗇庵。清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853年7月1日出生在江蘇海門常樂鎮(zhèn)一個(gè)富裕農(nóng)民兼小商人家庭。16歲中秀才,歷經(jīng)27個(gè)春秋,近30場科考,光緒二十年(1894年)登上了萬千舉子夢(mèng)寐以求的巔峰。光緒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乾清門外聽宣,張謇卻心緒矛盾,在當(dāng)天的日記中這樣寫道:“棲門海鳥,本無鐘鼓之心;伏櫪轅駒,久倦風(fēng)塵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類無端矣。”無他,國難族危的甲午國殤之年,他在悲慟之余,目睹滿朝文武屈膝跪在傾盆暴雨后的泥濘道路上,而鸞駕回朝的慈禧竟對(duì)這封建效忠式的公開展示不屑一顧,這凄涼的一幕和滿朝文武的奴性,刺激著張謇“世間科第與風(fēng)漢,檻外云山是故人”這副適然亭內(nèi)的對(duì)聯(lián),油然生起“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的念頭。
張謇被授以翰林院修撰,這種純粹咨詢、學(xué)術(shù)性質(zhì)的職位,令張謇深感行事之掣肘。他不甘墮為埋首故紙堆的迂腐書癡,志在政治上做出一番事業(yè)。甲午中日沖突方起之時(shí),他憑借十年游牧生活所積累的政治經(jīng)驗(yàn),迅速成為帝黨首領(lǐng)翁同龢的重要謀士之一。渦旋于帝后黨爭之中的張謇,深知“其實(shí)中國何嘗有必戰(zhàn)之布置耶”,翁同龢并非可代替李鴻章主持對(duì)日戰(zhàn)事的適宜人選。然而李鴻章消極畏戰(zhàn)主和誤國,在民族危亡的關(guān)頭,二人為首的帝后勢力仍在黨同伐異,權(quán)衡官場得失,張謇為此痛心疾首,深感清廷之腐敗,官僚體制之昏暗,封建仕途中帝光榮耀,在現(xiàn)實(shí)的沖擊下,張謇“入仕為上”的價(jià)值體系瀕于崩潰。
光緒二十年甲午九月十六日(1894年10月14日)日記:“得家訊,大人病退而未收口……家中僅婦女主張,心滋不寧,然兵訊未解,勢不當(dāng)便去也。”
光緒二十年甲午九月十七日(1894年10月15日)日記:“晚詣子培,與仲弢、叔衡議,請(qǐng)分道進(jìn)兵朝鮮,夜分心忽大動(dòng),乃與子培言大人病狀,歸亦不寧。”
《年譜》光緒二十年甲午七月一日(1894年8月1日):“上諭聲罪日本。朝議褫海軍提督丁汝昌,李鴻章袒之,朝局大變。”
《年譜》光緒二十年甲午八月十八日(1894年9月17日):“隨班加太后加徽號(hào)……聞我軍潰平壤,退安州。日兵揚(yáng)言,分道入寇。”
《年譜》光緒二十年甲午九月四日(1894年10月2日):“翰林院五十七人合疏請(qǐng)恭親王秉政;又三十五人合疏劾李鴻章;余獨(dú)疏劾李:戰(zhàn)不備,敗和局。”
《年譜》光緒二十年甲午九月十六日(1894年10月14日):“聞父背病疽,愈而未復(fù),心滋不寧,而國事方亟,不可言去。”
《年譜》光緒二十年甲午九月十八日(1894年10月16日):“亥刻,聞父十七日丑刻之兇問。”
《年譜》光緒二十年甲午九月二十七日(1894年10月25日):“由上海抵家。入門伏地慟絕,寢苫喪次,一第之名,何補(bǔ)百年之恨,慰親之望,何如侍親之終,思之泣不可抑。”
張謇父病逝,張謇循例丁憂回鄉(xiāng)盡孝,這次的硬性離職,客觀上加劇張謇去仕的決心,但其最終轉(zhuǎn)變實(shí)現(xiàn)于甲午戰(zhàn)敗之后。1895年“天朝上國”之泱泱中國,敗于“葞爾小國”之彈丸日本的手下。張謇雖丁憂在家卻心系國事,《馬關(guān)條約》之耗音傳來,張謇悲痛不已。《馬關(guān)條件》對(duì)中華民族毀滅性的打擊與摧殘,使張謇更深切地感受到民族危亡的緊迫,“幾馨中國之膏血,國體之得失無論矣”。此后,他在《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qiáng)疏》中指出:“此次日本之和,與西洋各國迥異。臺(tái)灣資敵矣,威海駐兵矣。南洋之寇在肘腋,北洋之寇在門庭。狡謀一生,朝發(fā)夕至。有意之挑釁,無理之決裂,無從預(yù)防,無從臆料……稍一枝梧,立見決裂,是日本之和不可恃,各國之和不可恃矣。”
在甲午國殤中,有著強(qiáng)烈的社會(huì)責(zé)任感與歷史使命感的張謇,自我譴責(zé)“徒為口舌之爭,不能死敵,不能鋤奸,負(fù)父之命而竊君祿,罪尤成無可追也。”終于沖破“學(xué)而優(yōu)則仕”的禁錮,完成職業(yè)價(jià)值觀的飛躍,實(shí)現(xiàn)棄仕從商的蛻變。張謇及同期的知識(shí)分子的職業(yè)轉(zhuǎn)型,是近代中國社會(huì)性質(zhì)轉(zhuǎn)型發(fā)展的衍生行為。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社會(huì)由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向近代工商經(jīng)濟(jì)逐步轉(zhuǎn)變,中國出現(xiàn)“買辦”、“通事”等近代意義的職業(yè),從事這種職業(yè)獲利既快又厚,遂從事此職業(yè)的人與日俱增,并形成了頗具影響的職業(yè)群體,該群體皆是對(duì)西方科技和商業(yè)有不同程度的認(rèn)可的仕人。至19世紀(jì)六七十年代,洋務(wù)潮流中,仕子們職業(yè)觀發(fā)生變化紛紛棄仕從商,投身近代工業(yè),并形成以商救國的思想,提出極具說服力的“商戰(zhàn)”救國的社會(huì)信條,士大夫棄官從商造成紳與商、官與商之間身份對(duì)流和重疊,使“學(xué)而優(yōu)則仕”的信條受到嚴(yán)重沖擊。時(shí)至甲午戰(zhàn)敗后,棄仕從商的浪潮高漲,1895年—1913年新增企業(yè)585家,其中約52%為仕紳、官紳所辦,形成以張謇為首的東南實(shí)業(yè)集團(tuán)。張謇亦感言:“中國今日,官皆商,商皆官也。”在商得到社會(huì)認(rèn)可,官本位思想漸次淡化的歷史潮流中,張謇逐浪而行,實(shí)現(xiàn)近代意義的轉(zhuǎn)變,成為時(shí)代的弄潮人。
- 中學(xué)政史地的其它文章
- 用多元化歷史教學(xué)活動(dòng)提升學(xué)生歷史核心素養(yǎng)
- 借助頭手部位的比喻判別認(rèn)識(shí)東西經(jīng)度
- 基于核心素養(yǎng)的高中教育傳統(tǒng)文化滲透研究的調(diào)查問卷的分析報(bào)告
- 淺析積極心理學(xué)在高中思想政治課堂中的運(yùn)用
——以《人的認(rèn)識(shí)從何而來》的教學(xué)實(shí)踐為例 - 基于學(xué)科核心素養(yǎng)的地理研究性學(xué)習(xí)課堂教學(xué)策略
- 基于核心素養(yǎng)下的思想品德教學(xué)設(shè)計(jì)
——《學(xué)會(huì)承諾》教學(xué)設(shè)計(j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