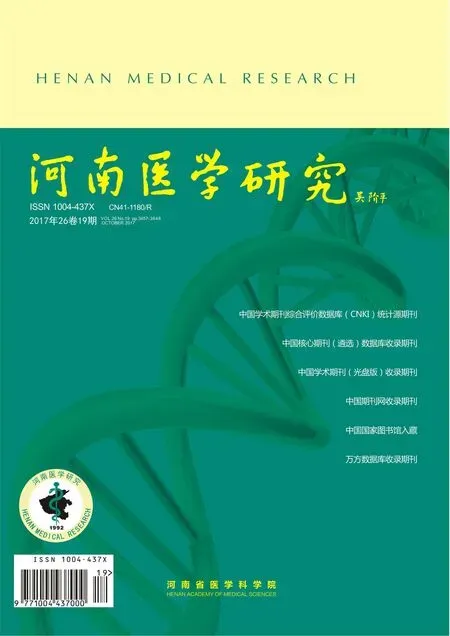風濕免疫性疾病合并急性髓系白血病2例
梁勇會 姜中興 孫慧 甘思林
(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血液科 河南 鄭州 450052)
風濕免疫性疾病合并急性髓系白血病2例
梁勇會 姜中興 孫慧 甘思林
(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血液科 河南 鄭州 450052)
干燥綜合征;系統性紅斑狼瘡;急性髓系白血病
風濕免疫性疾病合并惡性腫瘤多以乳腺癌、肺癌以及胃腸道腫瘤等為主,而血液系統腫瘤相對少見,多以淋巴造血系統為主[1]。相關研究顯示自身免疫性疾病可以增加多種B細胞腫瘤的發生風險[2]。目前風濕免疫性疾病合并惡性腫瘤多為個案報道,其機制仍不明確。本研究收集2例風濕免疫性疾病合并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病例資料,并分析此類病例的臨床特征、發病進展及預后,供臨床醫生參考,避免漏診、誤診。
1 病例資料
1.1病例1患者女性,49歲,因“關節疼痛5 a,心慌、耳鳴、頭暈15 d,發熱2 d”,于2016年6月6日入院。5 a前無明顯誘因出現全身多關節疼痛,當地醫院按類風濕關節炎予以口服甲強龍1片/次,2次/d,之后減至半片/次,2次/d;甲氨蝶呤片3片,1次/d;葉酸2片/次,1次/d;21金維他1片/次,2次/d”,關節疼痛明顯緩解。后因出現發熱,遂來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就診。查體:貧血貌,瞼結膜蒼白,心率快,未聞及病理性雜音,雙肺呼吸音粗,腹軟,肝脾肋緣下未觸及,左下肢散在瘀斑,雙下肢無水腫。既往無高血壓病、心臟病、肝炎等病史,家族無遺傳疾病史。實驗室檢查:白細胞數1.5×109/L,紅細胞1.76×1012/L,血紅蛋白58.0 g/L,血小板總數56×109/L;鐵蛋白517.7 ng/ml;抗核抗體(IgG型)1∶320(+),熒光模型顆粒型,抗Ro52抗體強陽性(+++),抗Ro60抗體強陽性(+++);抗環瓜氨酸肽抗體16.2 RU/ml,抗突變型瓜氨酸波形蛋白抗體109.5 U/ml,RA33抗體8.7 U/ml,類風濕因子(IgM亞型)27.1 U/ml;Schirmer1試驗(+);C反應蛋白94.69 mg/L;血沉47 mm/h;降鈣素原0.167 ng/ml。胸部CT示:雙肺炎癥并左下肺膨脹不全,左側胸腔積液。心臟彩超示:心動過速;腹部彩超示:肝膽胰脾未見明顯異常,雙腎、輸尿管、膀胱未見明顯異常;經腹子宮、雙附件彩超示:宮頸納氏囊腫,盆腔少量積液。骨髓細胞學示:①骨髓增生明顯活躍,粒系占86.8%,紅系占3.6%,粒∶紅=24.2∶1;②粒系比值增高,以異常早幼粒細胞為主,細胞胞體呈圓形,核呈圓形,橢圓形,部分細胞核扭曲,胞漿量豐富,漿內充滿粗大、大小不等的異常顆粒,可見Auer小體;③紅系比值減低,細胞形態大致正常,成熟紅細胞大小不等,色素充盈尚可;④淋巴細胞比值減低;⑤全片未見巨核細胞,可見散在血小板。流式細胞免疫分型:異常早幼粒細胞占85.2%,高表達CD117、CD13、CD64、CD38、CD58、cMPO,部分表達CD123;FISH法:PML/RARa基因融合細胞占78%。診斷結果:①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APL)[3];②干燥綜合征(sjogren syndrome,SS);③肺部感染。給予靜脈輸注比阿培南針、替考拉寧針抗感染等治療,并于2016年6月11日給予亞砷酸(10 mg/次,1次/d,靜脈滴注)聯合維甲酸片(20 mg/次,1次/d,口服)誘導治療。化療第2天,體溫控制差,將抗感染方案調整為“替加環素針、美洛西林舒巴坦針、伏立康唑針”。誘導治療第6天,血常規:白細胞數13.7×109/L,血紅蛋白86.0 g/L,血小板總數41×109/L,加用蒽環類柔紅霉素(60 mg,d1~3,靜脈滴注)雙誘導治療,誘導治療期間間斷高熱,胸部CT示雙肺感染較前加重。2016年6月22日出現氧飽和下降,不能排除誘導分化綜合征,應用靜脈注射地塞米松針治療無效,轉入呼吸ICU,2016年6月24日因“呼吸衰竭、消化道出血”自動出院。
1.2病例2患者女性,62歲,以“脫發、鼻衄6個月,乏力、心慌2個月余,間斷發熱10余天”為主訴,于2016年8月29日入院。6個月前無明顯誘因出現脫發、鼻衄,可自行停止,偶有肩關節疼痛,2個月余前活動后出現乏力、心慌,就診于當地醫院,實驗室檢查:白細胞4.74×109/L,血紅蛋白108 g/L,血小板307×109/L;風濕免疫相關指標:ANA著絲點型1∶320,dsDNA陽性,抗核小體抗體陽性;血沉121 mm/h;C反應蛋白26.05 mg/L;補體C3 1.38 g/L,C4 0.4 g/L;鐵蛋白1 535 ng/ml;胸部CT示:左肺散在磨玻璃樣結節,右肺中葉類結節,縱隔內淋巴結腫大。復查血常規結果示:白細胞9.05×109/L,血紅蛋白63 g/L,血小板463×109/L,2016年6月22日至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查骨髓細胞學示:①骨髓增生活躍,粒∶紅=1.68∶1;②粒系增生活躍,中幼、晚幼粒細胞比之偏高,余階段比值大致正常;③紅系增生明顯活躍,中幼紅細胞、晚幼紅細胞比值偏高,余階段細胞比值大致正常;④淋巴細胞占3.6%,比值偏低,形態正常;⑤全片見巨核細胞大于200個,血小板聚集、散在可見。診斷為系統性紅斑狼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給予口服潑尼松片6片/次,1次/d、羥氯喹片3片/次,3次/d、雙密達莫2片/次,2次/d藥物治療。10余天前無明顯誘因出現發熱,最高達39.0 ℃,自行口服退熱藥物,體溫反復。3 d前體溫最高達40.6 ℃,伴畏寒、寒戰、乏力、口干、口苦,偶有頭暈,就診于當地醫院,2016年8月28日查血常規示:白細胞56.61×109/L,血紅蛋白65 g/L,血小板756×109/L;IL-6 46.430 pg/ml;PCT 0.467 ng/ml;尿常規示:尿蛋白1+;肝功能示:白蛋白37.2 g/L。2016年8月29日收入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既往無高血壓病、心臟病、肝炎等病史,家族無遺傳疾病史。入院查體:貧血貌,瞼結膜蒼白,心率快,未聞及病理性雜音,雙肺呼吸音粗。血常規結果示:白細胞56.60×109/L,紅細胞2.05×1012/L,血紅蛋白58.0 g/L,血小板727×109/L。dsDNA:陽性;抗核小體抗體:陽性。C反應蛋白78.46 mg/L;降鈣素原0.125 ng/ml。胸部CT示:①兩肺胸膜下輕微慢性炎癥、微結節;②左肺底結節,建議動態觀察。外周血分類形態:未分化原始+幼稚占42%。骨髓細胞學示:①骨髓增生極度活躍,粒∶紅=7.08∶1;②原始及幼稚單核細胞占35%,該類細胞胞體較大,呈圓形、橢圓形,核呈圓形、橢圓形,染色質細致疏松,核仁隱顯不一,胞漿量多,染藍色,不透明,少部分可見紫紅色顆粒,POX陰性、弱陽性,NAE陽性,NAE+NaF陽性被抑制;③粒系增生活躍,原始粒細胞占14.2%,中性中幼、晚幼、桿狀核粒細胞比值減低,中性分葉核粒細胞比值增高,余階段細胞比值大致正常,部分中性粒細胞顆粒減少,嗜酸性粒細胞未見增多,POX陽性。流式細胞免疫分型:發現一群CD117+/CD38+/HLA-DR+共陽性的細胞,占有核的53.25%,另表達CD13、CD33、CD71、CD64,部分表達CD9,異常交叉表達CD7,不表達CD34、CD15、CD14、CD11b、CD36、CD2、CD11c等髓系標志及其他淋系標志,該群細胞存在分化,發育停滯及表型異常,為異常髓系早期細胞,結合細胞化學染色(POX:部分陽性,部分陰性、弱陽性;NAE:陽性,NAE+NAF陽性被抑制),FCM圖形及表型符合AML。BCR/ABL、FLT3/ITD、FLT3/TKD、NPMl、AML1/ETO、CKIT突變均陰性,MLL基因篩查陰性。診斷結果:①AML-M4;②SLE;③肺部感染。給予“替考拉寧針、比阿培南針”抗感染治療,經驗性應用“伏立康唑針”抗真菌治療,并于2016年9月11日給予靜脈滴注AA(阿柔比星針40 mg,d1~4,阿糖胞苷針200 mg,d1~7)方案化療,化療后出現間斷高熱,將抗感染方案調整為“替加環素針、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針、兩性霉素B針”,粒細胞缺乏期出現嚴重肺部感染合并心肺功能衰竭,轉入呼吸ICU,于2016年10月6日搶救無效,自動出院。
2 討論
SS是一種侵犯全身外分泌腺的彌漫性結締組織病,主要侵犯淚腺及涎腺,表現為眼和口干燥,也可累及呼吸系統、消化系統、血液系統、神經、肌肉、關節等。SS累及血液系統可出現發熱、白細胞減少或(和)血小板減少。與正常人群相比,SS患者合并淋巴瘤或淋巴增生性疾病的風險增加,但SS合并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臨床上較為少見,兩者發病機制的相關性尚不明確。SLE是風濕免疫科常見疾病之一。目前SLE的存活率得到了一定提高,但SLE本身導致的死亡率較高,特別是合并腫瘤發生死亡的風險進一步增高。文獻報道風濕免疫性疾病合并非霍奇金淋巴瘤居多[4]。有學者認為,應用免疫抑制藥物可以使腫瘤的發生增加,SLE疾病活動度高時亦可能增加惡性腫瘤的發生[4-5]。病例2發病期間未使用免疫抑制藥物,目前為止,檢測到SLE患者使用免疫抑制劑前合并白血病的相關報道較少,病例2較少見,易誤診,應引起重視。以上2個病例均因肺部感染、呼吸衰竭自動出院,推測其可能與以下有關:①自身免疫性疾病本身存在免疫功能紊亂;②長期應用激素、應用化療藥物后均可引起免疫功能低下。
風濕免疫性疾病屬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一種,其與多種B細胞腫瘤的發生相關。到目前為止,國內外研究沒有證據證明這些疾病之間有關聯的機制。有報道表明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治療(如皮質類固醇、抗炎藥和免疫抑制劑)可能增加AML發生的風險[4,6]。也有報道表明,自身免疫性疾病合并白血病與自身免疫功能紊亂,免疫監視功能低下,腫瘤細胞逃脫自身免疫監視概率增加有關[7]。此外,在自身免疫性疾病和AML之間可能存在共同的遺傳和/或環境易感性,在這種(患者自身免疫性疾病)人群中若能確定相關且可靠的預測因子,將極大地識別處于高危的患者,但自身免疫性疾病合并AML的報道仍較少,兩者之間的潛在機制缺乏證據。
總之,風濕免疫性疾病出現血象異常時,應積極排除血液系統疾病,避免漏診、誤診,一旦發現,應積極加強對癥支持治療。
[1] Maria B,Nishishinya,Claudia A.Identification of lymphoma predictors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Sjogren's syndrome: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Rheumatology International,2015,35(1):17-26.
[2] Fallah M,Liu X,Ji J,et al.Autoimmune diseases associated with non-Hodgkin lymphoma:a nationwide cohort study[J].Ann Oncol,2014,25(10):2025-2030.
[3] 張之南,沈悌.血液病診斷及療效標準[M].第3版.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106-107.
[4] Komrokji R S,Kulasekararaj A,Al Ali N H,et al.Autoimmune diseases and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J].Am J Hematol,2016,91(5):E280-E283.
[5] 方振玉.系統性紅斑狼瘡合并血液系統惡性腫瘤的研究進展[J].白血病·淋巴瘤,2013,22(2):124-125,128.
[6] 張國華,蘇金梅,劉心娟,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合并白血病八例臨床分析[J].中華醫學雜志,2011,91(29):2081-2082.
[7] Kristinsson S Y,Bjorkholm M,Hultcrantz M,et al.Chronic immune stimulation might act as a trigg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or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J].J Clin Oncol,2011,29(21):2897-2903.
R 733
10.3969/j.issn.1004-437X.2017.19.028
2017-02-08)
姜中興,E-mai:jiangzx31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