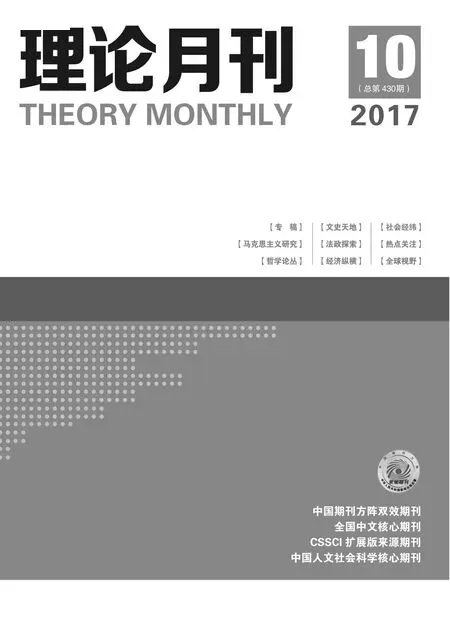民粹主義思潮在大學生中的滲透及其治理策略
□劉小龍
(中國人民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872)
民粹主義思潮在大學生中的滲透及其治理策略
□劉小龍
(中國人民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872)
民粹主義思潮在大學生中的滲透,交織著社會思潮俘獲主體的外在塑造過程和主體選擇及尋覓社會身份的內在認同過程。在載體上借助于網絡空間和文化形態進行傳播,在主體上呈現少數精英和大學生網民的互動,在演進趨向上呈現出議題推動以及和中產階級焦慮心態共振的特點,在話語上出現語言暴力和激進輿論傾向,促使當前大學生對民粹主義思潮兼有理性上的拒斥和情感上的認同的復雜特點。民粹主義思潮帶來了有限的合理要素和長期的潛在威脅,清除民粹主義滋長的社會土壤,完善理性思維和法律素養教育,強化危機應對舉措,是民粹主義治理的基本理路。
民粹主義;社會思潮;社會認同;大學生
民粹主義是當前值得關注的一種社會思潮和思想傾向。據《人民論壇》的跟蹤調查,2012年民粹主義在中國十大社會思潮中排名第八,2013年排第七,2014年躍至第四,2015年仍居第四,2016年成為最受關注、影響最大的社會思潮之一。民粹主義在大學生中的滲透值得高度關注。大學生緣何會受到以“草根”或者“平民”面目出現的民粹主義思潮侵蝕?本文從社會認同的視角出發,力圖揭示民粹主義思潮在大學生中的滲透趨勢及其影響,進而提出有效防范民粹主義的治理對策。
1 環境塑造與社會認同:民粹主義思潮研究的雙重視角
民粹主義是一種十分復雜的政治現象,它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乃至同一國家和地區的不同時期都有不同的表現。由此,關于民粹主義的研究總是充滿了歧義和爭論,目前主要有意識形態、政治風格、組織形式和政治邏輯等四種闡釋框架。從意識形態的視角來看,民粹主義是一種“中心稀薄”的價值觀念,它總是有意識地把社會分裂為兩大對立的集團,即“純潔的人民”和“貪腐的精英”,主張政治應當代表人民的普遍意志[1]。從政治風格的視角來看,民粹主義是政治領袖繞過政治系統、直接與大眾溝通的一種政治控制和權力行使方式[2]。從組織形式的視角來看,民粹主義是一種微觀的政治組織形式,簡單直白的語言風格、極端化思維和對于他者的社會想象,構成了民粹主義的突出特征[3]。從政治邏輯視角來看,民粹主義被認為是一種以話語斗爭為內核、以爭奪話語霸權為旨歸的政治抗爭邏輯,人民話語發揮著勾連統一戰線、指認共同抗爭對象的凝聚和認同功能[4]。
對于當前中國的民粹主義思潮,學界主要從社會思潮的視角來把握民粹主義,并且注意到了民粹主義思潮從歷史語境到現實生活的形態演變。回溯歷史,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發展過程中伴隨著對民粹主義的合理汲取和批判超越,而彼時的民粹主義主要指跨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直接進入到社會主義的“農民社會主義”思潮。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種“變異”的民粹主義思潮在中國興起,主要表現在各類輿情事件的演變和網絡輿論中。學界對于這種民粹主義思潮的本質存在爭議,主要有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5]、激進民意[6]、話語壟斷[7]和網絡集體行動[8]等觀點。 關于當前中國民粹主義思潮的表現形式,學界觀點比較一致,主要關注了網絡民粹主義、文化民粹主義和民族民粹主義三種形式[9]。關于民粹主義思潮的特征,學界概括了反對精英、非理性、極端性和間歇性等觀點[10]。
近年來,民粹主義思潮在大學生中的滲透開始引發研究興趣,大多堅持“環境塑造”的研究理路,網絡媒介作為民粹主義思潮的主要陣地和載體受到重視[11]。轉型期的社會躁動與網絡信息碎片化等外在環境因素,與大學生自身理論儲備不足等主體因素,共同推動了民粹主義思潮向大學生群體滲透[12]。這種環境塑造的研究思路有一定的科學性,但是大學生主體層面的社會認同則沒有受到足夠重視。事實上,任何一種社會思潮的流行,既是由一定的社會環境所決定,同時也承載了主體的某種訴求,體現了某種程度上的主體認同。換言之,研究主體緣何接受、認同一種社會思潮,需要深入探索主體的認同機制。因此,民粹主義向大學生群體的滲透過程,既是社會思潮借助于一定載體的傳播、形塑過程,也是主體自主選擇并進而實現社會認同的內化過程。
就民粹主義思潮的傳播來看,一方面,大學生群體所處的社會地位、社會身份和整個社會的思想境況是大學生群體被民粹主義思潮俘獲的重要原因。正如恩格斯說:“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13]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推進,大學生不再被視為“天之驕子”,社會階層分化在大學生群體當中同樣存在,很多大學生尤其是來自農村的大學生面臨就業、住房等諸多現實壓力。同時,網絡媒介的發展使得“媒介化政治”“媒介化生存”成為現實,民粹主義思潮在網絡空間尤其興盛,構成大學生認可民粹主義的結構性因素。另一方面,主體的社會認同,而不僅僅是客觀社會身份在大學生對民粹主義思潮的認同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后馬克思主義學者拉克勞甚至認為,民粹主義不是由主體的階級、文化和社會地位事先決定的,而是一種建構出來的話語,在本質上是一種把多樣訴求暫時性地統合在人民話語當中的“政治邏輯”[14]。顯然,大學生群體之所以受到民粹主義思潮的感染,與當前中國階層認同“向下偏移”傾向[15]和比較普遍的“弱者心態”直接相關。“屌絲”“青椒”等自嘲式稱謂顯示了大學生群體作為“預備中產階級”或者“邊緣中產階級”的焦慮、困惑和不滿,他們在民粹主義思潮中尋覓著某種程度的主體認同。
可見,客觀和主觀兩個維度的并存,提示著大學生群體受到民粹主義思潮感染的復雜成因,同時也要求開展相關研究時避免“決定論”的武斷,從社會認同的維度來考察民粹主義思潮在高校滋長的原因、機理和對策。一般來說,社會認同是個體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指個體對所屬特定社會群體的成員身份認知,及作為群體成員帶給他的價值和情感意義[16]。卡斯特認為,網絡時代催生了“合法性認同”“抗拒性認同”和“規劃性認同”等三種認同方式,合法性認同由已經居于社會支配者地位的行動者所擁有,抗拒性認同由那些其地位和環境被支配性邏輯所貶低或污蔑的行動者所擁有,規劃性認同則是社會行動者建構一種新的、重新界定其社會地位并因此尋求全面社會轉型的認同[17]。作為一種缺乏堅實內核的社會思潮,民粹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抗拒性”認同,正如簡·杜克特和艾·朗格分析的那樣,民粹主義話語是在與精英主義話語的博弈中生成的一種抗爭性話語[18]。抗拒性認同不僅昭示著大學生群體在政治維度上對精英話語的疏離和反叛,而且在文化維度上體現大學生群體構建身份標識和文化認同的主體努力。
為此,本文從社會認同的視角出發,以“堅持人民的中心地位”“反對精英”“強調人民的同質性”和“宣揚人民的權益正處于被社會精英侵蝕的危機之中”等四個核心要素作為判斷民粹主義思潮的標尺[19],設計了關于民粹主義思潮的個人深度訪談提綱,選取了廣東省三所高校(一所985高校、一所省屬二本高校和一所職業技術學院)各20名大學生共計60名大學生作為訪談對象,以此了解大學生群體緣何認同民粹主義思潮的原因和表現;同時在微信中自媒體類型中選取2016年6月1日到2017年6月1日閱讀量在10萬+以上的文本,對典型的民粹主義文本進行話語分析,力圖把握民粹主義思潮在大學生中的滲透趨勢。
2 理性拒斥與情感認同:民粹主義思潮在大學生中的滲透趨勢
當前大學生對于民粹主義思潮具有理性拒斥和情感認同相交織的特點。一方面,大學生對于民粹主義思潮并沒有系統的認知和自覺的認同,絕大部分訪談對象對于民粹主義的內涵和立場并不了解,也拒絕給自己貼上民粹主義者的標簽。同時,明確表達民粹主義立場10萬+以上的文本中占比在1%以下,說明大學生對于民粹主義思潮比較拒斥。另一方面,大學生又容易在情感維度認同民粹主義的價值立場和思維方式。相當一部分訪談對象對于民粹主義堅持人民至上、絕對平等、反對精英和渲染危機的價值立場,以及“非黑即白”“草根和精英對抗的二元敘事”“老百姓絕對正確”等思維模式認同度較高。這種價值立場和思維方式在涉及到某個具體的社會議題和個體經驗時尤為明顯。可見,大學生對于民粹主義思潮具有理性層面的拒斥和情感層面的認同、整體性上的拒斥和個別性上的認可、長時段的拒斥和階段性的認同等復雜心態。這既與民粹主義思潮固有的滲透性、多變性和迷惑性特征有關,也反映了大學生對于民粹主義的認知、認同需要置于具體的語境中仔細考察。當前大學生群體中民粹主義思潮的滲透呈現出如下特點和趨勢:
第一,民粹主義思潮借助網絡空間和文化載體進行傳播。網絡空間尤其是社交媒體對于大學生的思想觀念影響日趨擴大,從而成為民粹主義思潮向大學生進行傳播和滲透最重要的渠道。從訪談中了解到,相當一部分訪談對象表示在熱點輿情事件中進行過點贊、評論或者轉發,并且主要站在底層、草根和人民的立場,認為網絡自由賦予了他們一種表達“社會公正”或者“發泄情緒”的新方式。對于近年來發生的“藥家鑫事件”“李剛事件”“魏則西事件”“賈敬龍事件”等網絡事件,四分之三的訪談對象表示比較關注且參與了相關評論,他們認為官員、明星和專家比較“可恨”,社會弱者則“很可憐”,高度認可網絡民意的正義性及其展示的積極意義。不少大學生比較認同“民比官好、窮比富好、多比少好、社會弱者比強勢階層好”的網絡定律。一些大學生顯示出了仇官、仇富和仇權的心態,對民粹主義色彩濃厚的激進網絡輿論缺乏理性的辨識和思考能力,因而容易被情緒化的“網絡民意”所裹挾和感染,成為網絡民粹主義不自覺的推手。
文化民粹主義是大學生認同民粹主義的另一重要載體。如果說大學生對于以政治形態表現出來的民粹主義還有一定警覺的話,他們對文化民粹主義則高度認同且積極參與和主動創造。文化民粹主義,可以看成是民粹主義在文化領域的表現,極端地推崇冠以人民之名的大眾文化,同時貶斥精英文化。大學生是文化民粹主義的創造、消費和傳播的重要力量,在他們看來,文化民粹主義具有強烈的娛樂特征,包含著時尚元素,彰顯了反抗精神,顯得“好玩”“酷”和“很嗨”,并且在建構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過程中獲得了一種亞文化認同。以“我爸是李剛”事件中各種戲謔、調侃和惡搞的“造句運動”和“人肉搜索”為典型的文化民粹主義在大學生群體中很有市場,文化民粹主義與青年亞文化、網絡文化和大眾文化具有高度的重疊,成為民粹主義傳播和擴展的重要載體。
第二,在熱點議題的推動下反復發酵,與中產階級的焦慮心態出現共振。民粹主義思潮在大學生中的滲透,與轉型期的社會問題和社會心態嬗變直接相關,因而在熱點議題和社會心態的推動下反復發酵,中產階級的焦慮心態在大學生中的彌漫和擴張尤其值得注意。觸發民粹主義思潮的議題包括社會問題和高校領域的具體議題。社會議題主要有四類:其一是就業、住房等生活壓力。2016年以來新一輪房價暴漲引發了關于階層固化、底層逆襲無望的悲觀情緒,這種議題及其承載的焦慮心態在大學生群體中相當有影響。《關于社會階層的殘酷真相》等渲染階層固化的文章閱讀量、點贊率一直很高,使大學生提前感受到了中產階級的焦慮心態。其二是對“雷洋事件”“假疫苗”“聶樹斌”終審判決等涉及到公、檢、司法部門的社會管理事件的關注。其三是“盛世螻蟻”在微信朋友圈“刷屏”,“延遲退休”政策引發廣泛關注,表明大學生對于社會保障機制改革較為關注。其四是對于環境污染問題的關注度很高,一些大學生對地方政府解決環境問題的決心和舉措尚有疑慮。
高校管理中涉及師生切身利益的問題也容易誘發民粹主義,相關議題主要有教育公平、學費上漲、大學生就業、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延遲退休政策和教育制度改革等問題。大學生對于涉及到自身利益的公平問題尤為敏感,“有事向網上捅、把事情鬧大”成為少數大學生解決問題的慣性思維,近年來在研究生招生、評優評獎、學校硬件設施建設等議題誘發過網絡事件。
從深層次看,社會議題不斷變換的背后是一種影響甚廣的焦慮心態。中產階級的焦慮心態在作為“預備中產階級”或者說“邊緣中產階級”的大學生群體中彌漫開來[20]。超過八成的訪談對象談到了留在大城市生活的夢想與就業壓力大、房價壓力大之間的矛盾,那些來自農村的大學生為無法通過個人奮斗來縮小與家境優越的同學之間的差距感到無奈和無助,還有一些對象在談到房價問題時表露出對于政府調控不力的不滿,甚至還表露了對于整個體制的不滿。可見,焦慮心態有可能激發不滿情緒,并且也有可能成為激進政治自由主義的溫床[21],甚至醞釀、演變為一種反體制的躁狂。
第三,在主體維度上呈現出少數意見領袖和大學生之間的互動。與西歐、美國右翼民粹主義政治人物的強勢崛起不同,當前中國沒有出現公開宣稱主張民粹主義的政治人物,但民粹主義的主張經常被左翼和右翼激進分子所吸納,他們經常以平民的代言人自居,對改革開放多有批判。從訪談中可以發現,大學生對于左派激進人物和右派公知大V并不推崇,公知大V在大學生群體中的影響日趨式微。但是,以“格隆匯”為代表的投資精英和以@作業本為代表的草根寫手在大學生群體中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這些人把關注底層、貼近草根和反對精英的民粹主義作為塑造自身形象的手段,譬如格隆匯炮制的“盛世的螻蟻”一文帶來刷屏效應,@作業本發出的“東莞不哭”的民粹主義動員在大學生群體中影響甚廣。可見,少數意見領袖為了達到商業目的,傾向于使用民粹主義的手段和營銷方式。
同時,民粹主義思潮也迎合了部分大學生的主體訴求,不少大學生自覺不自覺地成為民粹主義思潮的推手。民粹主義思潮迎合了中國社會彌漫甚廣的“弱者心態”,折射了一部分大學生的焦慮心態,反映了大學生群體追求社會平等但理性思考不足、注重政治參與但方式過激等特征,因而承載了部分大學生的主體需求。因此,從情感宣泄、主體價值實現和政治參與訴求等層面,可以發現大學生群體容易感染民粹主義的主體因素。整個中產階級的焦慮、迷茫乃至怨恨情緒提前在大學生群體中進行預演。譬如高校青年教師自嘲為“青椒”“工蜂”,大學生對于“屌絲”的認同,既體現出他們所面臨的住房、就業等現實問題,更顯示出他們的不滿情緒和對于社會公正的期待,尤其是“網絡憤青”更傾向于民粹主義主張。從這個角度來看,相當一部分大學生具有擁抱民粹主義的主體動因,民粹主義話語構建了一種否定精英話語,表達不滿和憤怒情緒的一種“抗拒性認同”[22]。
第四,在表達形式上以話語暴力和激進輿論為主,在個別議題上出現集體行動苗頭。民粹主義的話語表達具有平民化、情緒化和批判性等特征,通過扣帽子、情緒渲染、散布謠言、抹黑精英、謾罵等手段實現一邊倒的話語壟斷[23],以激進話語和對立思維來顯示自身的情感力量和道義力量。因此,民粹主義話語擅長于煽情而不是說理,表現為偏激而不是平和理性,歸結為群體從眾心理而非個人冷靜思考。這種激進話語通過對內的批判和對外的仇視體現出來。從訪談的情況來看,絕大多數訪談對象都承認自己曾經在網上發表過過激的言論,在熱點事件上時常發表偏激乃至謾罵的帖子。他們認為,在網絡空間中不激進和極端難以彰顯力量,心平氣和的討論只會淹沒在信息海洋當中。但他們在主觀上并不承認自己倒向了民粹主義立場,運用了民粹主義話語。也就是說,大學生在社會輿論中表現出來的民粹主義傾向具有大眾心理的從眾特征,是網絡空間中群體極化現象的產物。
如果說對內立場還相對溫和的話,在涉及民族主義的議題時則更容易表現出激進立場,運用激進話語。近年來,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合流趨勢比較明顯,潛伏在民族主義背后的民粹主義值得關注。統計結果顯示,潛伏在民族主義背后的民粹主義文本數量占據首位。繼2016年針對蔡英文的“帝吧出征”、抵制趙薇選用臺獨演員事件之后,2017年民族主義事件頻有發生:歌手張敬軒被踢出《我是歌手》節目,特朗普對華政策引發高度關注,除夕之夜“炮轟聯合國”的網絡示威,尤其是反薩德系統、“手撕”樂天超市事件的持續發酵,顯示了大學生群體對于愛國主義認同度非常高。但是,也有個別大學生持有一種狹隘的愛國主義和極端的大國心態,表達方式也過于激進化和情緒化,一味強調對外強硬,對不同意見者動輒扣帽子,進行責罵甚至謾罵,甚至還采用人肉搜索、黑客行動和輿論施壓等手段,從而走向以愛國為名、民粹為實的民族民粹主義。一些人不僅在網絡上進行“敵我”區分,用扣“漢奸”帽子的方式來黨同伐異,甚至還出現了號召大家參與集體行動的苗頭,需要警惕。
3 合理要素與潛在威脅:民粹主義思潮帶來的復雜效應
民粹主義思潮在大學生中的影響比較復雜。從積極的一面來看,民粹主義思潮具有一些合理要素,譬如激發了大學生對于社會問題和政治參與的熱情,引發了人們對于社會公正的關注,約束了社會精英的言行舉止以及推動了教育制度變革。但是,總體而言,民粹主義帶來的消極影響是主要的,尤其是其潛在威脅值得警惕。
第一,民粹主義盡管打著人民的旗號,卻背離了和損害了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影響了大學生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認同,對現代化建設事業帶來威脅。民粹主義推崇社會底層、否定社會精英太過偏頗,偏離了有序民主的軌道,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無法得到切實保障。同時,在民粹主義建構的整體性、同質化的人民面前,個體權利無足輕重,在人民正義的口號下可以藐視法律制度,侵犯個人隱私,從而可能蛻變為多數人的暴政,任由民粹主義泛濫會對人民民主專政和依法治國帶來沖擊。“人民”話語強調了社會底層與社會精英的對立和對抗,加劇了社會分裂,沖擊了社會秩序,背離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民粹主義在推崇人民的話語背后隱藏著背離人民的內核,任由民粹主義思潮泛濫,必然影響大學生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認同。
第二,民粹主義倡導非制度化、情緒化的政治參與方式,不利于培養具有責任意識和理性思考能力的公民。民粹主義思潮是一種不成熟的政治參與方式,訴諸情感而缺乏理性,參與熱情過度而公民訓練不足,強調人民整體權利而忽視主體責任和個體權利,主張人民審判而輕視司法判決,在人民的名義下以激進輿論、人肉搜索等非制度化渠道來干預現實、表達訴求,具有只講權利不講責任的片面性以及缺乏自我約束而具有走向暴烈的危險性,在很多時候發展成為一群具有破壞潛力的烏合之眾和網絡暴民。這種苗頭在近年來網絡上泛濫成災的“人肉搜索”和輿論狂歡案例當中可以窺見;在“藥家鑫”案、“李剛事件”“余純合事件”“雷洋”事件中,網絡輿論審判對于司法審判公正性和獨立性的壓力已然顯現。民粹主義固然激發了大學生關注社會現實、表達訴求、參與政治的積極性,但他們卻沒有學會以理性的方式表達和溝通,也不善于通過制度化的方式來表達訴求,因此,民粹主義對于高校培養具有責任意識和理性思考能力的現代公民是很不利的,也影響了大學生對于依法治國的信任和法律意識的培養。
第三,民粹主義挑戰既有權力結構、激起群體對立、加劇社會分裂,又不利于大學生養成健全的社會心態,對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會帶來負面影響。民粹主義激化了大眾與精英、官與民、體制外與體制內兩大陣營的對立乃至對抗,二元對立思維撕裂了社會團結,妨礙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理性溝通,不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仇富、仇官、仇權的非理性心理開始蔓延,“磚家”“叫獸”等污名化稱謂體現了反智的傾向,不滿、怨恨和憤怒等社會情緒得以集中宣泄,甚至在網絡空間中開始出現“道德民兵”和“網絡紅衛兵”,這必然影響到當代大學生養成健全的社會心態,削弱了大學生對于知識的尊重和敬畏,也會影響到大學生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
第四,民粹主義在教育改革發展中堅持底層立場和結果平等,追求教育資源分配的平均主義、教育治理的大眾決策和教育改革的民意支配,給當前我國教育改革帶來巨大的壓力,不利于教育改革的順利推進。當前,在公立學校設置、高考指標分配、高校學費上漲、升學選拔機制等幾乎每一項教育改革議題上都可見民粹主義傾向的出現,具體表現有:在改革目標上以平等主義代替教育公平,主張“補償弱者、拉平強者,完善大善、舍棄小善”;教育輿情中的反精英立場;以及教育治理中的民意裹挾,以多數民意作為教育改革依據。應當說,民粹主義的這種關注對于糾正當前“寒門再難出貴子”“農村教育空心化”以及教育過度市場化等偏向有一定的糾偏作用。但是,只注重結果公平而不注重過程公平、加劇精英和底層以及百姓和政府的沖突以及教育改革過程中以“少數服從多數”民意來裁斷、裹挾教育改革進程,顯然是不合理的,必將導致另外一種教育不公平,進而把教育改革帶向歧途。
4 深化改革與危機應對:防控民粹主義思潮的基本理路
民粹主義被比喻為 “時刻存在且不定時發作”的“癬癥”,管控民粹主義被稱為“一場激烈而不能肯定取勝的斗爭”,因此,民粹主義的防控策略在于盡量限制其負面意義,防控其消極影響,而不是徹底清除民粹主義。其主要的治理思路如下:
第一,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努力促進教育公平,消除民粹主義的滋生土壤。歸根到底,民粹主義思潮是對社會現實問題的一種反映和評價,是貧富差距拉大、社會階層分化、民生問題突出等問題所引發的一種社會心理和社會情緒,因而民粹主義思潮的防控從根本來說是要解決現實問題,把民粹主義防控納入到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中,全面深化改革,實現社會公正,解決民眾關切的社會問題。具體到教育領域中,穩步推進教育改革,加大國家對于教育的財政支持力度,在教育資源分配上適當向農村、向基層、向社會底層和非重點學校傾斜,適當提高農村子女上大學的比例,以教育公正來吸納平等主義訴求;在教育決策過程中廣納民意,推進民主協商,鼓勵社會公眾的適度參與,把非制度參與沖動轉化為制度化、常規化的參與渠道;營造有利于高校人才成長的良好環境,創造條件解決高校師生面臨的現實問題,尤其是青年教師面臨的職業發展以及住房壓力、子女上學等現實問題,以及高校大學生面臨的生活困難、就業壓力等問題。
第二,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大學生的理性思考能力和法制意識培育,培養具有社會責任感和全面發展的現代公民。理性精神、法制意識的培育是抵御民粹主義誘惑的思想利器。為此,要堅持素質教育的基本方向,在教育目標上培養德才兼備的合格公民。在教育內容上注重培養大學生的理性思考能力和法制思維。在教育理念上注重尊重學生的主體性,采取互動式教學方式。在教育方式上不斷創新,實現從知識傳播、思想灌輸到培養大學生的理性思考能力和樹立正確價值觀念的轉變。在教育路徑上注重開拓網絡教育平臺,實現理論教育和實踐教育、線下教育和線上學習的有機結合。
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完善網絡教育平臺,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引領、整合民粹主義,尤其注重用真實、具體和鮮活的人民概念來整合整體性的人民話語,用社會公正來整合平等主義訴求,用法治理性來規約道義沖動,引導大學生以理性、發展的眼光看待社會問題,進一步增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實效。
第三,分工協作、突出重點、有針對性、有策略性地做好民粹主義疏導工作。在防控思路上,把民粹主義防控定位為一種柔性、細致和持久的思想工作,多在“引”和“導”上下功夫,盡量少去“堵”和“截”。在工作重點上,要把網絡民粹主義治理作為重點。建立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和各個高校專門的微信公眾號、網絡輿情跟蹤系統和應急處理系統。對網絡輿情進行定期監控和周期性總結,對觸發網絡民粹主義的社會議題做全面的整理歸類,對高校網絡輿情定期進行有針對性的搜集和監測,對那些可能引發動員的輿情苗頭進行關注和及時解決。在網絡民粹主義輿論形成之后迅速開啟輿情危機應對程序,堅持黃金24小時的應對原則,及時準確地發布權威信息,信息公開,及時進行師生溝通、情感疏導和啟動問責等,力避堵、躲、拖延和敷衍等態度。及時總結網絡民粹主義動員應對的經驗和教訓,在技術管理、平臺建設、議題觀測、應對策略等方面進行反思和完善。
在分類處理上,對草根維權型、針對于社會精英言行不當的情緒發泄型、商業利益裹挾型和娛樂狂歡型等四種民粹主義區別對待。對于草根維權類民粹主義,要解決問題,回應訴求;對于社會精英的不當言行引發的民粹主義輿論,譬如雷政富事件、周久耕事件、楊達才事件,則需要及時啟動追責、問責程序,實現相關部門與涉事主體的切割,盡量把負面影響控制在有限的范圍之內;對商業利益裹挾類型則需要適當管控;對于娛樂狂歡類型,要以積極的文化引導來提升網絡文化欣賞品味,同時為其劃定法治邊界,盡量避免其對個人隱私和社會安全帶來沖擊和影響。
在防控對象上,注重對激進左派知識分子的重點布防和統一戰線工作,對網絡意見領袖的圈子化要密切關注和及時干預。目前微博平臺仍然是思想觀念傳播和意見領袖塑造的重要領地,激進左派在價值觀上傾向于認同民粹主義,在話語表述當中也經常使用民粹主義的策略,他們的言論被轉發的數量遠大于右派意見領袖,因而對這類意見領袖是防控的重點對象。同時,也要注意網絡上意見領袖圈層化、抱團化的現象,采取管制和培育相結合的策略,從硬性管制走向軟性溝通。對大學生群體當中思想激進、偏激的學生也要開展個別性的引導和教育。
在防控策略上,需要社會多元主體的協同合作,同時也需要采取多種方式、多種手段以形成合力。建立有效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機制,建立以黨委、宣傳部門、思想政治教師、輔導員為主體,分工協調、運轉有效的大學生思想政治工作系統。積極培育高校意見領袖,培養一批懂網絡、善于開展網絡思想工作的網評員,在網絡空間亮劍和發聲。注重大學生人文精神塑造,凈化網絡生態,提升文化品位。開設專題講座,讓大學生對民粹主義的由來、實質和危害有清醒的理論認識。
[1]C.MUDDE.The Populist Zeitgeist[J].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2004, 39(3):541-563.
[2]KURT WEYLAND.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J].Comparative Politics,2001(1):1-22.
[3]MATTHIJS ROODUIJN.The Nucleus of Populism:In Search of 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J].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2014,49(4):573-599.
[4][14]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 reason[M].New York:Verso, 2005:224,224.
[5][9]陳同順,楊倩.當前中國的民粹主義[J].江蘇社會科學,2016(3):127.
[6]蕭功秦.超越左右激進主義:走出中國轉型的困境[M].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29.
[7]陳龍.網絡民粹主義的話語壟斷策略[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6):157.
[8]陳堯.網絡民粹主義的躁動:從虛擬集聚到社會運動[J].學術月刊,2011(6):25.
[10]李良榮.民粹主義的三個動向[J].人民論壇,2017(1):22-24.
[11]吳默聞.網絡民粹主義及其對大學生的影響研究[J].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17(5):25-27.
[12]王輝.論民粹主義思潮網絡嬗變對大學生的影響及其對策[J].湖南師范大學學報,2016(4):72-74.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4.
[15]李培林.社會沖突與階級意識:當代中國社會矛盾研究[J].社會,2005(1):20.
[16]N ELLEMERS, SELF-CATEGORISATION.Commitmentto the Group and Group Selfesteem as Related but Distinct Aspects of Social Identity[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99:2-3.
[17][22]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M].曹榮湘,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25,6-7.
[18]JANE DUCKETT,ANA INES LANGER.Populism versus Neoliberalism:Diversity and Ideology in the Chinese Media’s narratives of health care reform[J].Modern China,An InternationalJournal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2013,39(6):653-680.
[19]MATTHIJS ROODUIJN. The Nucleus of Populism:In Search of 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J].Governmentand Opposition,2014,49(4):573-599.
[20]李強.中產過渡層與中產邊緣層[J].江蘇社會科學,2017(2):2.
[21]李春玲.尋求變革還是安于現狀:中產階級社會政治態度測量[J].社會,2011(2):149.
[23]陳龍.網絡民粹主義的話語壟斷策略[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6):157.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10.019
G641
A
1004-0544(2017)10-0103-07
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 “十三五”規劃課題 (2016MZXY22);教育部2014年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14YJC710028)。
劉小龍(1982-),男,湖南邵陽人,法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廣東藥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 趙繼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