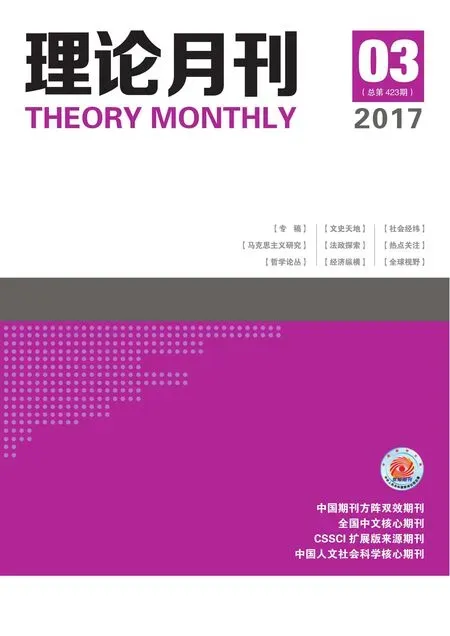“道-德”抑或“德-道”?
——基于語序原則的《老子》文本結構新釋
□涂江波,戴茂堂
(1.長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荊州 434023;2.湖北大學哲學學院,湖北武漢 430062)
“道-德”抑或“德-道”?
——基于語序原則的《老子》文本結構新釋
□涂江波1,戴茂堂2
(1.長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荊州 434023;2.湖北大學哲學學院,湖北武漢 430062)
帛書本與楚簡本《老子》的發現,在文本結構上將《老子》由通行本的“道-德”更正為了“德-道”。根據漢語語序的“信息中心原則”,“道”“德”可以視為《老子》中的兩個信息中心。根據“時間順序原則”與“整體先于部分原則”,《老子》的文本結構應為“道-德”。根據“凸顯原則”,《老子》的文本結構應為“德-道”。“道-德”或“德-道”,不是“道”與“德”的簡單拼合,它們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思想進路。《老子》最大的思想貢獻是形成了“道”與“德”之間的關系域。
語序原則;老子;道;德
《老子》全書分為“道經”和“德經”兩篇。過去流傳的版本(由王弼所注的通行本)以“道經”為上篇,以“德經”為下篇,形成了一個“道-德”的文本結構。而1973年從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發掘出的《老子》帛書本①據任繼愈先生研究,帛書本甲本的抄寫年代可能在漢高帝劉邦時期(公元前206年-前195年),乙本的抄寫年代可能在惠帝或呂后時期(公元前194年-前108年)。見任繼愈.老子新譯(修訂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杜,1985年版,第257頁。,1993年在湖北荊門郭店楚墓中發現的簡本《老子》②據陳鼓應教授推測,楚簡本《老子》的成書時間應不晚于戰國早期。見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485頁。因楚簡本是摘抄本,且多脫字,因此本文不以其為文本依據。,作為較早一些的版本,卻是依先“德”后“道”排序的,即“德經”在先,“道經”在后,恰與通行本次序相反。由此,《老子》在文本結構上便被事實地更正為“德-道”,這樣也就發生了通行本與帛書本《老子》文本結構的異同問題,而這個問題實際上可以表述為:到底《老子》的原本是什么樣的?在文本結構上,應如通行本那樣“道”先“德”后,還是應如帛書本那樣“德”先“道”后?“道-德”抑或“德-道”?歷來學術界關于這一問題爭訟不斷,各種見解紛陳疊出,至今熱度不減。
以下,筆者將結合漢語語法中的幾條語序原則,就這一問題給出一種新的解釋。語序是漢語中重要的語法手段,語序結構能夠賦予語句(段落)以意義。語序不同,會產生不同的意義。漢語語法中有四條基本語序原則[1]:信息中心原則、時間順序原則、整體先于部分原則(空間順序原則)、凸顯原則。其中,時間順序原則與整體先于部分原則分別基于人們感知時間、空間順序中事狀的方式,它們同屬于語序的“自然原則”。而自然原則與凸顯原則之間的區別在于:前者以感知為基礎,后者則帶有說話人的興趣、關涉的焦點等。有明于此,本文將依據語序原則來解析《老子》中“道”與“德”的關系,同時厘清,將《老子》的文本結構厘定為“道-德”或“德-道”,各自有什么樣的理據。
1 作為信息中心的“道”與“德”
漢語語序遵循一條“信息中心原則”。所謂“信息中心”,“是語用上構成的,跟說話人的態度沒有關系”,通常“句子的前提部分在前,斷言部分在后,‘信息中心’是斷言的部分。”[2]借用“信息中心”這一提法,我們要問的是:在《老子》中,有沒有“信息中心”?如果有,有幾個“信心中心”?
有一種觀點認為,在《老子》中根本不存在“信息中心”,理由是:《老子》確實是分成了“道經”與“德經”兩篇,但這樣的篇名,只是把開篇句首的字提出來而已,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含義。通行本《老子》,上篇第一句是“道可道”,便取出一個“道”字,下篇第一句是“上德不德”,便取出一個“德”字。在帛書本中,這種做法的痕跡更加顯著。帛書乙本《老子》的上下兩篇,并沒有篇名,也沒有分章,只是分別在篇尾標記了“德三千四十一”和“道二千四百廿六”,于是,“德”和“道”就被分別用作上下兩篇的篇名了。因此,《老子》一書并沒有“信息中心”,也沒有嚴密的結構,只是一系列具有“啟發性”的思想碎片。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老子》中只存在一個“信息中心”,那就是“道”,亦即只承認《老子》一書的主旨是“道”,而不包括“德”。這種觀點的典型例證是,直到最近,英語世界關于《老子》的討論幾乎完全集中于“道”,而很少關注“德”。香港學者劉殿爵在他影響廣泛的《老子》英譯本序言中,只用了一小段話講“德”,且直截了當地說:“在老子那里,這個概念并不十分重要,常常在習慣意義上使用這個詞。”[3]這些忽略“德”的做法可以找到一些表面上的理據:在各種版本的《老子》中,“道”出現的次數都要多于“德”字,似乎《老子》對“道”與“德”的探討不均衡,明顯偏重于“道”,“德”的地位及其重要性遠不如“道”。
在筆者看來,上述觀點都罔顧了一個不爭的事實:“道”和“德”是《老子》的兩個核心概念,也是《老子》中出現次數最多的兩個概念①由于不同版本《老子》的文字多有不同,“道”與“德”出現的次數也有所不同。據陳鼓應教授校定的版本,“道”字共出現73次,“德”字共出現43次。,這部經典本身就是由“道經”和“德經”兩部分構成。因此,認為《老子》有“道”和“德”兩個“信息中心”是有充分依據的。對于《老子》一書的主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概括說:“老子修道德,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無疑,《老子》的思想是以“道”和“德”兩個范疇為論述中心展開的。《老子》一書也有著嚴密的論述邏輯:“道經”與“德經”的結構高度一致,開卷分別對“道”和“德”的理念進行了規定。“道經”的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德經”的第一句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其德,是以無德……”。顯然,兩經的開卷語從句式到意境都高度一致,都具有提綱挈領的意義和作用。
另外,“道”字在《老子》中出現的次數多于“德”字,就可以由此得出“德”的重要性不如“道”的結論嗎?似乎并不應如此草率:第一,“道”字出現的次數多于“德”字,并不構成“道”比“德”重要,甚至可以忽略“德”的理由,因為,從“德經”的篇幅多于“道經”(如帛書本的數字統計)這一點,是不是也可得出相反的結論?第二,在“道經”中“德”出現的次數較“道”少,而在“德經”中“道”出現的次數也較“德”少,怎么可以認為《老子》對“道”與“德”的探討不均衡呢?《老子》分為“道經”和“德經”兩部分,本身就說明了《老子》對“德”的重視。所以,“道”和“德”同為《老子》的“信息中心”。
信息中心原則解決了《老子》文本結構——無論是“道-德”還是“德-道”的合理性問題。現在的問題是:“道”與“德”,到底何者更重要、更具有優先地位?而由通行本《老子》向帛書本《老子》反正,意味著存在兩種可能并且已經出現的答案:通行本《老子》在結構上取“道”先“德”后,是以“道”為重心;帛書本《老子》在結構上取“德”先“道”后,是以“德”為重心。而“道-德”抑或“德-道”?這個問題并非無關緊要,因為這兩種文本結構體現了兩種不同的思想進路,關系到對《老子》一書邏輯結構的理解:是由“道”而“德”,還是由“德”而“道”?這一問題,需要通過梳理“道”和“德”的關系來解決。如果我們將“道-德”、“德-道”視為一種語句的表達,則它們所表征的《老子》文本結構分別可以通過漢語語序的自然原則與凸顯原則獲得支持的理由。
2 自然之序:先“道”后“德”
如上所述,漢語語序的自然原則包含了“時間順序原則”與“整體先于部分原則”。時間順序原則,意指“兩個句法單位的相對語序決定于它們所表示的觀念里的狀態或事件的時間順序”[4],它概括了漢語表述中在時間上“先講原因,后講結果”的自然順序。整體先于部分原則,意指“把整體放在部分前面的線性排列原則[5]。就包含關系而言,漢語表達是傾向于把整體放在部分前面的。如果遵照自然原則來排列《老子》中“道”與“德”的順序,就應該是“道-德”而不是“德-道”,而通行本《老子》正是采取了這樣的排列方式。
2.1 “道”因“德”果,因先于果
首先,從時間關系來看,“道”在“德”之先,“德”在“道”之后。《老子》通行本第1章說:“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第25章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第40章說:“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第42章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第51章說:“道生之,德畜之”;第52章說:“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這些論述,無不揭示出“道”相對于“德”在時間上的先在性。且這種時間上的先在性,同時涉及宇宙生成論和本體論兩個層面。
在宇宙生成論層面,“道”的時間先在性是一種歷史性的先在性。《老子》“道生之,德畜之”之論,闡明了“道”是萬物的生成本原以及存在依據。“道”創生萬物后,繼續內蘊于萬物,成為涵養萬物之“德”,萬物得道以生,得德以成。“道”和“德”的關系是“道”生長萬物,“德”養育萬物。換言之,“德”是“道”作為萬物生成的本原及存在的依據,表現為內在于事物的具體規定。在此意義上,可以認為“德”也是由“道”衍生而成的,是“道”的發展。
在本體論層面,“道”的時間先在性是一種邏輯性的先在性。在《老子》中,世界的統一本源并不是“有”而是“無”。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強調的便是“無”構成了萬物本體論上的存在根據。然后,就萬物之間的相生而言,“有”才成為事物化生的現實出發點——天下萬物(一個一個的對象),總是以具體的規定為其現實的出發點。“道”,作為未分化的超驗存在,就其無形質、無限性而言,可視為“無”;“德”相對于“道”,具有實存性,亦即取得了某種“有”的形態。這樣,“道”與“德”的關系和“無”與“有”的關系,便有了一種邏輯上的相通性,“道”與“德”、“無”與“有”作為世界的二重原理,并不是彼此懸隔、決然分離的。由“道”而“德”,展現為從“無”(無具體規定的未分化形態)到“有”(獲得具體規定)的過程。所以,“道”與“德”的關系,在本體論上,便是“無”與“有”的關系問題,“道”主“無”,“德”主“有”,“有”從“無”出,“德”由“道”生。從邏輯關系上說,“德”作為“道”分化的產物,是“離無而之有”(賈誼《新書·道德說》)。“道”是無形之“德”,“德”是有形之“道”,“德”生于“道”,“道”立于“德”,二者并舉,共同化生萬物。
時間順序代表了“先講原因,后講結果”的自然順序,而《老子》中“道”與“德”的關系,在時間序列上,恰好可以視為一種因果關系。無論是在宇宙生成論意義上,還是本體論意義上,我們都可以把“道”理解為“所以然”的最高抽象,視為最一般意義上的“怎是”,它是在樣態“未發之先”的本根形態;同時,可以把“德”理解為“然”的最高抽象,視為最一般意義上的“已是”,它是呈現出來的“已發之后”的樣態。“道”與“德”的關系是解釋系統和事實系統之間的關系,是“未發之先”和“已發之后”的關系,是“所以然”與“然”的關系。而“然”與“所以然”的基本關系是:“所以然”是“然”的原因,“然”是“所以然”的結果。因此,“道”是因,“德”是果,“道”先“德”后。
2.2 “道”主“德”從,主先于從
從整體-部分關系來看,“道”是整體,“德”是部分。“道”主要表現為統一性的原理,“德”更多地展示了個體性的原理。關于《老子》中“道”與“德”的這種關系,歷代學者早已進行了詳細的探討。韓非子是歷史上最早注解《老子》的人,他說:“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核理而普至”(《韓非子·揚權》)。意思是,“德”是一事物所得于“道”的一部分,事物有了這一部分,就有它的性質,是為“核理”,每一事物都有它的“德”,是為“普至”。稷下道家的文子也明確指出:“夫道者,德之元”,“道散而為德”(《文子·道德》)。“道”是化生萬物的本體,“德”是“道”之本質的流轉,“道”涵蓋了“德”的內容。受黃老學影響的儒者賈誼,也把“道”釋為整體,把“德”釋為部分:“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新書·道德說》),“德”是寓于具體事物中的“道”,是“道”的具體表現。現代學者中,馮友蘭與賈誼的觀點多有類似,認為:“道為天地萬物所以生之總原理,德為一物所以生之原理。”[6]此外,馮友蘭還曾經給出一種更形象的表述:“德是道在某一點上停留下來的”[7]。徐復觀也認為“德”是一物得之于“道”而成之于體者:“萬物得道之一體以成形,此道之一體,即內在于各物之中,而成為物所以為物的根源;各物的根源,老子即稱之為德。”[8]張岱年主張:“道”是“德”的全體,“德”是“道”的部分,“道”與“德”的關系是“德是分,道是全。一物所得于道以成其本者為德。德實為一物之本性。”[9]陳榮捷在推衍《老子》“道”與“德”的關系時,認為“道將德賦予個體事物。一方面,道遍在于萬物;另一方面,正是得之于道的德讓一物區別于他物。德是個體化的因素,它體現了明確賦予事物特定品性的原則。”[10]
總之,《老子》中“道”與“德”的關系,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部分性的“德”以整體性的“道”作為自身存在的根據。如上所述,漢語語序的“整體先于部分”原則,是指就自然的包含關系而言,部分是從屬于整體的。部分從屬于整體,“德”則從屬于“道”。對“道”與“德”的這種從屬關系,在《老子》中最明白無誤的表達無疑是通行本21章所說的:“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這句話可謂《老子》對“道”與“德”關系的總論,指明了“道”主“德”從的關系。
綜上,從時間關系來看,“道”是無,“德”是有;“道”是因,“德”是果,“道”先“德”后。從整體-部分關系來看,“道”是一般,“德”是具體;“道”是普遍,“德”是特殊;“道”是總,“德”是分;“道”是全,“德”是單;“道”主“德”從。因此,根據語序的自然原則,《老子》的文本結構應為“道-德”。
3 凸顯焦點:先“德”后“道”
將《老子》的文本結構厘定為“道-德”,因合自然之序,似乎天經地義,毋庸置疑。但是,帛書本《老子》的文本排列方式卻不符合“時間順序”與“整體先于部分”原則。一旦我們考慮到“德”既不可能在化生時間上先于“道”,又不可能上升到整體的地位,則不免產生疑惑:帛書本《老子》放棄符合自然語序的做法,理據何在?與“自然原則”相對的“凸顯原則”,恰好可以用來對這一超乎常規的做法給出解釋,在解釋的背后,我們甚至還可以體會出帛書本的別具匠心和良苦用心,它可能涉及對《老子》思想中某些隱秘而重要的問題的表達。
凸顯原則,即“說話人依據興趣改變自然語序而凸顯表達重點”[5]。如上所述,使用“凸顯原則”,其目的是為了強調“說話人的興趣、牽涉的焦點”,通常的做法是把結果放在前面,把原因放在后面。據此原則追尋下去,我們可以給出這樣一種解釋:照帛書本的排列方式,《老子》的說話重點在“德”而不在那個包羅一切的“道”:“德”既然是“道”的具體化,那么《老子》行文的目的就是在“道”的總體規律之下,強調“道”的具體實踐——“德”。這可以從“德”的傳統意涵中發現一些端倪。“德”有兩層意涵:一是“得道”,二是“行道”。
何謂“德”?《釋名·釋言語》云:“德,得也,得事宜也。”《說文解字》訓曰:“德者,得也。外得于人,內得于己也。”這種解釋的基本特點是:以“得”說“德”,“德”“得”相通。事實上,在上引《老子》的論述中,也不難看出“德”與“得”的這種聯系,而且,它們更指明了所“得”為何:“德”是“得”于“道”的結果,“德”“得”的對象與內容是“道”。對此,歷代注老者皆有明確揭示。韓非子說:“德者,得身也”(《韓非子·解老》)。“德”就是得“道”而立身。同為黃老一系的《管子》亦曾指出:“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職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管子·心術上》)。事物得其“道”從而有其“德”,“德”為物獲其“道”之謂,它明確展示了與“道”相對的“德”這一范疇的本來意涵,“德”是“道”的體現,“德”就是“得”“道”,是具體事物從“道”那里獲得的、成其為自己的本性的東西。王弼云:“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利而無害,故以德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老子注·第三十八章》)。又說:“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老子注·第五十一章》)。“道”是萬物之本根,“德”是萬物分有“道”之“所得”,即道的具體化。“德”相對于“道”,已有所“得”,或者說,物由“道”而有了具體規定。總之,得之于“道”者謂之“德”。據此,認為帛書本《老子》顛倒“道”與“德”的因果順序,將“德經”置于“道經”之前,匠心是要提醒人們注目于“得”(凸顯何所“得”、如何“得”),應該是可以成立的。
“德”的另外一層基本意涵是“行道”,此為《老子》本于古義。“道”“德”在古代是分開使用的,二字各有其義又相互聯系。《說文解字》解:“道,所行道也。”《釋名·釋道》說:“道,一達曰道路。”因此,就一般意義而言,“道”指的是道路。而從《老子》的論述來看,“道”既有形而下的“道路”,也有從“道路”引申出的形而上的“規則”、“原理”、“規律”等意。而在甲骨文中,“德”字為“循”字,表示“循行而前視”,有“遵道而得路之意”[11]。循“道”而行的痕跡,便謂之“德”。“道”為“德”之原,“德”為“道”之行。“道”貴乎行,“道之為名,所假而行”(《莊子·陽則》)。萬物循“道”而行,表現為萬物之“德”;人循“道”而行,表現為人之“德”。“行”就是實踐,故“德”是對“道”的踐行。據此,帛書本《老子》在文本排列上先“德經”后“道經”,意在凸顯“道”之“行”,“行道”之“德”是其焦點所在。
“德最好理解為一個特殊的焦點,……道與德的關系就像場域與焦點的關系。這種關系是全息式的,意思是事物整體中每一個成分都包含了簡縮的整體。一個系列的特殊的焦點建立了其世界及其環境;整體作為所有可能有的秩序的不貫通的總和,由每一個系列簡縮了。”[12]無論是凸顯“得道”還是“行道”,都可以明了帛書本《老子》的落腳點在“德經”。“道經”雖是根基,“德經”卻是主干,“道經”不過是為“德經”提供本體依據罷了。的確,從本體論角度看,“道”是第一位的,“德”的性質由“道”決定,“德”從于“道”。但從發生學角度看,“德”是使“道”得以具體化的關鍵,“道”依于“德”才能把握。沒有“德”,“道”將失去現實性。表象是“德”合于“道”,真諦是“道”賴“德”以顯。
可以認為,在帛書本《老子》中,“道”只是一種“懸設”或“懸置”,而“德”才是其著力點所在,論“道”是為了用“道”。不可否認,“道經”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論道多與人事——人生和政治問題有關,是由天道說人道,由“道”的本性推出圣人的本性,所謂“自然無為”、“虛靜”、“柔弱”等,既是“道”的特性,也是圣人的理想境界,而這便是帛書本《老子》潛藏著的一個秘密主題:它并沒有使“道”與“德”的關系突破宇宙人生的“世間性”特征而成為超越現實世界的理想觀念,而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易·系辭上》)。由此便可以解釋,帛書本《老子》為何將“德經”置于“道經”之前:是因為它覺得“德”的問題更重要,“德”是《老子》的興趣和關涉的焦點所在,形而上的“道”如果不與人生發生關聯,那么它只不過是一個掛空的概念而已,當它向下落實到經驗界時,才對人生產生重大的意義,因此,先要考慮“德”的問題,然后再去找“德”的根據“道”,在此意義上,“老子開辟了一條從天地萬物、社會人生的根源和根本處探尋人事的依據、準則、行為方式和理想狀態之路。”[13]
4 結語:“尊道而貴德”
以上基于自然原則與凸顯原則,分別給出了《老子》“道-德”與“德-道”兩種結構的理由。從文本來看,整本《老子》雖分篇而論,但“道論”中有“德”,“德論”中有“道”,或以“道”說“德”,或以“德”說“道”。“道”和“德”是相互詮釋的關系。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辨析“道”與“德”孰先孰后就毫無意義。恰恰相反,如本文開頭所言,這個問題并非無關緊要。從“道-德”到“德-道”,其意義決不局限于文本正名或結構倒置。“道-德”與“德-道”,不是“道”與“德”的簡單拼合。在兩種不同的結構中,“道”和“德”的意涵并未發生變化,二者的關系也未被實質性顛覆,惟一發生了根本變化的是對“道”與“德”關系的把握方式,由此體現出了兩種不同的思想進路和價值取向。
通行本《老子》,采取的是由“道”而“德”、以“道”說“德”、由“天”及“人”的思想進路,暗含的是對統一性原理的關注;而帛書本《老子》,采取的是由“德”而“道”、以“德”說“道”、由“人”及“天”的思想進路,暗含的是對個體性原理的關注。我們應該意識到,在《老子》中,不是唯一的“道”或唯一的“德”,而是合一的“道-德”(或者“德-道”),才是最高的本體概念,因為《老子》強調要“尊道而貴德”(通行本第51章)。“尊道而貴德”,這一主張已明確地表明了《老子》溝通統一性原理與個體性原理的趨向,它是對統一性原理與個體性原理的雙重確認。總之,那個至今未知為何人的“老子”,分篇論“道”“德”的用意,或許不過是為了方便言說而已。但是,這一做法所形成的“道”與“德”的關系域(而非單獨的“道”、“德”理念),恰恰是《老子》最大的思想貢獻,對這一關系域的闡發,至今仍影響著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
[1]李葆嘉.中國轉型語法學:基于歐美模板與漢語類型的沉思[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546-547.
[2]戴浩一,葉蠻聲.以認知為基礎的漢語功能語法芻議:下[J].國外語言學,1991(1):25-33.
[3]劉殿爵.道德經[M].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14.
[4]李一平.現代漢語語法分析[M].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153.
[5]吳春相.現代漢語句子組成單位的語序變換研究[M].濟南:齊魯書社,2013:291.
[6]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137.
[7]《哲學研究》編輯部.老子哲學討論集[M].北京:中華書局,1959:103.
[8]徐復觀.中國人性史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3:298.
[9]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52.
[10]賴蘊慧.劍橋中國哲學導論[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89.
[11]趙軍華.新編中華倫理[M].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59.
[12]安樂哲.自我的圓成:中西互鏡下的古典儒學與道家[M].彭國翔,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 364.
[13]陸玉林.中國學術通史(先秦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03.
責任編輯 劉宏蘭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3.006
B223.1
A
1004-0544(2017)03-0036-05
涂江波(1982-),男,江西豐城人,哲學博士,長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戴茂堂(1964-),男,湖北江陵人,湖北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暨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