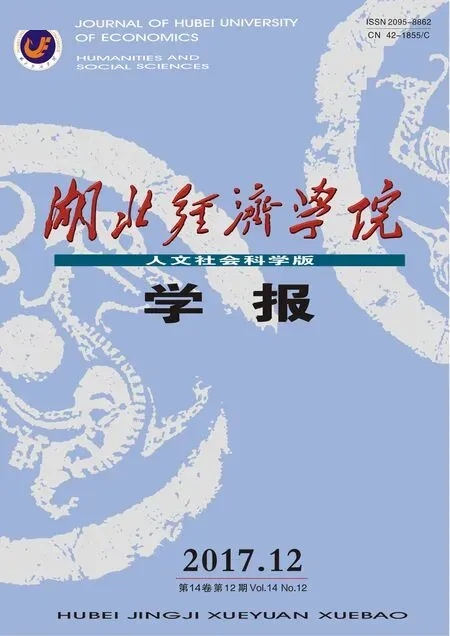“小說家”應該從諸子略中除名嗎?
(武漢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0)
“小說家”應該從諸子略中除名嗎?
楊葉青青
(武漢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0)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共收十家,“小說家”以街談巷議之內容、稗官小吏之傳播、叢殘瑣屑之意義忝列其中,其地位甚至遭到作者本人的否定,本文試圖通過厘清“小說家”這一概念在闡釋學層面和目錄學層面的雙重定位問題,為“小說家”的存在提供合理的出口。
《漢書·藝文志》;雜家;小說家;小說概念
《漢書·藝文志》是《漢書》十志之一,根據其序文可知,其作者班固對當世流傳書目的收集工作,應從劉歆所著《七略》溯源而上直至劉向《別錄》,每一略所列書籍之后,班固給出的的評論也是在參考了劉向、劉歆父子舊文的基礎上,略加批注的①。
《漢書·藝文志·總序》有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直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②也就是說秦以前的諸子文章都被付之一炬了。直至漢代,“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于是“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在這里,我們從“下及”之語便可不難看出,輯錄者在收選書籍時,首選仍是經學一類,諸子之言并不在重點關注之列。
來到“諸子”一略之中,其又有“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姚明輝《漢志注解》對此句惟“去小說家”之解讀。諸子本就不在關切之列,而“小說家”又被排除在“諸子略”可取的九家之外,“小說家”在《漢書·藝文志》中的不重要性便可不言自明了。
然而,《漢書·藝文志》中對于“小說家”和“小說”的這寥寥數筆描述:
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
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
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在后世卻成為了定義“小說”概念的先聲。這其中,后人闡釋與前人草創之間便產生了一種值得玩味的依違現象:從班固著史的角度出發,“小說家”無論如何都是拿不上臺面的,但若從文體學角度考量其歷史意義,“小說家”的成立卻又是中國文學史書寫中濃墨重彩的一筆。此二者間的巨大落差讓我們不禁想問:“小說家”是否可從諸子之說中剔除呢?本文將就此進行探討,試請論之。
一、“小說家”考辨
“小說”這一語匯確切真實的出現,要上溯到《莊子·外物篇》中,其文有“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難矣”③之語,但學者普遍認為,當時的“小說”只是和后文的“大達”相照應,“乃謂瑣屑之言,非道術所在”④,不僅和現代意義上的“小說”概念不同,甚至與《漢志》所載之“小說”也并不一致。王慶華《“小說”與“雜家”》一文認為,“小說”一詞產生于先秦諸子爭論之中,最初只是一個“社會普通用語”,“泛指與智者所論高深之理相對應的淺薄之論”⑤,《荀子》中有“小家珍說”⑥,蓋亦出于此。到了漢代,才有桓譚首次在《新論》中指出“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⑦——這是歷史上首次對“小說家”內容、體式、作用的具體說明,但也僅是一個模糊的概況,真正將其納入文學規范的仍要到《漢書·藝文志》。
錢賓四先生在《中國文學史》講稿中有“文章的體類”一節,他總結道:“中國有真正的文學當自建安時期開始。至宋元代才有西洋文學之體裁風格。在先秦諸子時代,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農家、縱橫家、小說家等各家,各家思想不同,故其文章亦不同”⑧,由于思想的不同,造成了語言上的區別、文體上的差異,如果要對各家體式進行明晰的分別,則應清理“言”、“人”、“文”之間的關系:“言”是針對作者說的,創作者試圖表達的話語就是“言”;而作者之“言”的輸出主體,也就是讀者或聽眾,指“人”;最后,“文”指的就是那些,如何將作者的描述精準度最大化的技巧。因此當我們討論某種文體時,我們最終要解決的無出于“言”、“人”和“文”這三個方面。
讓我們從“言”開始。首先,“言”從何處來?“諸子略”十家之體例,以各家由誰人所著為始,《漢志》為每一家之思想都歸納了一定的官職,從各官員的職分和地位便可以推測出各家思想所側重的方面,由此更可體現《總序》之所言“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的特點。
“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司徒之官為《周禮》之中負責教導君主禮儀教化的官員;“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其職責就是要記錄歷史上“成敗存亡福禍古今之道”,然后方知如何保持本心,“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其余諸子,如陰陽家出于義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之出于禮官、墨家之出于清廟之守⑨,縱橫家、雜家、農家又分別出于行人之官、議官和農稷之官,而“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
《漢書·藝文志》緊接著說,“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之所造也”,即這些“小說”是在坊間的街頭巷尾被拿來議論的,因為其傳播媒介是每個人的口耳相傳,又因其發生地點在民間,故這些言論的真實性與科學性不得不打上一個問號,這也正是孔子將之稱為“小道”的原因。然而根據儒家一貫重視民間聲音的傳統,孔子繼續說:盡管這些是為文人士大夫所不齒于談論的內容,但仍有它的可取之處,如果圣賢之人離這些聲音太遠,恐怕就難以獲得兼聽則明的品德,從而成為賢者了。
余嘉錫先生在《小說家出于稗官說》⑩一文中詳細考證了“稗官”的概念,他指出,就現存可考之古籍而言,先秦時期,對類似“街談巷議”的言論進行傳達的,有這樣幾種情況:
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春秋》襄十四年傳)
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過書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即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賈誼新書·保傅篇》)
《春秋》之云“士傳言”,傳的當是庶人的“謗”言,即庶人負責謗譏于野,士則負責將這些議刺的話傳達給上級,從而完成底層環節的信息交換[11]。《賈子新書》則又向前邁了一步,“大夫進謀”是向管理者提供更適用于統治的策略,一個“進”字,實際上道出了大夫工作的兩個面向,“謀”首先由大夫輸出,而輸入者顯然就是他們效忠的君主,同樣的,“士傳民語”也能體現出士所溝通的上、下兩個渠道,《國語》“周語篇”中所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12]正是雙向渠道的最佳證明,這里的“庶人傳語”,韋昭注曰: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士也。
余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中談到“士”的地位問題,認為“士”是存在于“庶人”與“大夫”之間的階級,階級之劃分對于當時的邦國而言,是其成立之根本,是以《左傳》有:“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下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 ”[13]
孟子《萬章章句》先有,“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的等級制度,又有“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14]這樣更森嚴的階級設立。也就是說,首先周朝之“士”分三層,但就地位而言,整體低于大夫,而又略高于庶人。又因為“下士”和做官的庶人獲得的經濟收入是相等的,并且這樣的一份收入足以使其無需參與耕種勞動,這讓他們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盡管已經脫離了最底層民眾的范疇,但仍是統治者維護政權穩定的第一個分野。《晉語》又有:
吾聞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于市,辨妖祥于謠,考百事朝,問謗譽于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15]。
這也是在告誡君主聽取意見于民間:需要在市朝之間采集底層的聲音,通過辨別個中之真偽善惡來對管理工作進行相應的修補和糾正。先秦時期,諫言的傳統已經被普遍接受,而根據嚴格的等級制度,庶人之語由士來轉達應當是不應有疑的,因此稗官出于士之階層也是可信的了。
訓詁學的研究成果亦可作為以上推測的理論支撐,《九章》有“細米為稗”的說法,而街談巷議,閭里風傳的又無非是一些瑣碎的言論,故收集民風之官員的選派,也應任用貼近庶民的階層,一方面這是人力資源的最合理支配,同時也是對封鎖階層間流動的必然要求。
二、“小說家”研究的尷尬局面
本文開頭引入賓四先生“言”與“人”的理論,在前文論述中已經得到了解決,但是“文”,即“小說家”的創作規范究竟如何,我們無法從班固的評語中獲得答案,這也正是學界研究中國古典小說源頭時繞不開的話題。畢竟當我們將歷史的拼圖一片片聚合在一起,以求還原出小說最早的樣貌時,我們都會感到疑惑,它似乎與魏晉南北朝開始往后的“小說”很不一樣。陳文新師在《中國文言小說流派研究》的開篇便有“‘小說’首先是故事嗎?”一問,因為班固在諸子總論中稱各家“曰‘術’(學術),曰‘說’(學說),曰‘股肱之材’,曰‘萬方之略’,都意在突出它們的共同特征:諸子以立論為宗。”[16]盡管小說不在“可觀”者之列,但“既附于驥尾”,應當也不離議論之法,然自魏晉以來之小說,都以敘述為宗,通過虛構、非虛構的情節來傳情達意,實與《漢志》之小說大相徑庭。
更有甚者,如明胡應麟就發現,《漢志》中所稱之小說,“雖曰‘街談巷語’,實于后世博物、志怪等書迥別,蓋亦雜家者流,稍錯以事爾”[17],他認為“小說家”和“雜家”是大體相同的,只不過“雜家”所言仍圍繞國體王治生發,而“小說家”議論的無非是些“家長里短”的小事罷了。
當然,我們所談到小說家之“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創作內容,也只能是一種理想情況下的抽象概括,《漢志》收錄的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小說”究竟記載了怎樣的內容,由于它們早在唐代以前便全部亡佚,今已不得而知,故我們也只能根據其題名和班固簡短的批注,以及其他文獻中保留下來的短小片段中進行推測,魯迅先生在《中國文學史略》中作了一些考證工作,華中師范大學的王齊洲教授為之專著一書,名為《稗官與才人——中國古代小說考論》[18],其史料之詳備,內容之完整,堪為學界小說源流研究的厚重之作。
從漢《藝文志》所列小說家書目之題名便可發現,其中諸如“伊尹”、“鬻子”等,本應分屬先秦諸子,其內容估計或多或少都代表了諸子的部分思想,但從“其語淺薄”的點評可看出,對于這些思想的描述,小說可能只提供最簡單的呈現,缺乏觀點的凝練;有的盡管兼有多家思想,但內容似乎不太嚴謹,風格傾向民間俚俗的普及,故被劃為閭里巷議之談也未可知。另有一些諸如《封禪方說》、《虞初周說》,題中有“說”字的書籍,前者或描述封禪之故事、傳說、意旨、器物、方法等方面的禮儀;而后者之“虞初”,據《漢書·藝文志》注:“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史記》也曾載其為張衡《西京賦》中“小說九百,本自虞初”之虞初,所以此類小說由方士所作,是沒有問題的。
至于《待詔臣饒心術》、《待詔臣安成未央術》,其一,“待詔臣”本是漢代地位極其低下的官員,被漢武帝視為“俳優”的東方朔就曾“待詔金馬門”,我們甚至可以從“待詔”二字猜測他們連正式編制都未見得擁有,因此這些人員的身份之復雜程度就可窺見一二了;其次,題中有“術”字,說明它講的就是一些方式方法,“饒心術”、“未央術”大概就是一些身體保健的民間驗方[19],它們或者與時令節氣相關,或者同星象水土有關,因此容易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因此,這些書籍只能短暫流傳而不能被長久保存,也出于這部分的原因。
如此雜亂無章的目錄分布,也令很多人產生混淆,即“小說家”與“雜家”是否可以相等同,從而放棄“小說家”類的劃分,而將名下諸書歸入“雜家”一類呢?比如,我們在《劍橋中國文學史》中看到對于雜家《淮南子》一篇是這樣描述的:“《淮南子》吸收了不同流派的政治、哲學思想,其宇宙秩序整合了古代神話、作為理想的天地主宰的完美“真人”形象、以及五行相生相克思想等若干因素。與《呂氏春秋》一樣、《淮南子》在《漢書·藝文志》中列入“雜家”類。 ”[20]“小說家”里有關儀典、方術、延年益壽的內容與《淮南子》何其相似,甚至在這些諸子散文中,敘述的筆法也已經日趨老道。
鄭樵《通志》有“古之編書不能分者五,一曰傳記,二曰雜家,三曰小說,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21]的評價。韓進廉在《中國小說美學史》中直言,諸子散文中的寓言對情節描寫的掌握,和情感表達的升華“已經符合了小說的創作原則”[22],只因這些故事已經寓于散文之中,并非獨立的問題,故而無法成為小說的直接傳承者。
綜上所述,我們至少能總結出兩點漢志中“小說家”在文學史上的尷尬局面,首先,該“小說”與近代意義上的“小說”近乎于兩種文體,漢代小說不重虛構、沒有情節發展、甚至沒有一定的篇幅,更遑論敘事手法,人稱視角的運用;其次,在分類上,“議官”與“稗官”同為諫言之官職,且“稗官”的位階離庶民只有一線之隔,“小說家”和“雜家”又實在不容易區分,“小說家”在漢代的地位確實當得起“不可觀”三個字。當歷代學者抱著追尋中國小說之淵藪的偉大希冀翻開《漢書·藝文志》時,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便足以使他們垂頭喪氣了。
三、淺議文學史研究的“戀母”情結
近代以來,無數的文獻被發現,無數的假想被驗證、被推翻,新文化運動以來,記敘文學的蓬勃發展,讓中國的俗文學異軍突起,而那些在本國悠久的歷史長河中尋找不到答案的問題,突然就得到了答案:
敦煌變文的出現,為宋元敘事文學起源的研究撕開了一道口子,為此,鄭振鐸激動地振臂高喊著:“這個謎團解開了!”和摩西的《十誡》,穆罕默德的《古蘭經》這類帶有宗教色彩的經典不同,他說:“我們的‘寶卷’、‘彈詞’,絕不可能是“從天上憑空落下來的。”[23]于是關于西域文明、敦煌文獻的研究便開始了。
但想要這個擁有三千年文明的文化國度,承認吾國之文學是抒情的文學,不是記敘的文學,并且記敘的傳統只怕還是從遙遠的中南半島,從歐亞大陸的交界處,從神秘的印度教、佛教、梵劇當中移栽過來,恐怕即便是受到了當時如梁啟超、鄭振鐸,現在如季羨林、饒宗頤這樣的大家的支持,也還是令人在情感上無法接受罷。因此我們更要在更古老的文獻里挖掘更古老的材料,用我們的史傳傳統,散文傳統充當故事情節的演繹,以證明我們的各體兼備。
石昌渝在《中國小說源流論》一書中談到了小說文體與史傳、諸子散文的關系[24],事實卻是,他討論的是西方意義上的小說,并非中國最古老的小說家之語,也就是說,天平的至少一端被人為地放錯了砝碼。《漢書·藝文志》將小說家列入“諸子略”中實乃首創,且在《莊子·外物篇》里“小”和“說”二字偶然巧遇之后,為學者追溯小說文體之源流提供了完美的目錄學史料,但是在狂喜過后,附加的過分期待便隨之到來,人們始終努力地想要為唐代的傳奇、宋元的話本、明清的章回小說找尋一粒屬于本民族的種子[25],中華民族的“戀母”情緒在文學史研究中可謂體現得淋漓盡致,這或許也是儒家文化傳統下,群體自身體會到“危機感”的一種表現。
現代人之閱讀記敘文學所為何事?朱東潤先生的見解頗具啟發性。《八代傳敘文學述論》中有《傳敘文學與人格》一篇,其中引述狄士萊里[26]的話:“用不到讀史,止要讀傳敘,因為這是不帶理論的生活。”盡管朱先生區分了小說與傳敘文學的概念[27],為虛構和真實定義了清晰的邊界,“傳敘文學底價值,全靠它底真實。……真實是傳敘文學底生命”[28],但對有關“記敘”這一文學手法的見解,是可以燭照到小說文學上去的,所謂“不帶理論”的生活,是否是要求我們拋開形而上的一切構筑,回歸到對生命本真的忠實表達,單純地享受不同情節中不同的人生體驗呢?
民國六年,錢玄同在寄予胡適的書信中提到:“戲曲、小說為近代文學之正宗:小說多用白話之故,用典之病尚少。”[29]此語也意在認可近代小說在解放人類個體意識上所作出的貢獻。然而當我們回到公元一世紀的東漢,這個模棱兩可、含混不明的“小說家”應該被排除于“諸子”之外嗎?請想象一下這樣的場景:
有一個房間,內有許多可供歸置的書柜和抽屜,然而各色不同的雜物被屋主凌亂地拋卻在房間的每一個角落。終于到了這一天,有人提出要將它們收納起來,于是他先構思好,要將貴重的物品擺在架上以供客人觀賞,要讓實用的小件放于最順手的地方隨時取用,然而還有一些零碎的小物,它既不似其他事關日常生活的用品一般富于實用價值,又不具備賞玩功用,于是整理者為它找到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抽屜,它不華麗,卻也安全無虞,這似乎是它最好的歸屬。
對于漢代小說而言,“小說家”就是這樣的一個抽屜,在現有的文學理論無法解釋其存在的當下,有一個可供其棲居的空間讓它等待,等待下一個人將其發現,這也許是兩千年前的文學家對于知識和文學所給予的最大善意罷。
注 釋:
① 《漢書·藝文志·總序》記載了,經劉向、劉歆直至班固,《漢志》成書的過程,即: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② 本文征引《漢書·藝文志》及其后世評注之諸文字,均出于(漢)班固,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后文不再贅述。
③ 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07頁。
④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頁。
⑤ 王慶華:《“小說”與“雜家”》,載自《浙江學刊》,2008 年 2 月。
⑥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85頁.
⑦ [漢]桓譚撰:《新輯本桓譚新論》,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2頁。
⑧ 錢穆講授,葉龍記錄整理:《中國文學史》,成都:天地出版社,2015年版。
⑨ 此處“守”據考也應為“官”字,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守字者官字之誤,志敘諸子十家,皆出于某官,不應墨家獨作守。
⑩ 余嘉錫:《古代小說叢考》,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版,第1頁。
[11]底層的信息交換曾一度被忽視,臺灣籍學者試圖詮釋中國社會的“底邊文化”概念。該文化所涉及的人物都是傳統意義上的“下九流”者,這類所謂的庶民在法理和個體支配上,長久以來都沒有完整的權利和自由,但他們無疑是全體社會生活中不可抹殺的環節之一,他們也有自己的思維邏輯、宗教信仰、政治意識,,如果說《水滸傳》的偉大反映在對底層游民義上梁山的豪俠情義的推重上,那么“民間的聲音”在人文學科的研究中,顯然也應獲得我們的關注。喬健.底邊社會:一個對中國社會研究的新概念[J].西北民族研究,2002-01.
[12]曹建國,張玖青注說:《國語》,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頁.
[13]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頁。
[14][戰國]孟軻著,楊伯峻,楊逢彬注譯:《孟子》,長沙:岳麓書社,2000年版,第175頁。
[15]曹建國,張玖青注說:《國語》,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頁。
[16]陳文新:《中國文言小說流派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8頁。
[17][明]胡應麟撰:《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頁。
[18]王齊洲:《稗官與才人——中國古代小說考論》,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版。
[19]參考李零:《中國方術考》,上海:東方出版社,2001年版。
[20]宇文所安:《劍橋中國文學史》,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141頁。
[21][宋]鄭樵著,吳懷祺校,吳懷祺編著:《鄭樵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22]韓進廉:《中國小說美學史》,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頁。
[23]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頁。
[24]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63-81頁。
[25]我們找到了,但它顯然并非全部。
[26]英國政治家、文學家,今譯為迪斯雷利,該句出自小說《康塔利尼·弗萊明》,見蔣承勇等著,英國小說發展史,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03月第1版,第182頁。
[27]朱東潤:《中國傳敘文學之變遷·八代傳敘文學述論》,上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07頁.“中國傳敘文學,是比較后起的文學《穆天子傳》、《燕丹子》是小說,不是傳敘。”
[28]朱東潤:《中國傳敘文學之變遷·八代傳敘文學述論》,上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83頁。
[29]黃霖,韓同文選注:《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99頁。
楊葉青青(1992-),女,湖北武漢人,武漢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明清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