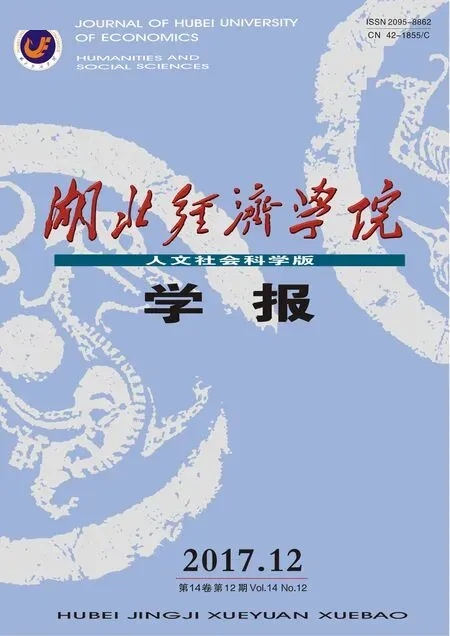新認知語用視角下調侃的認知語用機制
(四川外國語大學 法語系,重慶 400031)
新認知語用視角下調侃的認知語用機制
涂天煦
(四川外國語大學 法語系,重慶 400031)
調侃交際是“認知”和“社會”兩因素互相影響的過程。依照新認知語用學“說聽雙中心”觀點,雙方各自的“自我中心”對調侃話語的形成過程與言后之果均可產生能動的作用力。說話人在突顯原則的作用下可靈活調整話語結構、詞匯選擇、語音語調和語句節奏,從而巧妙制造特定的交際效果;聽話人也可在相同因素的影響下對說話人的話語進行不同視角的有效理解,并形成具體的個人認知。
調侃;新認知語用學;認知;社會
調侃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溝通方式,屬間接言語行為,具有豐厚的語用研究價值。與過往的關聯語用研究相比,運用認知語言學的基本原理及相應的認知方式對調侃進行分析有助于我們對此類話語有更深入、全面的認識。突顯作為認知方式的一種,近年來受到了各個學派的普遍關注。在認知語言學中,突顯指對語言所傳遞信息的取舍和安排[1]。“突顯原則”對調侃的認知機制、語用效應等均具有科學的闡釋力,說話人為制造特定的言語效果,突出交流的中心信息會合理安排話語的表達形式,聽話人也會出于不同原因對說話人的話語信息進行不同層次的有關識別。因此,調侃行為中說話人的交際意圖、語言藝術和聽話人的信息接收、話語理解等均可用突顯原則予以解讀。Giora在1997年提出的“層級突顯假設”中指出:無論直義語言還是非直義語言,其使用均受“突顯原則”統轄;突顯意義總是優先加工的[2]。但意義的突顯往往因人而異。受各類因素的影響,不同的人會對相同對象的意義進行不同層面的突顯。而調侃作為常見的社交方式,社會因素對交際雙方的話語機制自然擁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影響。因此,對調侃認知語用機制的解讀離不開對“認知”和“社會”兩個層面的深入考量,這與“新認知語用學”的基本主張是相契合的。本文以新認知語用學為理論基礎,從認知參照點和視角聚焦兩個角度探討“突顯原則”對調侃產出及理解機制的作用原理,并從社會角度考察相應機制的形成來源。
一、調侃的新認知語用視角
利用當代認知語言學的理論分析框架對語言交際開展認知研究,可以稱為 “新認知語用學”(Neo-cognitive Pragmatics)[3]。其基本觀點可概括為:交際雙方的認知經驗和認知方式決定了各自話語的表達形式和理解模式;而話語的產出和理解機制也印證了雙方特定認知方式的存在與應用。因此,新認知語用學主張以認知語言學基本原理和多種認知方式探討交際雙方的言語行為和會話含義,并在關注“合作原則”的同時,對雙方各自的“自我中心”作出了解讀。調侃作為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交際方式,調侃者與聽話人在對話中可擁有不同或一致的言語動機、心理狀態或認知能力,雙方各自的“自我中心”對調侃行為的過程與結果均可產生能動的作用力。因此,研究調侃的認知機制應從說話人和聽話人兩方面入手。運用“突顯原則”可對交際雙方的話語機制作出解讀,包括說話人的交際意圖和聽話人的理解模式等,這與新認知語用學“說聽雙中心”的基本特點相吻合。在調侃行為中,說話人在“突顯原則”的作用下可靈活調整話語結構、詞匯選擇、語音語調和語句節奏,從而巧妙制造特定的交際效果;聽話人也可在相同因素的影響下對說話人的話語進行不同層面的有效理解,并形成具體的個人認知,進而產生不同的交際結果。由此可見,“突顯原則”可作為解讀調侃認知機制的可靠方法,為調侃的認知研究提供了有力保障。
王寅(2013)對新認知語用學進行了深入討論,認為在研究語言機制的同時需將“認知”和“社會”兩方面因素有機結合起來,從社會角度分析語言認知的形成來由,以此解決“認知來源”的問題。從以往的研究成果看,Kecskes通過Sociocognitive Approch的方法表明了同樣觀點:言語交際是 “認知”和“社會”兩因素互相影響的過程。他強調:交際雙方在話語產出及理解的過程中必然受到個體語用因素的 “污染”,包括先前經歷各有不同、對語境作不同評價、意向具有動態變化性、而個體也有不同的突顯方法。
新認知語用學彰顯了未來語用學領域的發展方向,也為調侃的認知語用研究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從新認知語用學視角可深入探究“突顯原則”和社會因素對調侃行為交際雙方的不同影響。
就調侃而言,說話人的動機、目的和表達方式以及聽話人的感受、理解和反饋效果必然受到雙方個體因素的影響,而個體因素的形成自然離不開社會層面的制約。在不同語境的作用下,處于不同社會群體,擁有不同社會身份的人,由于個人經歷、認知水平,交際需求及情感狀態各不相同,對調侃話語的使用和理解也必然帶有鮮明的個人特色。因此,對調侃的語用研究,除應分析言語的產出及理解機制外,相應機制的形成來源即說話人與聽話人各自擁有的社會經歷,承受的社會影響等社會因素同樣值得關注。
二、新認知語用視角下對調侃話語的具體解讀
“突顯原則”對交際雙方認知機制的影響可從不同角度予以討論。認知參照點和視角聚焦作為突顯原則重要的表現形式,對調侃話語產出和理解機制的形成具有較強的闡釋力。此外,社會因素為交際雙方的話語機制提供了充實的認知來源,對雙方選取的突顯方式具有重要影響。下面從認知參照點和視角聚焦兩層面予以深入探討:
(一)認知參照點
從突顯層面看,調侃的運用與識別涉及到認知參照點的問題。認知參照點這一概念最初由心理學家Rosch提出。Rosch(1975)認為,語義原型(prototype)是人類對世界進行范疇化的認知參照點,人們通過語義原型可對相同范疇內的其它成員進行判別。Langacker(1991)隨后將認知參照點理論引入了認知語言學,他認為:交際中說話人通常以某突顯實體作為認知參照點,并以此激活聽話人概念系統中與之相關的其它概念,從而引導聽話人跨越心理空間,領會話語含義。
調侃是非直義語,話語的真實意圖通常包藏在命題表面之下,說話人有意采用明顯與真實意圖或相關語境不符的話語形式,以此刺激聽者產生矛盾的心理反應,進而對說話人委婉的交際方式進行識別。由此可見,調侃的非直義效應根源于“不一致性”,不一致性構成了識別調侃的認知參照點。不一致性包括命題表面與內在含義的不一致,命題信息與相關語境的不一致以及命題所指與聽話人心理期待的不一致等,這是調侃者話語藝術的產出成因,也是聽話人判別語義的認知關鍵。在具體調侃交際中,聽話人以不同實質的不一致性作為突顯實體,從自身認知經驗出發,在不同因素的影響下發現說話人是有意為之,從而成功領會話語的真實原意。請看例1:
2016年4月30日,在號稱美國政治圈“吐槽大會”的白宮記者晚宴上,奧巴馬當然不忘拿共和黨參選人唐納德.特朗普調侃一番。奧巴馬說到:“今晚他沒有來,讓我很受傷。這里滿屋子的記者、明星和攝像機,特朗普居然說不!難道這個晚宴太俗氣了嗎?”他繼續說到:“共和黨大佬們說特朗普缺乏總統外交政策經驗,但他其實一直在跟世界各國領袖們打交道,比如瑞典小姐啦,阿根廷小姐啦,阿塞拜疆小姐啦……”(摘自搜狐新聞 2016年5月4日版)
此例中,奧巴馬對特朗普的調侃屬反諷式調侃。該類調侃最常見的表現形式為字面意義與實際意義直接悖反。命題表面與內在含義的不一致性構成了反諷式調侃的認知參照點。不過,反諷話語對語境的依賴性很強,失去語境的支撐,調侃的反諷效應便不復存在[4]。從認知層面看,字面意義與實際意義屬于相同認知域內方向相反的不同極點。二者的不一致性刺激聽話人的思維在兩個極點間反復游移,并在語境的影響下最終達及字面意義的逆向極點,從而得以成功領會話語的內在含義。眾所周知,白宮記者晚宴高端而正式,當然不會是“俗氣的晚宴”。“俗氣”與“高端”同屬于“場合規格”的認知范疇,呈逆向相悖關系。二者在詞義上的直接悖反構成了突顯的參照點,再在語境的支撐下可促使聽話人順利領會命題信息的逆向意義,從而使其準確理解說話人的真實意圖。奧巴馬巧借“俗氣”一詞反向說明特朗普通常只愛出現在高檔場合,以此指責其好大喜功,偏愛作秀。反諷式調侃的另一表現形式為:命題信息與內在含義表面存在相似性,而實質卻大不相同。二者表面的相似性使得聽話人先對命題信息產生心理期待,隨后二者實質上的差異性又使得聽者的期待落空,命題所指與聽話人心理期待的不一致性同樣構成了調侃的認知參照點。該參照點的突顯效果使調侃者得以制造巧妙的話語形式,并促使聽話人最終領悟命題的真實內含。此例中,奧巴馬所言之“各國領袖”和“各國小姐”存在相似性,即同屬“外國人士”,使聽話人產生心理期待;但就外交政策經驗而言,選美小姐與政治人士畢竟完全不同,聽者的心理期待在聽到隨后的話語時瞬間落空,調侃的反諷效應由此而生。因此,信息表面相似性與內在相異性的沖突同樣突顯了反諷的效果。奧巴馬借此諷刺特朗普不懂外交,且喜好美色,終日流連于聲色犬馬之間。
奧巴馬之所以對特朗普施以調侃,并成功使聽話人理解自身意圖,背后離不開社會因素的影響。2016年,在特朗普正式當選美國總統之前,其公眾形象及競選總統一事一度引發美國乃至世界人民熱議。特朗普雖在商界擁有一定成就,但為人招搖,囂張狂妄,且談吐粗俗,不懂禮節,個人形象持續遭受影響。外加毫無政治經驗,特朗普與一位合格總統的樣子仿若相差甚遠。而作為美國前任總統,奧巴馬之前與特朗普有過摩擦,對特朗普更是持有非議,認為其人飛揚跋扈,不懂政治,“特別不夠格當總統”,尤其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兩人的矛盾更為突出。由此可見,奧巴馬與特朗普之間的沖突關系構成了說話人的調侃動機,而特朗普的公眾形象和二人間的矛盾沖突又早已為世界人民所熟知。因此,聽話人與奧巴馬擁有相同的認知背景和認知經驗,對說話人話語的領會有了關鍵的認知基礎。再在語境一致的影響下,聽話人自然能以準確的認知方式對說話人之言進行推斷,從而使得交際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二)視角聚焦
運用“突顯原則”對調侃進行解讀還牽涉到視角聚焦的問題。在CL中,所謂“聚焦”,是指人們在認知某一事物時,僅將視角固定于該事物的某一方面或側面而由此忽略其他方面(王文斌,熊學亮,2008)。陳新仁(2011)認為,視角聚焦不是一種簡單的、隨機的行為,而是一種有意識、有目的的認知過程。認知客體有時并不是一個完全客觀的屬性,認知主體會根據自己或雙方認可的興趣、需要、利益、價值觀、信仰等能動地加以選擇,從而影響自身和對方的認知過程和認知結果。因此,在調侃行為中,由于交際雙方所處的社會群體,以及由具體背景決定的社會觀念不同,相同事物在不同的人心中得以突顯的層面自然不同。不同的人會對相同事物進行不同角度的視角聚焦,從而形成不同的認知結果,進而促使了調侃的生成。請看例2:
2016年,在訪談節目《魯豫有約大咖一日行》中,魯豫深入萬達集團,采訪中國首富兼萬達總裁王健林。訪談中,當談及年輕人的奮斗規劃時,王健林向年輕人提出了一句忠告:“想做首富是對的,這是奮斗的方向。但是最好先定一個能達到的小目標,比方說我先掙它一個億。”此句一出,立刻被無數人奉為“金句”,短時間內刷爆朋友圈。網友紛紛留言表示:“這個目標確實有點小”,“看來人生務必有個小目標,比方說我先掙它一百塊”,還有網友稱“看來我的人生要破罐子破摔了”。(摘自騰訊新聞2016年8月29日版)
與例1不同,例2中廣大網友作為說話人經歷了“先理解再表達”的過程。網友先作為聽話人對王健林之言進行過濾,進而再在理解的基礎上繼續進行表達。此例中,網友對王健林之言的調侃明顯聚焦在“小目標”和“一個億”兩個詞上。從認知的層面看,由于在言語交際中說話人和聽話人會不自覺受到“自我中心”的影響,因此會對相同的事物進行不同角度的視角聚焦。與網友不同,王健林所言之“小目標”,意在告誡年輕人做事應按部就班,步步為營,“一個億”在其話語中未處于突顯位置,不屬于其話語的聚焦對象。但在廣大網友看來,“一個億”卻具有明顯的刺激效應,把一個億當成小目標更是形成了強烈的突顯效果。一個億,對于首富來說是小數目,但對于平民百姓來說卻是不可企及的天文數字。把不可能實現的目標當作“小目標”,其中的荒誕感便引發了陣陣調侃。網友之“這個目標確實有點小”,“比方說我先掙它一百塊”等調侃之言,其話語動機當然依舊建立在“一個億”和“小目標”之間的差距上。調侃背后所折射出的真實含義自然是對現實的感嘆:太多人根本無法把過高的標準當成小目標,自己的小目標往往更加實際而簡單。
其次,對王健林“小目標”之言的調侃,背后的社會原因同樣值得探討。當今時代泡沫經濟帶來的巨大壓力使無數人將目光過多投射在了生活的物質層面,把“努力賺錢”視作現實的主要矛盾和奮斗的首要目標。由此一來,“做首富”、“一個億”等與“錢”有關的話題自然在廣大網友心中得到突顯,極易受到關注。此外,當代中國競爭激烈,矛盾突出,致使不少人對社會的期望不斷降低,負面情緒難以宣泄。因此,面對緊逼的生存壓力、殘酷的競爭環境以及普通人與富人之間的巨大差距,網友紛紛借調侃之言,用自嘲的心態表達了自身對現實、對生活、對理想的無奈之情,背后的社會根源值得深思。
值得一提的是,網友對王健林之言的調侃還有語境差異的問題。事實上,很多網友未曾完整看過訪談實錄,僅從網絡截圖獲取了部分信息。若將訪談從頭至尾看完,我們便會發現王健林所言并非“無稽之談”:首先,王健林討論的是立志做首富的年輕人,而非對一般人而言。想做首富,那一個億確實不多。且隨后的交談透露出:王健林的關鍵意圖在于勸誡有宏圖大志的年輕人要敢想敢闖,且需謹慎行事,不要盲目浮躁。因此,王健林的言論實際上邏輯清晰,有理有據,完全可以接受。之所以會遭到網友調侃,究其根源,只因部分網友未和說話人處于相同的認知語境內,對說話人話語的背景知識缺乏了解,因而不能對其話語形成完整而動態的認知,才造成了“斷章取義”的后果。然而,Giora于2003年在層級突顯假設中提到,語境對語義加工確實存在影響,但作用有限,當交際內容中某成分的語義突顯異常明顯時,語境并不能起到相應的抑制作用。因此,即便部分網友未與王健林處于同一語境,“小目標”與“一個億”之間近乎荒誕的差別仍舊形成了極大的突顯效果,致使網友的視角聚焦與王健林并不一致,仍舊對其話語發出了感嘆。由此可見,調侃是有意識的誤讀,誤讀是無意識的幽默。
三、結語
調侃之所以能成為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交際形式,緣于其多元的語用效應和深刻的社會根源。運用“突顯原則”從“認知”和“社會”兩個層面對交際雙方的話語機制進行解讀不失為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認知參照點和視角聚焦作為“突顯原則”兩個重要觸角,可用以詳細考察該原則對話語機制的作用原理。此外,“突顯原則”對交際過程的具體闡釋離不開社會因素的相關制約。社會因素對交際雙方認知方式和話語機制的形成起到了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說話人與聽話人受社會因素影響而形成的實際經歷、心理動態和認知經驗等直接影響了各自認知機制的生成。
[1]王文斌,熊學亮.認知突顯與隱喻的相似性[J].外國語,2008,(1).
[2]林元龍.突顯、關聯與英語雙關的認知解讀機制[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9,(2).
[3]陳新仁.新認知語用學——認知語言學視野中的認知語用研究[J].外語學刊,2011,(2).
[4]楊慶云.認知參照點與反諷的識解[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3,(2).
[5]王寅.新認知語用學——語言的認知——社會研究取向[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3,(1).
[6]周紅輝.凸顯與言語交際[J].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
[7]Giora,R.Understanding Figurative and Literal Language:The Graded Salience Hypothesis[J].Cognitive Linguistics,1997:8-13.
[8]Giora,R.Understanding figurative and literal language:The graded salience hypothesis[J].Cognitive Linguistics,1997, (7):183 -206.
[9]Giora,R.On our mind:Salience,Context,and Figurative Languag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e,2003.
[10]Kecskes,I.On my mind:Thought about salience,context, and figurative language from a second language perspective[J].Second Language Research,2006,22(2):219-237.
[11]Kecskes,I.Socio-cognitive approach to pragmatics[J].外國語,2010,(5):2-20.
[12]Leech,G.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London:Longman,1983.
[13]Rosch,E.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s[J].Cognitive Psychology,1975,(7):532-547.
[14]Langacker,R.W.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Ⅱ:Descriptive Application[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四川外國語大學2017年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論調侃的認知語用研究”(SISU2017YY24);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項目(17Q183);黃岡師范學院教研項目(zj201783)
涂天煦(1990-),男,湖南長沙人,四川外國語大學法語系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語用學、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