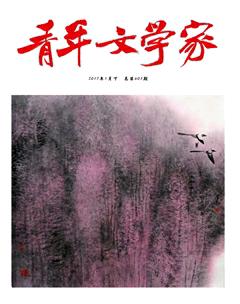淺析卞之琳英詩漢譯之“以頓代步”
摘 要:在中國現代詩史上,卞之琳的定位是一個精致的藝術家,一個卓越的翻譯家,他以自己獨特的翻譯風格,在英詩漢譯方面創造性提出“以頓代步”的翻譯方法,并遵循“亦步亦趨”的翻譯準則,一定意義上推動了中國新詩的長足發展,對中國的現代主義詩歌產生了不可或缺的影響。
關鍵詞:卞之琳;英詩漢譯;“以頓代步”;翻譯實踐
作者簡介:白玉潔(1991-),女,西北大學外語學院碩士生,從事英語筆譯研究。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03-0-02
一、引言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縱觀古今中外,詩歌名家的翻譯歷來是公認最艱難的譯事之一。如果翻譯一首詩歌,若是逐字逐句直譯出來,原文的音韻就會大為減少。因此,美國著名詩人弗洛斯曾說:“詩歌就是在翻譯中喪失的東西。”因此,無論是英詩漢譯或是漢詩英譯都要注意保留詩歌的視覺美感,準確傳達原詩的意義和意境,再現原作的藝術效果。自新中國成立至今譯者無論是質量還是數量上都有明顯提升,所采用的翻譯方法也是時殊風異,各有千秋。這一階段主要從事英文詩歌翻譯的代表有王佐良、卞之琳、屠岸等人,這一時期主要提倡采用格律詩形式翻譯英語格律詩,其中一派主張“克隆”英文原詩的韻律,另外一派主張用漢語的頓來代替英詩中的韻律,再現原詩的節奏,這種方法即由翻譯名家卞之琳所提倡的“以頓代步”。
二、百年新詩史上的“第一人”——卞之琳
“從技術上來說,卞之琳是中國新詩百年來的第一人!”這是著名學者,同時也是卞之琳的學生江弱水對其老師的評價。卞之琳(1910~2000)是我國著名的翻譯家,著名詩人以及文學批評家,曾是徐志摩的學生。著有詩歌《斷章》,作為其流芳百世的代表作。同時,他在莎士比亞文學方面也頗有建樹,為現代詩壇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其另一個重要身份即新文化運動中別具一格的詩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詩人。
作為一名譯者,卞之琳譯介的外國詩歌,主要來自英國和法國,特別是英國詩人莎士比亞和法國象征主義詩歌以及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代表詩人。其詩歌譯作經歷了從浪漫主義、象征主義到現代主義的發展道路。在他豐富的譯作當中,典型的代表作品有《英國詩選》和《莎士比亞悲劇論痕》。六十年代以后卞之琳作為外國文學研究員,對于莎士比亞文學方面頗有研究。他提出要用格律詩體的詩歌形式來翻譯莎劇,這一主張可以說是我國解放后莎劇翻譯的最高成就,是利用詩歌體裁翻譯莎劇的典范。
就從翻譯詩歌角度來看,卞之琳先生主張“破‘信達雅說。但這一主張并非表示他對這些理論或學說的全盤否定。只是出于對詩歌文體特殊性的考量,他提出在進行詩歌翻譯時,不能拘泥于以上這些理論,而應該量體裁衣,根據詩歌自身的特點發展出最適宜于詩歌翻譯的理論或策略。在英詩漢譯中,他創造性提出了“以頓代步”的翻譯策略,將譯詩中的詩句也劃分為不同的音組以反映原詩中的節奏,從而使譯詩與原詩在詩歌韻律上做到相似成為可能。
三、“以頓代步”譯詩法
格律體英語詩歌應如何翻譯,這是長期有爭議而未能解決的一個問題。就現在來看主要可歸納為三種方式:(1)采用中國傳統詩、詞、曲的格律或其變體;(2)不拘格律,采取自由體或散文詩的格式;(3)移植英詩的格律,最顯著的就是“以頓代步”的方式,即以漢語中的頓代替英詩中的音步(foot)以再現原詩的節奏。“以頓代步”法通常強調原文的韻式也應在譯文中加以復制,以這種方法譯詩,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追求形似,同時再現音美的探索創新,當然后來也的確產生了一些形神兼具的譯作。
在《關于詩人譯詩的對話 ——文藝評論家屠岸訪談屠岸》一文中,對于如何看待翻譯詩歌時所采用的“以頓代步”原則這一問題,屠岸這樣講道:“在惠特曼創作出自由體詩(free verse)之前,幾乎所有的英語詩歌都是格律詩(regular verse),連素體詩(blank verse)也是有格律的,只是不押韻而已。如果僅僅翻譯詩歌的意思,僅僅忠于詩歌的內容,而不顧其形式,那就是一種偏枯,也就沒有詩了。到現在為止,“以頓代步”是兼顧詩歌內容與形式的最佳譯法,也可以說是翻譯詩歌的基本原則。孫大雨首先提出了這一方法,用漢語的“音組”譯英語的“音步”,但沒有做到等行。后來,卞之琳完善了這一方法,并且用這個譯法翻譯了莎士比亞的四個悲劇和一部分十四行詩。卞之琳稱“音組”為“音頓”或“頓”。卞之琳的這種譯法可以歸結為一句話:“等行、以頓代步、韻式依原詩”。其中,以頓代步是最主要的,做到了嚴格意義上的以頓代步,譯詩和原詩自然就會等行了。
因此,可以說卞之琳所提倡的“以頓代步”的譯詩思想對于我國詩歌翻譯做出了卓越貢獻,他在保持原有英語格律詩歌結構的基礎上,使那些對英文不熟悉的中文讀者們更好地去理解英語詩歌,并且在后世的詩歌翻譯中扮演者積極的引導角色。
四、翻譯實踐應用
卞之琳不僅主張翻譯英語格律詩要采用“以頓代步”的方法,而且在他的翻譯實踐中,也以身作則,努力實行。以他所譯的華茲華斯的《孤獨的割麥女》(The Solitary Reaper,1807)第一段為例:
The Solitary Reaper
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
Yon solitary Hig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Stop here, or gently pass!
Alone she cuts and binds the grain,
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
O listen! for the Vale profound
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
孤獨的割麥女
看她,在田地獨自一個,
那個蘇格蘭高原的少女!
獨自在收割,獨自在唱歌,
停住吧,或者悄悄走過去!
她獨自割麥,又把它捆好,
唱著一只憂郁的曲調,
聽啊!整個深邃的谷地
都有著一片歌聲在洋溢。
這首詩的英文標題是The Solitary Reaper,中文一般譯作《孤獨的割麥女》。這首詩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威廉·沃茲華斯的典型代表作之一,詩人通過利用平鋪直敘的敘述詩體和樸實簡潔的語言,表達出他對割麥女的關心、同情及其對割麥女美妙歌聲的迷戀。全詩一節八行,共計四節,多采用抑揚格。文中較為明顯地體現出沃茲華斯的浪漫主義文學風格。以第一節為例,祈使句式開頭,突出視覺和聽覺。這之中大量使用了表示孤獨的詞語來形容割麥女,事實上這也是詩人對自身孤獨情懷的寫照。首先翻譯詩歌首句”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卞之琳采用“以頓代步”的翻譯方法,用漢語的“四頓”替換文中的英文“四音步”形式,將其譯作:“是她/在田地/獨自/一個”。并且在語氣上也保留了原文的祈使語氣,將“Behold her”譯成“看她”。此處以重復的方式將“by herself”翻譯為“獨自……獨自”,對原文適當進行伸縮。這里譯作排比分句的方法再現了原作思想內容。第三聯的翻譯尾韻與上下文相呼應,表達出割麥女的孤獨。末尾兩行作者以“profound”、“overflow”和“sound”三個詞語描寫了割麥女動聽的歌聲,而卞之琳則將其處理為“深邃”、“洋溢”、“歌聲”三個美詞。從上述例子中不難看出卞的譯作更為突顯其自身的翻譯主張,無論從藝術形式還是思想內容上都再現了原作的精華。
五、總結
“未經過藝術過程者不能成為藝術品,我們相信內容與外形不可分離”。卞之琳創作態度嚴謹,孜孜不倦地探索"藝術過程"中的轉化與表現,即使對新詩的外部形式也刻意追求變化和創新,更不用說在詩的意象、內容方面。他堅持不懈地進行詩歌創作和理論研究,成功地實驗和引進了西方多種現代詩歌形式;其所提倡的“以頓代步”作為英詩漢譯的重要方法之一,在翻譯實踐中得到不斷完善和發展,對中國象征主義、現代主義詩歌的發展開拓了新的景觀,有著很大的啟蒙意義和重要的貢獻。
參考文獻:
[1]劉重德.翻譯論稿[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2]江弱水.卞之琳詩譯研究[M].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3]卞之琳.英國詩選[M].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4]盧煒.關于詩人譯詩的對話—文藝評論家屠岸訪談[N]. 文藝報, 2013-7-29(3).
[5]王雅瓊.卞之琳詩歌翻譯思想探究[D]. 南京: 東南大學英語語言文學, 2014: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