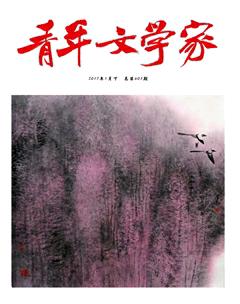探尋文學演進的規律及其啟示性意義
作者簡介:伍靜(1984-),四川瀘州人,復旦大學文學學士。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03-0-02
老子早在先秦時代就提出“反者道之動”(《道德經》,第四十章》)的深刻智慧。所謂“反者道之動”,老子認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道德經》,第二十五章》),也就是說“反者道之動”是在相反相成中不斷的循環往復。
就中國詩歌和西方文學流派嬗變而言,其運動路徑從文學史角度都可以表述為:從產生、發展到高潮(正反融合的中和平衡)——再到超出平衡進而矯枉過正、最終衰落——然后又否定之否定式回歸——這樣一個“反者道之動”的循環往復過程。
一、從中國詩歌的發展概況及文學流派的嬗變來闡釋其變化規律與特征
從《詩經》、《古詩十九首》開始了詩歌的興寄傳統;到了建安時期,興寄言志的傳統得到了進一步的繼承和發展,形成了“魏晉風骨”這一美學特征:“政治理想的高揚,人生短暫的慨嘆,強烈的個性表現和濃郁的悲劇色彩”。[1]
“到了梁陳時期,在以宮廷為核心的文人創作中,應詔詩、容物詩、艷情詩迅速發展。歌詠身邊瑣事、描寫月露風云成為詩歌主流,漢魏以來在詩歌中思考人生意義、追求遠大理想的傳統便逐漸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齊梁式的‘弄花草,嘲風月,是一種缺乏言志述懷的深刻內容和剛健骨力的創作風尚的齊梁綺靡文風。”[2]
及至初、盛唐,對齊梁靡風又有了批判式的革新和繼承,同時強調風雅的復歸。在融合正反(魏晉風骨和齊梁文風)的基礎上,呈現出集大成的大唐之音。殷潘《河岳英靈集序》稱之為:“既閑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達到“神來,氣來,情來”的“既多興象,復備風骨”的完美詩境。[3]至此唐詩在興象雄渾和聲彩兼備的正反融合下,達到了詩歌發展的高潮。
詩變于盛衰之際,詩歌的發展在唐代到了極致之后,宋代詩歌想超越唐詩的成就就顯得非常困難。江西詩派提出了一些“脫胎換骨”、“點鐵成金”的辦法,但也過于理想化,隨著江西詩派的發展流變而出現了偏移:江西詩派把學古作為創作的主要來源,參死句,而不像早期江西詩派的創始者那樣在學古中有所創新,因而形成了擬古、因襲的弊病,最終走向了沒落。雖然宋詩發展中也有像蘇軾詩那樣的代表宋詩的最高成就,但總體來說,宋詩的光環已經被宋詞所取代,詩歌走向衰弱,并不是說后世詩歌沒有好的作品,本來詩歌的優劣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只是能像唐詩一樣那么大范圍、名家輩出的時代已經遠去。
江西詩派以后,嚴羽在其《滄浪詩話》中提出詩應該學習盛唐,以“興趣”為主,注重“羚羊掛角,無跡可尋”以及提倡“言有盡而意無窮”朦朧含蓄的意境美,也就間接針對了江西詩派的以學問為詩、以理為詩的詩法弊病,一定程度上是對江西詩派后期以學問、以理為詩的揚棄和反叛。可見,詩歌的發展又在矯枉過正中向相反的方向變動。
再到后來的前后七子的復古主張,又呈現一定程度上學古習古式的復古,雖然同江西詩派的學古因襲有所不同,但也可也看作某一層面的反向運動;在針對前后七子復古的基礎上,唐宋派、李贄的“童心說”以及公安派的“性靈說”等又體現了對前后七子提出的理論的偏移與否定。
從上可以看出,宋詩的整體發展過程呈現出“否定之否定”式的循環往復的運動。在這個過程中,各流派之間并非完全的否定和二元對立,也有一定程度上的繼承和相互吸收,盡管發展過程中還有其他流派不同的觀點和主張,但大體的方向呈現產生—發展—高潮(正反融合)—極致和矯枉過正—否定之否定的循環、脈絡、周期性的過程。
因此,總結以上各朝代的發展脈絡不難看出,從漢魏以來注重風骨、興寄到齊梁靡音或宮體駢儷的轉向;到唐詩的兼容并蓄、相反相成的集大成從而達到詩歌發展的高潮;再到宋以后偏執的發展導致擬古、因襲嚴重,以及過分主理——以理為詩、以議論為詩等使詩歌的意蘊和審美大大減弱而開始逐漸走向衰落。其發展流變、特征正好體現了從產生、發展、高潮(正反融合的中和平衡),到超出平衡的極致、矯枉過正的偏移以致最終衰落,最后又否定之否定式的循環往復回歸這樣的過程。
二、從西方文學流派嬗變來探討其發展規律
托多洛夫提出一種文學史演變模式——“白天/黑夜”模式:即一種文學潮流之后,往往是一種與之相反的另一種文學潮流;他還曾指出,“在詩學歷史上似乎有從‘有機模式(一種文學形式的產生、發展、成熟,死亡)到‘辯證模式(命題-反命題-綜合)的過渡”。[4]
而從西方文學評論潮流的幾次轉移來看,朱立元認為,出現了“從重點研究作家到重點研究作品文本的轉移。在19世紀以前占主流地位的浪漫主義、實證主義等都強調了作家的主體地位,更關注作家的生平、傳記等研究。到了20世紀20、30年代,隨著俄國形式主義、語義學和新批評等學派的崛起,西方研究的重點又轉向了文本。俄國形式主義提出的文學性問題以及新批評學派的“意圖謬見”、“感受謬見”等都強調了對文學作品內部的回歸,割裂了與文學作品外部與文本之間的聯系。到了結構主義,羅蘭·巴特甚至認為,作品誕生后,作者已死。再到后來的第二次轉移,又從作品文本轉向讀者接受方向,這個轉移到解構主義達到頂峰,每一次轉移的結果都導致對前一種研究思路的總體性揚棄。[5]這兩次轉移總體上呈現出在發展過程中向相反的方向轉化。
而現在備受重視的“文化研究”學派,既關注除文本以外的作者、歷史、社會、意識形態等外部研究,也關注作品文本以及文本的意識形態和文本所潛藏的意義生成與意義解讀。馬黎明認為,“文化研究本身就是多學科聚合的產物,批評性話語分析綜合了話語理論、分析哲學、精神分析等方法論上的優勢,既超越了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分歧,又匯集了現代思想文化主要潮流的方法論特征并化合為一種全新的闡釋藝術。對于文學文本意義的解讀來說,文化研究以學科間性或學科互涉切合了文學意義的前學科性,同時也消除了所謂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分歧”[6]。從他的論述中不難看出,文化研究綜合了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方法論,體現出融合包容、集大成的特點。可見,西方文論發展從內部研究對外部研究的反叛和顛覆,再到后來文化研究對其內外部的兼容并蓄與融合,使文學研究或文學意義的闡釋更具有合理性,而不只是偏執于任何一方,不管是只專注于外部研究還是只專注于內部研究都體現了思維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三、揭示變動規律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性意義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中國詩歌的發展還是西方文論的流變,到達最完美狀態的路徑都是通過對正反兩方面特質的吸收、融合進而達到合一、不偏不倚的中和狀態。
而儒家的“中庸之道,無過無不及”、道家的“正反相生,相反相成”、佛家的“色空不二”、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也從不同角度表明:事物的存在和發展都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或非此即彼,而是此有故彼有的相互融合。
認識到這個特點,需要我們做到思維開闊而不故步自封,不僅要看到正反相生、相反相成這樣對立統一的融合,還應該看到事物發展的不平衡傾向,避免矯枉過正,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學會在動態中保持相對的平衡——用“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的智慧實現“去甚、去奢、去泰”。這對我們研究文學問題、發現文學演進的規律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1]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三版,第二卷,第33-35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葛曉音著:《唐詩宋詞十五講》第二版,第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3]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三版,第二卷,第196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4]托多洛夫:《結構主義詩學》,轉引自:朱立元主編:《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第三版,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第185頁。
[5]朱立元主編:《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第三版,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第3頁。
[6]馮黎明著:《學科互涉與文學研究方法論革命》,武漢大學出版社,第1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