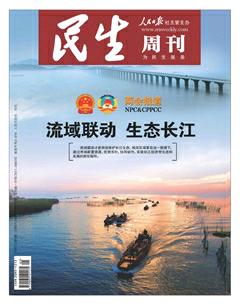上學早點遲點都別急
劉洪波
過度的“起跑”心態,本身就是一種非理性的東西。從“起跑”畸形到“搶跑”,更是一種病態。
教育部通知做好今年義務教育招生入學工作,就讀一年級兒童截止出生年月由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根據法律規定和實際情況統籌確定。8月31日滿6周歲還是不是小學入學的鐵定條件,就是各省份的事情了。
在社會輿論熱議此“新規”時,教育部又表示,義務教育法規定年滿6周歲兒童應送其入學,具體截止日期的確定,一直是由各省份“統籌實施”中作出具體規定。這就是說,教育部表示自己不過是重申舊例,沒出臺新規。
舊例被作為新規解讀,說明上學年齡的算法有著多大的社會關切。
有報道說,2015年廣東兩會上,媒體詢問省教育廳廳長能否打破8月31日前滿6周歲才能入學這個硬性條件,得到的回答是,這是全國通用做法,總得有截止日期。各省份統籌,為何統籌出“全國通用做法”,殊堪玩味。此次教育部重申 “不會統一規定具體入學年齡截止日期”,應當也能讓人們明白,這個眾所關注的問題要由誰來解決,并催促各省份真正統籌自己,別去搞“全國通用做法”吧。
“總得有截止日期”,就得是8月31日嗎,為何不是滿6周歲的當年直至12月31日都可以?有人會說,那晚一天出生的兒童跨了年,又會不滿意了。我想,規定滿6周歲當年都可入學,不過是讓部分家長能夠選擇當年還是次年入學,并非強制性地要求當年滿6歲孩子都得入學。至于那些孩子次年才滿6周歲的家長,當年孩子才5歲,孩子之間半年之差,注意力、理解力、自理能力差距明顯,想象中這些家長可能有不滿,但真的愿意讓孩子5歲就上學去跟6歲以上的大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線”嗎?
過度的“起跑”心態,本身就是一種非理性的東西。從“起跑”畸形到“搶跑”,更是一種病態。相當長一段時間,整個社會的“年輕化”追逐,對人們普遍想要“搶早”有重要的影響。早工作早賺錢,年齡越小競爭越占先,所有的機會都在向更具“年齡優勢”者開放,人們當然要避免“輸在起跑線上”。但對孩子來說,家長過早使其背負學業、競爭、“成功”的包袱,犧牲掉孩子的童年快樂、正常身心成長過程,造成其發展的單面向,又怎樣判斷得失?
社會也在趨于成熟,亟不可待的“追趕”心態會被從容不迫的“自信發展”替代,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將取代GDP主義,幸福將比“成功”更加受人關注,自我安適的生活品質將比出人頭地更加令人看重,退休年齡延后使人生有更多的時間工作,這些都趨向于讓人們更加重視孩子全面健康地發展,更加希望給予孩子充分的自由和陽光。從普遍的窘迫到普遍的小康,進而邁入更高的發展水平,搶跑爭先、唯得是務的峻急心態要得到改變,孩子不再擔負“成龍”的重壓,父母不再視孩子將來“做普通人”是一種人生失敗,健全的社會心態一定會養成,那么孩子提早或推遲一年半年上學,真的值得在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