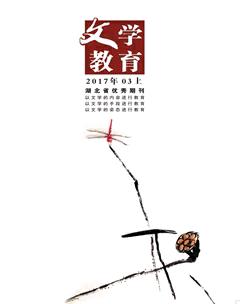比較張愛玲和亦舒筆下的薇龍和喜寶
內容摘要:張愛玲筆下的薇龍和亦舒筆下喜寶有著相同的遭遇,都在求學但又家庭貧困,但細究兩位處于都市之中的女子淪落的原因又不盡相同。對物質的渴望、道路的選擇、情感的需求、女性的自主意識在兩個時代發生著不同的變化。雖相隔兩個時空,張愛玲與亦舒通過對兩性關系冷靜地體察,對女性自身的缺陷毫不諱言,對女性的命運發出深沉的叩問。
關鍵詞:女性 欲望 缺陷
很多人喜歡把張愛玲和亦舒放在一起,并有這樣的一個公式:喜歡亦舒的人一定喜歡張愛玲,喜歡張愛玲的一定喜歡《紅樓夢》。因為張愛玲說人生有三大恨事:一恨海棠無香,二恨鰣魚多刺,三恨紅樓未完。”亦舒說她有三大崇拜:“我崇拜魯迅,崇拜曹雪芹,崇拜張愛玲……”[1]
兩位同樣都是都市女作家,一位與香港有緊密聯系,一位生長在香港。都受過良好的教育,都同樣有中西方的文化底蘊。都創作女性視角的言情小說,同樣的對兩性關系有冷靜地體察,同樣對女性自身的缺陷毫不諱言。亦舒有很多小說與張愛玲的小說題材類似,如敘述戀父情節,張愛玲有《心經》、亦舒有《圓舞》;同樣敘述年輕女子的沉淪墮落,張愛玲有《沉香屑──第一爐香》、亦舒有《喜寶》。
薇龍和喜寶有著相同的遭遇,都在求學但又家庭貧困,薇龍為著自己的學費投靠名聲不好的姑母梁太太而淪為交際花;喜寶同樣也是為了籌措劍橋大學的學費而出賣給大富豪勖存姿。她們一開始剛開始都想保有自己獨立的追求,想要保存自己的人格獨立,比如薇龍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禮相待,外頭人說閑話,盡他們說去,我念我的書。”而喜寶對勖存姿提出的唯一要求也是要完成自己的學業。可是三個月工夫,薇龍“她對于這里的生活已經上了癮了。”喜寶也是如此,在擁有了金錢之后就覺得失去了求學的意義,以前要讀書就是因為想賺更多的錢。
一.對物質的欲望:隱秘與坦白
雖然薇龍與喜寶命運相似,但細究兩位女子對物質的態度,一位“隱秘”,另一位則非常“坦白”。
薇龍初到姑媽家,一邊說:“這跟長三堂子里買進一個人,有什么分別?”[2]一邊卻“忍不住鎖上了房門,偷偷的一件一件試穿著”。雖然態度隱秘,但女性的虛榮與不堅定在這里也一覽無余。在姑母的家中,各種聚會、沙龍、攀比,豪奢的生活逐漸蠶食薇龍最開始堅定求學的心。到最后司徒協給他手鐲,她漸漸適應了這種以美色兌換物質的生活了。
喜寶一開始的態度就很坦率,她說被自己幼時的貧困生活嚇怕了,所以她對金錢的態度很明晰:“如果有人用鈔票扔你,跪下來,一張張拾起,不要緊,與你溫飽有關的時候,一點點自尊不算什么。”[3]“假如有人來問姜喜寶:女人應該爭取什么?我會答:‘讓我們爭取金錢,然后我才告訴你們,女人應當爭取什么。”
時代發生變化,雖然對物質的態度雖然從隱秘到坦白,女性的聲音從低微到響亮。但在香港這座紙醉金迷的都市中,物質決定一切的環境并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女性對物質的依賴、對男權的依賴仍是女性的痼疾,女性傳統意識的狹隘仍然導致女性出路的狹窄。兩位作家對女性的體察、對社會環境的清醒認識是一脈相承的。
二.道路的選擇:陷落與主動
為了滿足自己的物質欲望,薇龍和喜寶都做出了出賣自己的選擇。但兩人對道路的選擇從個人意志上來說是有明顯區別的。薇龍懷著求學的目的去投奔姑媽,第一次見到姑媽,從姑媽的態度、下人的議論、周邊的環境,薇龍就隱隱覺得不妥。但她單純地認為自己能抗住誘惑,堅定心思讀書。后來,薇龍逐漸明白姑媽的目的,就是把自己作為勾引男人的誘餌。可是這個時候,她沒有堅定的意志讓自己離開,反而使自己更加深陷其中。她雖然宣稱要回去,甚至買好船票,結果身體卻生病了。這場病也讓她自己意識到也許生病就是給她自己的拖延找了一個絕佳的借口。她的反抗和掙扎如此虛弱無力,最后變成對姑媽的順從:“你讓我慢慢學呀!”薇龍的單純和軟弱讓她逐漸失去自信、喪失人格。
喜寶所在的時代有了巨大的進步,環境一更為開放,所以喜寶的欲望也就更多。由于她從小不堪的社會處境,她的目標很明確,她為自己設計了一條從劍橋讀法科再進英倫皇家律師協會再到獲得掛牌律師資格,她想“揚眉吐氣”“鶴立雞群”。喜寶相對薇龍來說是主動出擊的。首先她就很明確地想利用勖存姿來幫助她完成學業。因為她的精明、世故和對自己地位最清醒的認識,她成為了勖存姿最喜歡的情婦。在勖存姿死后,她又獲得了巨額的財產。但小說的最后,喜寶對著滿屋子的金錢卻沒有一絲歡喜,變得更加虛無。
無論是被動陷落還是主動出擊,繁華都市,其實就是欲望的沼澤地,女性沉淪其中無法自拔。薇龍和喜寶都走上了同樣的命運軌跡,薇龍是在朦朧狀態下半迫半就選擇的,而喜寶是在清醒的狀態下對生活進行自認為冷靜的判斷而作出的決定。她的選擇是自以為理智的、自覺的。如果說薇龍是半夢著的,喜寶就是半醒著的。在這半夢半醒之間,她們都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生命中的亮色。
三.情愛的需求:沉迷與不屑
細究兩位女子出賣的原因,她們是各不相同的。薇龍為愛、喜寶為錢。這也就決定了兩人對情愛的態度也截然不同。
葛薇龍“明明知道喬琪不過是個極普通的浪子,沒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蠻暴的熱情”。正是這種熱情,薇龍對喬琪這個情場浪子情有獨鐘。她幻想自己能從喬琪那兒得到愛情,她也幻想能用婚姻換來喬琪的不同對待。但最終,她落到了不是為梁太太“弄人”,就是為喬琪“弄錢”的地步。小說結尾,薇龍與喬琪共度新年,逛新春市場,外面的火樹銀花,看似熱鬧,實際不過一場虛無。
亦舒的筆下,喜寶對感情是不屑的。她與宋家明產生了感情,她也內心種種算計:“但宋家明能愛我多久,我又能愛他多久?我是否得每天煮飯?是否得出外做工?是否得退學?是否要聽他重復自老板處得回來的嚕蘇氣?是否得為他養育兒女?”即使她后來愛上了一位德國教授,對敷衍勖存姿感到厭煩,打算做出自己的努力,勖存姿用獵槍射殺了這位年輕的教授并用金錢洗脫了自己的罪責。勖存姿曾問過喜寶是否后悔,喜寶說也能清醒地說出不,雖然她心里有后悔,但“后悔管后悔,過管過”。
薇龍和喜寶的環境不同,對愛情的態度也不同,但女性內心的軟弱與虛無在這里都得到了充分體現。最終,薇龍選擇的是依賴沉迷,自欺欺人;喜寶選擇的是滿屋子的金錢和無愛的人生。
四.女性自我意識:自卑菲薄與自我認同
在張愛玲的筆下,薇龍自始至終都是一位軟弱的小女子,雖有個人意愿,但始終被環境推著往前走。學業、愛情、婚姻,她都沒有明細的打算和堅定的目標。薇龍的自我意識是沒有任何覺醒的,在愛情和物質面前,她一步步失去自我,迷失其中,泥足深陷。她雖然有強烈的直覺,但也沒有自信可以自我救贖。潛意識的渴望讓她選擇寧愿在夢中沉醉。
在亦舒的筆下,喜寶始終是理智、清醒的。她明白自身的優勢,也有自己明確的追求。與薇龍沉醉在愛情中不同,喜寶是有明確的事業規劃。雖然她的規劃走錯了路,選擇用美色去換來資助。從薇龍和喜寶可以看出,隨著時代的變化,女性內心的渴望從單純到復雜,從僅僅想獲得愛情婚姻到對事業和社會地位有了追求。從薇龍的自卑菲薄到喜寶的自我認同,女性的自主意識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雖然這種進步并沒有給“薇龍”和“喜寶”們帶來實質性的變化。
兩位作家生長和生活的環境一是上海,一是香港。大都市文化和都市女性的命運是兩位作家都極為關注的。張愛玲出生于沒落貴族,新舊交替的時代讓她洞察出女性命運的悲涼;亦舒曾留學英國,當過記者、酒店侍應總管及公關、編劇、政府新聞官。豐富的經歷、敏銳的觀察讓她總是能從獨特的角度對都市女性進行描繪。兩位作家以完全的女性視角和絕對的女性主體來敘述女性自身的故事。最可貴的就是兩位女作家均對女性自身進行了嚴格的自省和解剖。
一直以來,男性都是社會的主導,女性是社會的附屬。雖然一直也都有為女性呼喚吶喊的聲音,但這些聲音大多都是男性作者所發出的。或多或少,這些吶喊和主張都是男性根據他自己的理解來發出的。更有甚者,他們主張的女性獨立只是去女性化,成為另一種“男性”。兩位女作家為我們揭示了女性痛苦的根源,從古至今,女性的生存、生長、生活長期依附于男性,也就造成了女性不同程度的“依賴”。或是有敏感的自覺,但除了依附看不到別的出路,如薇龍;或是有清醒的認識,但追求地位的道路還是選擇依靠男性,如喜寶。
這種對女性自身嚴格的反省和解剖讓我們看到了女性自身的缺陷。除開社會阻力、男性的壓迫,女性自身的缺陷也是造成女性悲劇的主要原因。女作家對女性的書寫和男性不同,女性形象不再是男性符號系統下的解釋和定義。讀者在這里直接感受到了女性的心理需求,感受到了時代女性的特色。
張愛玲在冷冷的旁觀中為我們道出了諸多女性的一個個故事,亦舒在尖銳犀利的議論中為我們講述了眾多女子的一個個想法。都市文化的投射、物質力量的“神話”、香港的時代變遷都在兩個女作家的筆下一覽無余。張愛玲是上海灘的一抹傳奇,亦舒是香港女子心中的師太。這兩個聰慧的女子,創造了一條情愛畫廊,以十丈紅塵,萬般世相,成就了一部部都市女性傳奇。
參考文獻
[1]羅孚:《香港有亦舒》,天涯社區網轉載。
[2]張愛玲《張愛玲文集》,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37頁。本文《沉香屑──第一爐香》選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3]亦舒:《喜寶》,新世界出版社2007 年版,第56頁。本文《喜寶》選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作者介紹:余醴,湖南汽車工程職業學院講師,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