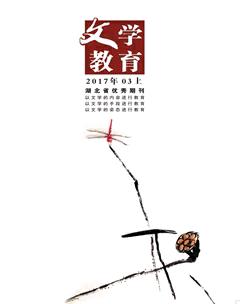施害者與受害者的雙重人物形象分析
內容摘要:電影《青紅》、《我11》、《闖入者》是王小帥以“三線生活”為主要內容的三部曲,再現了處在社會變革時期三線工人的社會生活與思想狀況。他們中的一群人在時代與歷史的浪潮中成了無辜的受害者和粗暴的施害者。本文主要分析電影中擁有施害者與受害者這樣一個雙重身份的人物形象,探討王小帥塑造的這種雙重人物形象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感受大時代變動給個體帶來的創傷。
關鍵詞:王小帥 三線生活 施害者 受害者 雙重人物形象
1966年國家提出“開發大三線”,為響應支援三線建設的號召,一大批工人來到建設三線的窮困山區。幾十年后,國家戰略的調整、時代潮流的進步和身處異鄉的孤獨,逐步擊碎了這群三線建設者的堅守信念,焦慮與恐懼充斥著他們的生活。隨之而來的是他們日益濃烈返鄉的愿望,仿佛只有返回家鄉,才能彌補他們內心的不安和被遺棄的失落,給他們的生活帶來新的希望。電影《青紅》就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展開,青紅父親一心回到上海,但他的返鄉執念一步步摧毀了他的女兒。《闖入者》里的老鄧也在爭奪返回北京的名額中,背棄良知摧毀了另一個家庭。《我11》則為我們展現了文革時期三線工人和他們的子女精神上的壓抑與扭曲。
王小帥的三線三部曲,既是對當時三線生活的一種真實再現,也蘊含了他對歷史和人性的思考。他將鏡頭聚焦在一群普通工人身上,他們被王小帥賦予了一個復雜雙重身份——可恨的施害者與可憐的受害者。王小帥通過塑造這一類雙重人物形象,清晰展現了大時代變動帶給普通個體的創傷、帶給底層人物的傷害。
一.施害者與受害者的復雜雙重性
在王小帥的三部曲中,我們沒有那種大奸大惡的既視感,一切都緩慢鋪陳開來。《青紅》中老吳唯一的生活目標就是回到上海重新生活。正如他對妻子壓抑的怒吼:“我就是要我的孩子,不能再跟我們一樣有一個同樣的十幾年。”然而,困守三線的幾十年早已磨平了當年的意氣風發,時代變革的浪潮也拋棄了他們,強烈的回家欲望與自卑感讓老吳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的兒女身上。面對這樣一位被焦躁、憤怒和壓抑緊緊包圍的父親,青紅和當地“小赤佬”小根的愛情注定會引起父親的強烈反對,他甚至認為這是對他返回上海的一種挑釁。責罵、跟蹤、監視、囚禁充斥著青紅接下來的生活,女兒的教育問題也成了青紅父母之間矛盾的導火索。父親老吳對當地青年小根的輕視嘲諷,激起了這個男孩隱藏在內心的自卑與怨氣,出于對青紅一家“上海人”身份的仇視,他選擇強暴青紅來報復他們。家庭的冷酷、戀人的背叛,讓這個正值花季的女孩兒變成了一個癡兒,小根則為他的沖動行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小根是青紅愛情與生命的施害者,也是被青紅父親侮辱輕賤的受害者。老吳如愿以償返回上海,但卻是以女兒瘋傻、夫妻離異、一個年輕生命的消逝為代價的。與其說老吳返回了故鄉,不如說他是逃離了腳下這片土地。父親老吳是這個家庭、是女兒愛情與精神、是小根生命的施害者,同時也是那個變革時代的受害者、棄兒。
《我11》呈現的只是一個11歲孩子的朦朧感受。因為謝父調動工作的原因,致使妹妹覺紅被謝父的上級老陳施暴強奸,周圍人的異樣眼光與流言蜚語又對覺紅造成了二次傷害。看著沉默自卑的妹妹,瘋狂極端的覺強將內心的不公與憤怒全都訴諸暴力,殺人、逃逸、燒廠。然而突如其來的一場大雨卻淋熄了覺強的復仇計劃,也束縛了他的生命。因為一件白襯衣讓懵懂無知的“我”從一個旁觀者變成一個參與者,11歲的“我”還不能完全理解別人口中“殺人犯”的真正含義,比起白襯衣上沾染的鮮血,“我”更害怕因為丟失白襯衣而被母親責打,也許是“我”的憨厚老實令覺強放下芥蒂,他承諾還“我”一件新的白襯衣,只要“我”嚴守秘密。當覺強臨死前從監獄里寄來那件白襯衣時,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誠實守信、真誠善良少年,然而冷漠殘酷的世界并沒有善待他的這一份純真,他是殺害老陳的兇手,同樣也是被那個黑暗無情時代扼殺的受害者,環境的殘忍不公和人們的愚昧無知都變作一顆顆“正義”的子彈,摧毀了老謝的家庭,奪走了覺紅和覺強對未來生活的憧憬與希望,甚至生命,讓他們年輕的生命里只剩下絕望。
《闖入者》對三線的記敘顯得有些“輕描淡寫”,反而更多聚焦在老鄧忙碌奔波的晚年生活上。隨著陌生電話的鈴聲和頭戴小紅帽的男孩忽然闖入老鄧的生活,在入夢與出夢的交替、歷史與現實的重疊中,老鄧陷入了極度的恐慌。王小帥采用倒敘手法帶我們走進老鄧“遺忘”的那段三線生活。原來當初為了返鄉,老鄧寫盡材料向上面檢舉和她同有競爭資格的老趙,致使老趙一家人從此只能留在那個窮困山區,老趙也中風癱瘓在床幾十年。幾十年后,老趙之孫一心復仇,不惜入室搶劫措手殺人。男孩雖然最后中斷了復仇大計,但仍沒能逃脫法律的制裁,在逃逸中墜樓而亡。男孩在老鄧通風報信的逃亡中意外墜樓身亡,所以無形之中老鄧又成為殺害男孩的間接“兇手”。因為老鄧的一己之私,老趙一家的悲劇一直延續了幾十年。老鄧一直想要忘記當年她對老趙一家所造成的傷害,然而男孩的出現又勾起了她隱埋心底的黑暗。在那個集體主義盛行的紅色年代,返鄉是老鄧唯一一份私欲,可就是這份私念讓另一家人從此掙扎在痛苦之中,我們既無法原諒老鄧傷害他人的自私行為,也對她當年所處的時代感到深深的無力,老趙一家人的悲劇是老鄧的自私造成的,也是那個冷漠無奈的歷史壞境造成的。老鄧得以返鄉,卻也一直活在無盡的恐懼壓抑之中,最后男孩墜樓的那一聲巨響將永遠成為對老鄧、對過去的無聲叩問與譴責。
王小帥塑造的這類施害者與受害者的雙重人物形象,我們不能單純的用好人壞人來加以區分,變革發展的社會環境注定了他們形象的復雜性,他們都只不過是時代歷史浪潮中的受害者與犧牲品。
二.新舊交替的沖擊與精神世界的崩潰
王小帥三線三部曲的背景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在新體制、新思想逐步建立的過程中,人們固守的舊生活與精神世界勢必會被打破,機遇與挑戰相伴而來。當外面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時,這群來自繁華大城市又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卻只能困守在這個山區,物質生活的貧乏、對自由生活的向往、自我價值得不到實現和精神信仰的崩塌接踵而來,正是這種復雜的社會環境賦予了他們復雜的雙重人物身份。
《青紅》里同事老包口中的責任包干、計件工資等新字眼沖擊了老吳一行人原有的生活模式,當初引以為傲的工廠再也不是“鐵飯碗”般的存在。物質生活的落后讓他們開始惶恐,當初拖家帶口來到三線,將自己最好的年華全都耗費在這個山溝里,到底是為了什么?然而一切都處于朦朧之中,正是這種不確定性讓一部分人回鄉的欲望急劇膨脹。《青紅》和《我11》中一句“這是我的家鄉”唱出了這群三線人的心聲。留下,只能是讓他們的子女重復他們過去幾十年的生活,出去,意味著冒險,但更是改變命運的唯一方法。被外界生活深深引誘的老吳和老鄧都迷失在了返鄉路上。
《我11》里常出現父親教“我”畫畫的場景,青紅父親也督促小弟學手風琴、監督青紅考大學,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讓子女能走出這個山溝,過上自己無法擁有的自由生活。父親對王憨說:“大人在哪里上班,不是大人能自己決定的。”“如果你以后當了畫家,就可以自由在在的生活了。”父輩們久居三線,工作生活處處受限,一言一行都要再三思慮,《我11》中人們就像一群驚弓之鳥,看似平靜的山區實則處處充滿了防備與警惕。王小帥以一個孩子的視角去講述這個故事,只提供一個少年朦朧的感受,將一切暴風雨都歸于平淡之中,然而正如王小帥所說:“在那樣一個大時代里,比這駭人聽聞得多的事情隨時都在發生,《我11》里所展現的更像是大時代風浪里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它不代表全部,甚至,跟那個時代的殘酷性相比,它顯得無足輕重。但它卻是存在的。”強奸、殺人、放火,一切瘋狂的舉動都在那個瘋狂的的時代得到了合理的解釋。那里所有人都是覺強兄妹走向毀滅的施害者,但他們也是特殊斗爭環境里的受害者。老鄧是批斗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可正是她的“積極”阻斷了他的回鄉路。
時事變遷,建設三線的滿腔熱血在這個山區里逐漸冷卻,當初去開發三線是政策號召,現在放棄三線建設也是戰略所使,只有他們成了奔波其中無人理會的棄子;本該是建設祖國的希望之地,卻成了兩派斗爭的戰場,因為害怕卷入無端的爭斗中,人們終日活在惶恐不安的算計中,所有駭人聽聞的慘事都變得稀松平常,是非黑白界限渾濁,法律道德失去約束力,毫無攻擊的獨善其身反倒是一種仁慈,所有的堅守與信仰忽然被顛覆,動蕩和變革改變的不僅是生活,更是讓人們的精神世界轟然崩塌,他們不再相信任何人,不再相信組織、相信國家,成了一個個失去信仰的空殼。正因如此,老吳才枉顧兒女意愿一心回到上海,小根才無所畏懼地犯了強奸罪,酒精的刺激只是讓他更肆無忌憚的放縱了自己惡行,覺強最終選擇如此決絕的方式去懲罰惡人。《闖入者》中老鄧多次徘徊在小區合唱組織排練的門口,她臉上總是掛著渴望又害怕的神情,然后又匆匆離去,但當她在受到小男孩的恐嚇之后,最終又重新戴上了小區巡邏的紅袖章,選擇依靠組織。從老鄧的猶疑行為中,可以看出她對組織既向往、又排斥,甚至是在逃避這個集體,即使再次戴上袖章,也無法磨滅她內心的恐懼,被仇恨毀滅的老趙之孫也成了這場精神傷害的延續。繼續滯留三線的老工人一直盼望國家對于他們這幾十年的付出能給于一個肯定的態度,不至于讓他們在臨走之際仍滿懷不甘和怨氣,然而這份希望卻十分渺茫。
三線三部曲中王小帥為我們展現的是一群普通三線工人的社會生活,雖然他們原本的生活被打破,但仍然對未知的三線建設充滿了信心與熱情。可新舊交替的朦朧變化和傾倒坍塌的精神世界在這個底層社會激起了巨大漣漪,貧窮封閉的生活、絕望壓抑的人性和扭曲的世界觀逐步擊碎了他們的夢想和希望。他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也成了最無奈的施害者。
三.傷害造成后的逃避與面對
傷害是一份記憶,是走過那段歷史的憑證,但由于它的不堪回首,三線電影中的這群人不約而同的選擇了遺忘逃避,無論施害者或受害者,他們不愿意面對,不敢去面對。
王小帥對老吳一家返回故鄉用的是“逃亡”二字。在返鄉車上,老吳再也找不到絲毫返鄉的喜悅,此刻他已經意識到就是因為他的暴躁和固執,才造成家庭的支離破碎,讓女兒的戀情慘烈收場。然而這份傷害太過沉重,沉重到讓老吳只能選擇狼狽不堪的“逃亡”來回避他犯下的錯誤,遠離這個傷心地。青紅被辱后,小根一心逃避青紅父親的責打,直到傳來青紅自殺的噩耗,他才坦白認罪。與其說他的認罪是醒悟,不如說他是因為青紅的自殺感到害怕,寄希望于用認罪伏法來尋求心理安慰,擺脫自己是傷害甚至殺害青紅這一劊子手的身份。
《我11》中的覺強在殺人后四處逃逸,覺強逃避的是警察的追捕,更是他對這個世界的憎恨與絕望。妹妹不僅被侮辱,還遭到人們閑言碎語的圍攻,惡人逍遙法外,冷酷的社會徹底顛覆了這個青年的世界觀,他放任仇恨的火苗在他心中熊熊燃燒,支使他去毀滅眼前的一切。死亡成了對覺強的一種救贖和解脫,那件白襯衫是這個少年心底唯一一絲光亮,所以他在臨死之際又將這份希望寄給王憨。監獄里王憨一家人避開覺紅父女選擇從后門離開,王憨和小伙伴去看槍決場景時忽然獨自留在原地,種種逃離的景象泄露了他們刻意掩藏的的茫然與恐懼。電影中說:“覺紅再也不會回來了。”在那個年代,可能有更多個像覺強和覺紅一樣年輕的生命體,在美好的年華逃離了這個世界。
《闖入者》中的老鄧是逃避行為最典型的代表。老鄧成功回北京后,幾十年如一日地忙于生活瑣事,希望借此忘記過去。可在她做出那件違背良心的檢舉之行后,她的生活就再也沒有了光明,她的記憶深處從來沒有讓“過去”真的就此過去,她遺忘的不是過去,而是現在和未來。即便因為小男孩緣故再次回到三線舊地面對故人,也并非是為過去的罪行懺悔,只不過是為了避免家人再次受到傷害。在那個奉行集體主義的年代,家人是老鄧最后的底線和唯一的私心,若是再次面臨這樣的兩難窘境,老鄧依然會選擇傷害他人來守住自己的底線和私欲。警察緝捕小男孩歸案時,老鄧的通風報信與她口中的那句:“這次真的不是我”,出賣了她多年來從未宣之于口的自私、懦弱與恐懼,因為害怕報復、害怕家人受傷害,她再次選擇逃避,站到了法律道德的對立面。男孩四處躲避警察的追捕,不敢面對他殺人的事實,但卻墜樓身亡,他逃避了自己的罪行,卻沒有逃脫疏而不漏的法網。
《闖入者》并未詳細描繪三線時期兩家人的恩怨,“過去”只是一個模糊的背景,核心人物老趙從未現身,反倒是他的孫子化身復仇者與老鄧有了糾纏。因為老鄧只是那個年代里的普通一員,是王小帥鏡頭下的一個典型人物形象代表,還有許多個像老鄧一樣的人曾積極地在各種運動中隨波逐流,最終成為一個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復雜結合體,因為無法面對過去的噩夢,只能催眠現在的自己,營造出一個問心無愧的假象。
飾演老鄧的呂中老師說:“我們不去批評這個國家,但是我們當然應該反思,反思過去的錯誤是為了這個國家更好。”而導演王小帥更愿意把“反思”理解為“面對”,他說:“面對似乎更坦蕩一些,面對也是更難一些,反思可以自我完成,而面對則是你把你自己交出去,是更勇敢的舉動。”午夜夢回當內心獨處時,他們可能會對自己過去展開回憶,可以獨自躲在黑暗的角落盡情地舔舐自己的傷口、反思過往,因為他人無法窺探知曉,所以這個反思舉動他們可以做的輕而易舉、肆無忌憚。但如果要他們把血淋淋的傷口和傷害他人的利器示于人前、暴露在陽光底下時,有人就開始退縮了。
面對需要勇氣,需要勇于承擔后果的堅毅與魄力。無論是電影中的他們,還是現實生活中的人們,總是習慣遇事就逃,若無其事地將傷口掩蓋,卻忽略了傷口潰爛后帶來的更大災難。面對傷害,你可以在時空上逃離,但卻擺脫不了自己的記憶,所以要勇于面對、及早面對,至少不能讓傷害繼續蔓延給我們帶來更大的傷害。
四.結語
王小帥的三部曲展現了大時代變動帶給普通工人的傷害和底層社會的動蕩不安,鏡頭下那些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的雙重人物形象,讓我們直面歷史本身的殘酷和遺留下來的弊端與傷害。動蕩時期的精神壓迫與新舊交替的浪潮給他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世界予以重大沖擊,無論是隨遇而安留居三線,或是冒險奔波返回故鄉,都無法磨滅在他們內心深處劃下的一道道傷痕,因為沒有勇氣面對傷害,只能選擇逃避那個滿目瘡痍的世界。他們是最殘忍、最無奈的施害者,更是最直接、最無辜的受害者,是時代變革里三線地區的真實寫照,是現實生活中被我們遺忘的記憶。
參考文獻
[1]王小帥.薄薄的故鄉[M].2015年1月第一版.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5年
[2]溫天一.“不合時宜”的王小帥[J].中國新聞周刊,2015年第18期
[3]王小帥,方鐳,李非.《闖入者》:無從救贖的后文革記憶[J].電影藝術,2015年第3期
[4]蔡運麟.王小帥電影中的男性形象研究[D].上海師范大學碩士.2013年
[5]吳艷.故鄉的少年——王小帥“三線生活”電影三部曲人物分析[D].南通大學.2016年
(作者介紹:劉莉,湖北大學文學院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