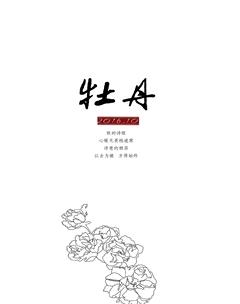媒介文化語境中的文學(xué)閱讀解析
劉月娜
20世紀(jì)末期,國內(nèi)掀起了文學(xué)閱讀浪潮,經(jīng)過十年短暫的發(fā)展后,進(jìn)入衰弱模式。國內(nèi)對媒介文化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而文學(xué)作為一種特殊性質(zhì)的媒介文化,在新媒介廣泛蔓延的過程中,文學(xué)閱讀受到波及已在所難免,并且會對文學(xué)的產(chǎn)生與研究造成一定影響。游離或者恪守文學(xué)閱讀的現(xiàn)狀,都再一次地證明了媒介文化語境中存在著媒介文化沖突的事實(shí)。
基于傳統(tǒng)電視發(fā)展起來的數(shù)字電視和可移動電視等新興的電視媒體、網(wǎng)絡(luò)媒體和手機(jī)媒體均可以被稱之為新媒介,其具有大眾化、互動性和快速性等優(yōu)勢。在新媒體文化語境中,印刷文化與視覺文化重新構(gòu)建了人類的感知結(jié)構(gòu)。新媒介的盛行給文學(xué)閱讀制造了怎樣的影響效果,以及人類的認(rèn)知結(jié)構(gòu)是如何被重塑的,都成為熱議的話題。本文將“新媒介沖擊”和“文學(xué)閱讀式微”作為探究對象,探究不同類型的媒介文化是影響人身心塑造的形式。
一、概述文學(xué)閱讀從興盛到衰弱的演變進(jìn)程
無論從哪一維度分析,1980年都被視為全面讀書熱的時期,大量作品的問世最大限度地激發(fā)了人類讀書的熱情,托爾斯泰的《復(fù)活》《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銷售量極大,《十月》《收獲》和《人民文學(xué)》的發(fā)行量驚人,分別是60萬、100萬和150萬份。1990年以后,電子媒介資源日益豐富,“電子媒介場”的文化空間得以構(gòu)建,人類逐步從相同背景的閱讀活動中退出。在21世紀(jì),國民閱讀率總體呈現(xiàn)下滑趨勢,網(wǎng)絡(luò)閱讀方式位居首位,雜志和廣播的接觸率明顯下降,“文化快餐”被大力推崇,紙質(zhì)版的文學(xué)名著不再受到重視。
二、探究新媒介對文學(xué)閱讀產(chǎn)生影響的眾多形式
與紙質(zhì)報紙、紙質(zhì)圖書、廣播、電視等傳統(tǒng)媒介相比較,新媒介語境下的文學(xué)擁有著龐大的信息量和受眾群體等眾多優(yōu)勢。在新媒體快捷性傳播功能的協(xié)助下,新媒介語境中的文學(xué)閱讀彰顯了文藝“大眾化”特色。文藝大眾化曾被視為中國文學(xué)史上的夢想,五四啟蒙運(yùn)動、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均掀起過文藝大眾化的熱潮。而實(shí)際上,文藝大眾化的程度與媒介的發(fā)展模式有著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性,尤其是在經(jīng)濟(jì)知識一體化的時代中,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代表的新媒介將更多的文學(xué)作品展示給大眾,為“文學(xué)閱讀式微”這一文學(xué)閱讀模式的啟動與應(yīng)用注入活力。具體體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一)新媒介語境中的文學(xué)閱讀愈來愈向圖像閱讀領(lǐng)域靠攏
在紙質(zhì)閱讀時代,讀者主要借助文字以獲得信息。過去的紙質(zhì)書大多由文字構(gòu)成,而少有插圖。而在新媒介時代,由于電子構(gòu)圖、排版、印刷等便利條件的應(yīng)用,使得圖文出版演變成一種潮流。現(xiàn)在的很多讀者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時間,通過智能手機(jī)、平板電腦來觀看,既節(jié)約了時間也提高了效率。并且在新媒介時代,影視劇的觀看已不再受空間因素的制約,觀眾可以隨時隨地地通過電腦與手機(jī)進(jìn)行觀看。甚至隨著無線網(wǎng)絡(luò)的覆蓋率越來越大,觀眾可以隨時聯(lián)網(wǎng)在線觀看或者是下載影視劇,這更證明了“沒有任何一個時期能夠像今天的圖像擁有著如此超凡的實(shí)力沖擊人們的生活”這一論點(diǎn)。圖像閱讀可以被視為新形勢下文學(xué)閱讀的重要方式,其直接影響著作者和讀者對文學(xué)內(nèi)涵理解的程度。
圖像閱讀方式克服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閱讀之間的復(fù)雜性,削弱了其中的嚴(yán)肅性和謹(jǐn)慎性。其與單純的文字閱讀相比,直觀性更為強(qiáng)烈。如讀者閱讀文字版的《紅樓夢》時,不同的讀者對林黛玉的形象會產(chǎn)生不同的想象,正所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在讀者觀看電視劇版的《紅樓夢》后,其在對林黛玉的形象進(jìn)行勾勒時會情不自禁的以飾演林黛玉的演員形象為基點(diǎn)。模糊性、不確定性和多義性是文字的魅力所在,而新媒介語境中圖像閱讀方式的出現(xiàn),在某種程度上消融了文學(xué)的魅力,不利于讀者閱讀能力的提升。
(二)新媒介語境中的文學(xué)閱讀表現(xiàn)出瀏覽式閱讀的特點(diǎn)
新媒介以快速傳播的優(yōu)勢為受眾提供了海量的信息資源,同時也在快節(jié)奏的時代中為受眾者帶來了無形的閱讀壓力,使得閱讀速度無法跟上信息資訊更新的速度,無法詳細(xì)閱讀每一條信息成為必然,推動了快速瀏覽方式衍生的進(jìn)程,成為“標(biāo)題黨”出現(xiàn)的內(nèi)驅(qū)動力。
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是新媒介時代中產(chǎn)出的新型文學(xué)形式,該類文學(xué)寫作難度相對較低,使具有不同層次的文學(xué)愛好者都踴躍地參與到與網(wǎng)站簽約的環(huán)節(jié)中,為成為專業(yè)網(wǎng)絡(luò)寫手不懈努力。相關(guān)統(tǒng)計資料顯示中國有高達(dá)200萬人的網(wǎng)絡(luò)寫手,受眾人數(shù)高達(dá)2.27億,每年作品產(chǎn)出數(shù)量不下7萬部。有“碼神”之稱的“唐家三少”更是堅持每天上傳8 000~10 000字,每年寫作字?jǐn)?shù)不低于280萬字,最多的一年高達(dá)400萬字。
面對規(guī)模如此龐大的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采用瀏覽式的閱讀形式,只是將讀者的注意力集中于作品人物的外形勾畫及情節(jié)發(fā)展等方面,而不能將作品創(chuàng)作的本質(zhì)挖掘出來,阻礙了文學(xué)情趣和審美鑒賞能力的提升。在新媒介語境中,構(gòu)建瀏覽式的閱讀模式,在某種意義上加速了文學(xué)作品自身向膚淺化區(qū)域靠攏的腳步,拉低了讀者的文學(xué)欣賞層次與文化情趣。因此,在新媒介語境中,對文學(xué)閱讀方式進(jìn)行多維度地反思是極為必要的,將會成為保持文學(xué)內(nèi)涵的要素之一。
(三)新媒介時代的文學(xué)閱讀具有“被迫”式閱讀的特點(diǎn)
在新媒介時代中,網(wǎng)絡(luò)以低成本、快捷性、受眾高的優(yōu)勢受到了當(dāng)事人與廣大商家的青睞,也隨之衍生為宣傳的有效利器。部分當(dāng)事人與商家以夸大的口吻、扭曲的手段對其作品進(jìn)行宣傳,以獲得更大的商機(jī)。這種閱讀方式不利于受眾做出正確、客觀性的判別,帶有“迫使”性地被帶入點(diǎn)擊量高的區(qū)域中。
在新媒介語境中,讀者在閱讀作品前,通常會搜集與本作品相關(guān)的信息。現(xiàn)階段,文學(xué)期刊和出版社通常會將圖書書訊上傳至網(wǎng)站,并附加許多出自著名評論家的評論,將這些評論在微博、微信等公共平臺展示,在讀者大量轉(zhuǎn)發(fā)的局勢中,提升社會影響力。例如余華的《第七天》在正式出版之前,就已被各大網(wǎng)站大力宣傳,責(zé)任編輯與那些看過書稿的評論者都對該作品予以好評,當(dāng)當(dāng)網(wǎng)、京東網(wǎng)亞馬遜網(wǎng)等網(wǎng)絡(luò)書店,借用預(yù)售的方式吸引采購者。在評價信息的輔助下,《第七天》獲得了大批量的讀者,首印就已達(dá)到了70萬冊。但在新媒介語境中,宣傳策略在某種意義上干擾了讀者對作品的點(diǎn)評,甚至擾亂了讀者“讀什么樣的書”這一意念,使讀者缺乏明確的對某一作品獨(dú)立審美判斷和價值定位的能力。
三、分析媒介文化語境中的沖突
新媒介可以視為是視覺文化產(chǎn)生的基礎(chǔ),而文學(xué)閱讀則被視為是印刷文化留下的歷史遺產(chǎn),文學(xué)閱讀的式微是上述兩類文化碰撞的產(chǎn)物。視覺文化語境下的上網(wǎng)、聊天、發(fā)帖、讀碟、玩游戲、看電視等方式逐漸演化成新世紀(jì)人們生活的基本模式,這種模式衍生出特質(zhì)型的思維方式、表達(dá)方式及快速瀏覽方式,使得很多新一代的年輕人對文學(xué)閱讀產(chǎn)生了敬畏心理。此外,文學(xué)閱讀的式微也推動了文學(xué)研究的式微演進(jìn)歷程,也就是說影像、視覺文化記憶最終會取代文學(xué)、印刷文化記憶。
四、結(jié)語
有評論者指出以網(wǎng)絡(luò)為代表的新媒介,是大眾娛樂性平臺,但并非思想啟蒙陣營。因此在上述圖像語境、快速瀏覽式語境以及“迫切”式閱讀語境中,讀者恪守具有一定深度的閱讀形式是提升閱讀素養(yǎng)的基礎(chǔ),而創(chuàng)作者保持嚴(yán)謹(jǐn)?shù)膭?chuàng)作風(fēng)格也是優(yōu)秀作品產(chǎn)生的根源,只有這樣文學(xué)文化才會在物欲橫流的社會中保持本色、熠熠生輝。
(常州衛(wèi)生高等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