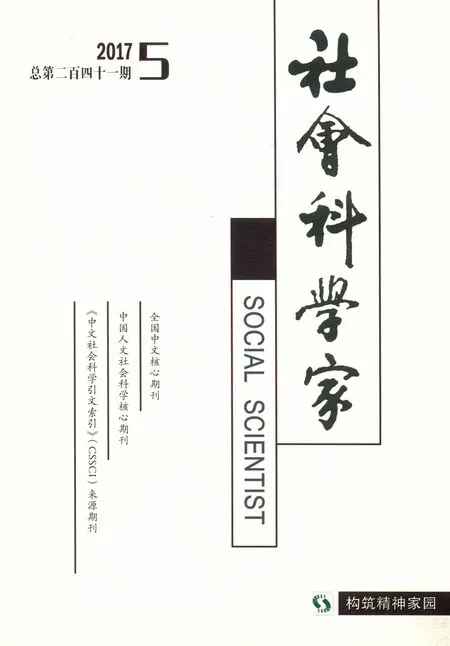關(guān)學(xué)史著作之演變:以《關(guān)學(xué)編》為中心
李敬峰
(陜西師范大學(xué) 哲學(xué)院,陜西 西安 561000)
關(guān)學(xué)史著作之演變:以《關(guān)學(xué)編》為中心
李敬峰
(陜西師范大學(xué) 哲學(xué)院,陜西 西安 561000)
朱熹開啟理學(xué)史上編纂學(xué)派道統(tǒng)著作的先例,后世學(xué)者延承此例,至明代中后期蔚然成風(fēng)。馮從吾作為明代復(fù)振關(guān)學(xué)的重要學(xué)者,首撰《關(guān)學(xué)編》以彰關(guān)學(xué)道統(tǒng),清代王心敬、李元春和賀瑞麟相繼作《關(guān)學(xué)續(xù)編》擴(kuò)展和增容關(guān)學(xué)史,至清末民初張?bào)K作集大成之作《關(guān)學(xué)宗傳》,形成以事跡、思想、著作和按語為框架的編寫體例,使關(guān)學(xué)史趨于豐富和完善。他們所勾勒的關(guān)學(xué)發(fā)展脈絡(luò)以及輯錄的文獻(xiàn)資料,對于推進(jìn)關(guān)學(xué)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價(jià)值和意義。對比分析這些不同時(shí)期的關(guān)學(xué)史著作,有助于透視和折射關(guān)學(xué)的演變和發(fā)展。
關(guān)學(xué)史;《關(guān)學(xué)編》;演變
關(guān)學(xué)是由張載始創(chuàng),并在與不同時(shí)期思想流派的交流、融通中動(dòng)態(tài)地發(fā)展的與張載學(xué)脈相承之關(guān)中理學(xué)。從宋代直至清末民初,在八百余年的時(shí)間跨度中,關(guān)學(xué)歷經(jīng)北宋的醞釀與開創(chuàng)、南宋金元的變革與低沉、明代的變異與中興、清代的延續(xù)與總結(jié),最終在清末民初牛兆濂那里終結(jié)。對于綿延八百余年的關(guān)學(xué)史,自明代關(guān)學(xué)大儒馮從吾編纂《關(guān)學(xué)編》進(jìn)行系統(tǒng)的梳理和研究,后世學(xué)者在其基礎(chǔ)補(bǔ)修不輟,形成五部關(guān)學(xué)史著作。然當(dāng)今學(xué)界尚無對其進(jìn)行系統(tǒng)性的研究,只是將其作為工具書視之,且多集中在馮從吾的《關(guān)學(xué)編》。因此,對比分析關(guān)學(xué)史上的五部著作,詳剖各自特色,比較分歧差異,揭示演變軌跡,從而透視和折射關(guān)學(xué)在不同時(shí)期的演進(jìn)路徑和時(shí)代特征。
一、開山之作:馮從吾的《關(guān)學(xué)編》
馮從吾(1557-1627),字仲好,號(hào)少墟,陜西西安人,為關(guān)學(xué)在明代復(fù)振的重要傳人,亦是明代哲學(xué)史上舉足輕重的學(xué)者,被譽(yù)為“關(guān)西夫子”。李二曲評(píng)其道:“關(guān)學(xué)一派,張子開先,涇野接武,至先生(少墟)而集其成,宗風(fēng)賴以大振。”[1]李氏認(rèn)為馮從吾是關(guān)學(xué)得集大成者,門派學(xué)風(fēng)賴其而重振。是時(shí)學(xué)界,編纂學(xué)派道統(tǒng)譜系蔚然成風(fēng)①明代中后期的學(xué)界,理學(xué)與心學(xué)之爭已成水火,且地域性學(xué)派遍地開花,在衛(wèi)護(hù)道統(tǒng)和發(fā)揚(yáng)地域?qū)W統(tǒng)信念的支持下,學(xué)者或編道統(tǒng),或續(xù)編道統(tǒng),如周汝登的《理學(xué)宗傳》、朱衡的《道南源委》、程瞳的《新安學(xué)系錄》、宋端儀的《考亭淵源錄》、劉元卿的《諸儒學(xué)案》、黃宗羲的《宋元學(xué)案》和《明儒學(xué)案》等。,馮從吾以道自擔(dān),發(fā)凡起例,探隱索跡,立志為發(fā)源于關(guān)中地區(qū)的張載關(guān)學(xué)編寫關(guān)學(xué)的道統(tǒng)譜系,他說:
我關(guān)中自古稱理學(xué)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學(xué),皋比勇撤,圣道中天……迨我皇明,益隆斯道,化理熙洽,真儒輩出……余不肖,私淑有日,頃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shí),僭為纂次,題曰“關(guān)學(xué)編”,聊以識(shí)吾關(guān)中理學(xué)之大略云。[2]
馮從吾認(rèn)為關(guān)中自古就是理學(xué)之邦,文、武、周公起于關(guān)中,學(xué)術(shù)德行不可逾越,張載接續(xù)圣學(xué),倡明此道,至明朝,此道日隆,大家輩出,然這段學(xué)術(shù)史零碎無傳,故他擇取諸儒之行事,編類成書,以使人識(shí)關(guān)中理學(xué)之源流。經(jīng)數(shù)年之努力,馮從吾終在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編成《關(guān)學(xué)編》,是編特色鮮明:
1.只收錄理學(xué)人物。馮從吾明確其收錄范圍,他說:“是編專為理學(xué)輯,故歷代名臣不敢泛入”[2],也就是此書對于名臣一概不取。同時(shí)也“不載獨(dú)行,不載文詞,不載氣節(jié),不載隱逸,而獨(dú)載理學(xué)諸先生。”[2]且將關(guān)學(xué)源頭追溯至孔門弟子:子南、子思、子從、子明四人。因四人資料不全,故只列小傳于前,然后直接從張載開始編纂。
2.以時(shí)代為序編纂。為防止古今混淆,馮從吾按照宋、金、元、明的時(shí)代順序編列學(xué)者。
3.以地選人,擯棄門戶之見。馮從吾在擇取人物上,采取地域?yàn)闃?biāo)準(zhǔn),只要是陜西籍的理學(xué)學(xué)者皆在其考慮之內(nèi),他認(rèn)為學(xué)者雖門戶不同,但“一脈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詭于吾孔氏之道則一也”[2],他收錄陽明弟子南大吉便是明證。
4.只取蓋棺定論之言。在資料擇取上,他認(rèn)為宋、元諸儒有史傳可考,沒有妄論,稍加編纂即可,而本朝儒者,則多妄論,文章之工,拙不可提,故對于本朝儒者只錄其蓋棺定論之言(只錄已逝之人),不知者寧缺毋濫。
5.在人物選擇上,不論升沉、不計(jì)尊卑,凡符合條件之學(xué)者,無不載焉。由此可見,在編纂原則上,馮從吾既有對以往學(xué)者的承繼,更有創(chuàng)新。尤其是其在資料擇取上的嚴(yán)格審慎態(tài)度,對后世影響深遠(yuǎn)。在編纂體例上,他首先置陜西籍的孔門四弟子于前,卷一錄宋代張載、張戩、呂大臨、呂大鈞、呂大忠、蘇炳、范育、侯師圣和劉愿;卷二錄金代楊天德;元代楊?yuàn)J、楊恭懿、蕭維斗、同恕、韓擇、侯均、五居仁、程瑁;卷三錄明代段堅(jiān)、張杰、周蕙、張鼎、李錦、薛敬之、王承裕;卷四錄明代呂柟、馬理、韓邦奇、南大吉、楊爵、呂潛、郭虢、王之士,共收錄33位關(guān)中理學(xué)家,另外10人附小傳。在為每個(gè)學(xué)者編纂之時(shí),以事跡、思想、著作為框架,體系顯明,內(nèi)容清晰,易為學(xué)者把握。
作為勾勒關(guān)中理學(xué)道統(tǒng)的第一部著作,馮從吾的《關(guān)學(xué)編》受到后世學(xué)者的推崇,張舜典說:“書成,人無不樂傳之。然則,是學(xué)也,是何學(xué)也?果何學(xué)也?誦是編而印諸其心”[2],以此可見《關(guān)學(xué)編》的地位與價(jià)值。也正因此,后世學(xué)者對此不斷補(bǔ)修,使其臻于完善。馮從吾的《關(guān)學(xué)編》雖有瑕疵之處,但作為一種嘗試,其價(jià)值不可小覷。
二、創(chuàng)新之作:王心敬的《關(guān)學(xué)續(xù)編》
最早對馮從吾的《關(guān)學(xué)編》進(jìn)行補(bǔ)修的是清初關(guān)中大儒李二曲的高弟王心敬。王心敬(1656-1738),字豕緝,學(xué)者稱豐川先生,陜西戶縣人,一生志在關(guān)學(xué),著述豐富。對于馮從吾的《關(guān)學(xué)編》,他論道:
關(guān)學(xué)有編,創(chuàng)自前代馮少墟先生。其編雖首冠孔門四子,實(shí)始宋之橫渠,終明之秦關(guān),皆關(guān)中產(chǎn)也。自秦關(guān)迄今且百年,代移世易,中間傳記缺然,后之征文獻(xiàn)者,將無所取證,心敬竊有懼焉,乃忘其固陋,去自少墟至今,搜羅聞見,輯而編之。既復(fù)自念,編關(guān)學(xué)者,編關(guān)中道統(tǒng)之脈絡(luò)也……編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圣于孔門四子之前,并編伯起楊子于四子之后,合諸少墟原編,以年代為編次焉。蓋愚見以為,必如是而后關(guān)學(xué)之源流初終,條貫秩然耳。[2]
在此自序中,可以看出王心敬編纂的動(dòng)機(jī)和緣由,一方面是馮從吾的《關(guān)學(xué)編》編纂的不夠全面;另一方面時(shí)過境遷,自明末儒者王秦關(guān)之后的這段關(guān)學(xué)史未曾梳理,故須重新編纂。除了遵循馮從吾以年代為編寫次序的原則外,王心敬的《關(guān)學(xué)續(xù)編》較之《關(guān)學(xué)編》有以下相異之處:
1.增列道統(tǒng)人物。王心敬在馮從吾首卷的孔門四子之前又加上秦地的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位圣人。馮從吾之所以不取此,乃在于他認(rèn)為“文、武、周公不可尚已”[2],也就是說文武周公四人地位崇高,世人不可逾越,無法尚習(xí),故不取。另一方面,則在孔門四子之后加漢代董仲舒、楊震;明朝加馮從吾、單允昌等六人,又附以周傳誦、黨還醇、白希彩、劉波、王侶諸人;清代則斷自李二曲及其弟子。可見,在篇幅上,王心敬的《關(guān)學(xué)續(xù)編》比馮從吾的《關(guān)學(xué)編》多出20余人。
2.分級(jí)排列。馮從吾的《關(guān)學(xué)編》采取的是不分尊卑高下,同等視之,而王心敬則推崇周敦頤的“士希賢,賢希圣,圣希天”[3]的人格層級(jí),故以此來判別關(guān)學(xué)道統(tǒng)人物,他將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等六人之卷標(biāo)目為“圣”;將孔門四子之卷標(biāo)目為“賢”;而將自漢以后的學(xué)者則統(tǒng)稱為“儒”。
3.地域標(biāo)準(zhǔn)寬泛。馮從吾嚴(yán)格按照以地選人的標(biāo)準(zhǔn),非關(guān)中籍不列,而王心敬則采取相當(dāng)寬泛的標(biāo)準(zhǔn),將僅是死后葬在陜西的董仲舒(河北衡水人)亦收錄進(jìn)去。
4.增加按語、創(chuàng)新體例。馮從吾的《關(guān)學(xué)編》只是按照事跡、思想和著作的體例編纂人物傳記,不加評(píng)論,而王心敬的《關(guān)學(xué)續(xù)編》則在人物篇后詳加按語,點(diǎn)評(píng)事跡、褒貶人物。
可以看出,王心敬的《關(guān)學(xué)續(xù)編》較之《關(guān)學(xué)編》有諸多突破和發(fā)展之處,在經(jīng)過明代中后期編纂道統(tǒng)著作之風(fēng)盛行之后,王心敬可以站在更高的角度吸取和借鑒以往學(xué)者的經(jīng)驗(yàn),在編寫體例上進(jìn)行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
三、增益之作:李元春的《關(guān)學(xué)續(xù)編》
李元春(1769-1854),陜西朝邑(今屬渭南市)人,字仲仁,又字又育,號(hào)時(shí)齋。著述豐富,主要有《四書簡題課解》、《諸經(jīng)緒說》、《經(jīng)傳摭余》、《春秋三傳注疏說》、《諸史閑論》、《諸子雜斷》、《諸集揀批》、《群書摘旨》、《讀書搜纂》、《圖書揀要》、《拾雅》、《數(shù)記典故》、《左氏兵法》、《綱目大戰(zhàn)錄》等數(shù)百卷。李元春首先高度評(píng)價(jià)馮從吾的《關(guān)學(xué)編》,他說:“《關(guān)學(xué)編》,馮少墟先生所輯,以章吾關(guān)學(xué),即以振吾關(guān)學(xué)者也”[2],李元春認(rèn)為馮從吾作《關(guān)學(xué)編》意在彰顯關(guān)學(xué)道統(tǒng)和復(fù)振關(guān)學(xué)。李元春自述其續(xù)編緣由:
此編人皆知之,而后學(xué)或未能盡見。予不敏,未能自振,顧恒欲人之胥振于正學(xué),往與同志訂《文廟備考》一書,邑中雷氏刻之,思此編亦不可不家置一冊,因與及門共訂補(bǔ)入七人,續(xù)入十二人。[2]
吾邑趙廷璧先生嘗刻之(《關(guān)學(xué)編》),而學(xué)師中衛(wèi)劉先生得炯即以少墟補(bǔ)入,又入吾邑王仲復(fù)先生,意皆勤矣。[2]
李元春認(rèn)為馮從吾此編人盡皆知,恐后學(xué)不能見,也為振興正學(xué)之故,與門人共修此編,訂補(bǔ)七人,續(xù)入十二人。李元春始終未提及王心敬的《關(guān)學(xué)續(xù)編》,這可能與其未見到此書有關(guān),如果見到,必定不會(huì)只說劉得炯將馮從吾補(bǔ)入,而這早在清初王心敬的《關(guān)學(xué)續(xù)編》中已經(jīng)收錄,亦不會(huì)在周勉齋已經(jīng)補(bǔ)入王心敬傳之后,再另寫王心敬傳,造成重復(fù)。可見,李元春的《關(guān)學(xué)續(xù)編》是在馮從吾《關(guān)學(xué)編》的基礎(chǔ)上直接修訂,而非在王心敬的《關(guān)學(xué)續(xù)編》上改訂。李元春的編纂原則較之馮從吾、王心敬更為寬泛,他說到:
圣門弟子材不一科,品不一等,圣人有予有斥,有未及論列,而既以圣人為師,承其傳者,皆不可謂非圣人之學(xué)也。此編有待補(bǔ)入,少墟固自言之矣。[2]
李元春認(rèn)為圣門弟子材質(zhì)不一,品節(jié)不同,圣人有贊有貶,更有未列之弟子,既然這些弟子都以圣人為師,傳承圣人,就不能說不是圣人之學(xué)。何況此編有待補(bǔ)入,是馮從吾本人早就說過的。李元春在此為自己補(bǔ)修此書之緣由追溯到創(chuàng)作者本人,之所以如此,乃是有人以為他修此書“將有僭妄之議”[2],故不得不辯。以此寬泛之則,他將學(xué)人遺忘的張載門人游師雄補(bǔ)入其內(nèi),并詳述道:
游師雄,受業(yè)橫渠,載之《宋史》,學(xué)術(shù)幾為事功掩,然事功孰不自學(xué)術(shù)來,此疑少墟之所遺也。他若在少墟前者,或未及蓋棺,或與少墟同事同學(xué)及諸門人,少墟所不能入。[2]
李元春認(rèn)為以往學(xué)者因游師雄事功杰出之故,不將其列入關(guān)學(xué)道統(tǒng)之內(nèi),殊不知事功皆由學(xué)術(shù)而來,因此他懷疑是馮少吾遺之。如果他在馮從吾前面,或未到蓋棺之時(shí),或與其同輩,馮從吾皆不會(huì)列入道統(tǒng),這里他再次重申馮從吾的編纂原則,也可反襯出李元春裁斷標(biāo)準(zhǔn)之寬泛,在這種標(biāo)準(zhǔn)之下,李元春又增加明代劉璽、劉儒、劉子誠、溫予知、溫日知、張國祥、趙應(yīng)震、盛以弘、楊復(fù)亨等人,清代則增王茂麟、王建常、王宏度、譚建蘊(yùn)、王宏學(xué)、王心敬、馬域士、孫景烈和王巡泰等人。
除在裁斷標(biāo)準(zhǔn)上更趨于寬泛之外,李元春《關(guān)學(xué)續(xù)編》較之馮從吾的《關(guān)學(xué)編》除了在人物上有所增加之外,其他并無有相異、突破之處,較之王心敬的《關(guān)學(xué)續(xù)編》,李元春的《關(guān)學(xué)續(xù)編》沒有加按語,所加人物亦沒有王心敬豐富。當(dāng)然,我們不能因此判斷孰優(yōu)孰劣,他們只是從不同的角度對《關(guān)學(xué)編》的增補(bǔ)。
四、紹述之作:賀瑞麟《關(guān)學(xué)續(xù)編》
賀瑞麟(1824-1893)是李元春高弟,字角生,號(hào)復(fù)齋、中阿山人、清末著名理學(xué)家、教育家、書法家。與山西芮城薛于瑛(仁齋)、朝邑楊樹椿(損齋)并稱“關(guān)中三學(xué)正”。賀瑞麟論道:
關(guān)學(xué)之編自馮少墟先生始,厥后王豐川有續(xù),李桐閣有續(xù)。豐川、桐閣皆以關(guān)學(xué)自任,其編關(guān)學(xué)也,與少墟同一振興關(guān)學(xué)之心,其人為不愧少墟之人,其書亦為不愧少墟之書。麟雖有志關(guān)學(xué),而實(shí)于少墟、豐川、桐閣諸先生無能為役。惟嘗于學(xué)關(guān)學(xué)之人如劉柏容以下七人,久愛之慕之,口誦而手錄之,置諸案頭,私自取法,以為擇善思齊之資而已,非敢云續(xù)關(guān)學(xué)也。然七人者,固關(guān)學(xué)之續(xù)也。[2]
賀瑞麟高度評(píng)價(jià)馮從吾的《關(guān)學(xué)編》以及王心敬和李元春對其的續(xù)編之功。他自述其雖有志關(guān)學(xué),卻遺憾無法效勞于馮從吾、王心敬和李元春左右,故于1893年編寫《關(guān)學(xué)續(xù)編》,將其愛慕之劉柏容、王遜功、李元春、楊樹椿、史復(fù)齋、鄭冶亭和張?zhí)}谷七人補(bǔ)入《關(guān)學(xué)編》。賀瑞麟的《關(guān)學(xué)續(xù)編》是在其師李元春的基礎(chǔ)上增補(bǔ)的,其最大特點(diǎn)就是以“宗程朱之學(xué)”為標(biāo)準(zhǔn)擇取,他與其師皆朱子學(xué)羽翼,李元春明確說:“予之學(xué),朱子之學(xué)也”[4],賀瑞麟亦說:“竊謂千古學(xué)術(shù),孔孟程朱已立定鐵案,吾輩只隨他腳下盤旋,方不錯(cuò)走了路。”[5]正是師徒二人對朱子學(xué)的恪守,賀瑞麟所擇七人皆為宗朱子學(xué)者。由此可見,關(guān)學(xué)發(fā)展至賀瑞麟,已背離馮從吾不擇門戶之宗旨,呈現(xiàn)出固守門戶之見的趨勢。
需要指出的是,賀瑞麟作《關(guān)學(xué)續(xù)編》的緣由除了本身志向關(guān)學(xué)外,另一外因乃是受柏景偉所托,柏景偉(1831-1889),字子俊,學(xué)名灃西先生,陜西西安人。柏景偉有意續(xù)補(bǔ)《關(guān)學(xué)編》,但因病困擾,故請賀瑞麟接手此任。柏景偉雖沒有為之續(xù),但卻積極刊印,并對三人之書評(píng)價(jià)道:
豐川(王心敬)編,遠(yuǎn)及羲、文、周公,下及關(guān)西夫而下,非恭定(馮從吾)所編例,去之……蓋統(tǒng)程、朱、陸、王而一之,集關(guān)學(xué)之大成者,則馮恭定公也。于是,二曲、豐川超卓特立,而說近陸王;桐閣博大剛毅,而確守程朱。今刊恭定所編關(guān)學(xué),即繼以二家之續(xù),蓋皆導(dǎo)源于恭定,而不能出其范圍者也。因刊恭定所編關(guān)學(xué),而并及豐川、桐閣、復(fù)齋之續(xù),凡以恭定之學(xué)為吾鄉(xiāng)人期也。[2]
柏景偉首先認(rèn)為王心敬的《關(guān)學(xué)續(xù)編》違背馮從吾的編寫體例,故在刊印中將其增加的道統(tǒng)人物一概刪除。他認(rèn)為馮從吾是綜合程朱、陸王的,李二曲、王心敬之學(xué)則近陸王,李元春則恪守程朱之學(xué),且認(rèn)為幾家之說皆沒有突破馮從吾所定之規(guī)模。可見,柏景偉實(shí)際是以馮從吾的學(xué)術(shù)體系為裁斷標(biāo)準(zhǔn),但這種可以維護(hù)則容易忽視其他學(xué)者的貢獻(xiàn)。從學(xué)術(shù)史的演變來看,王心敬、李元春的《關(guān)學(xué)續(xù)編》對馮從吾是有推進(jìn)和突破之處的,并非不出馮從吾之規(guī)模。
五、集大成之作:張?bào)K的《關(guān)學(xué)宗傳》
張?bào)K,字先識(shí),雖為四川成都人,但常年寓居關(guān)中,推崇關(guān)學(xué),廣搜材料,查閱一千三百余種書,于“民國”十年(1921)撰成皇皇巨著《關(guān)學(xué)宗傳》。他敘述作書動(dòng)機(jī)道:
長安馮少墟先生舊輯關(guān)學(xué)編四卷,朝邑李氏、三原賀氏各有增益,蔚然可觀。第諸儒學(xué)說都付闕如,后學(xué)問津茫無把握,關(guān)學(xué)之奧義未窺,鄒魯之淵源何接?又卷帙寥寥,搜羅未廣,小子懼焉,爰仿周海門《圣學(xué)宗傳》、孫夏峯《理學(xué)宗傳》之例,輯橫渠以來至于澧西、古愚,計(jì)如干人。本傳為經(jīng),學(xué)說為緯,立傳則以本事為憑,錄語則以全書為據(jù),俾關(guān)中學(xué)者于茲取裁,亦在關(guān)言關(guān)之意云爾。若濂、洛、新安,則遺書具在,源流別有可尋,不在本編范圍之內(nèi)也。茫茫絕緖,繼續(xù)何人?吾寓關(guān)中,留心關(guān)學(xué)。以余所見,三水蕭筱梅,堅(jiān)苦卓絕似二曲,臨潼郭希仁,明體達(dá)用類古愚。而所聞則有高陵白悟齋,藍(lán)田牛夢周,恪守西麓之傳,皆關(guān)學(xué)之晨星碩果然。竊不知此外尚有人焉否也?陽明子曰:“關(guān)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沈毅之質(zhì),明達(dá)英偉之器,吾見亦多,安知不更有牛、白、郭、蕭之儔耶?關(guān)學(xué)之興替,大道之存亡,將于是編卜之矣。[6]
在這篇短文中,張?bào)K認(rèn)為馮少墟作《關(guān)學(xué)編》,李元春、賀瑞麟各有增益,但后世學(xué)者多有缺損,且搜羅不備,后學(xué)無從下手,不去把握關(guān)學(xué)宗旨,如何接續(xù)關(guān)學(xué)道統(tǒng),故張?bào)K效仿周海門的《圣學(xué)宗傳》和孫夏峰的《理學(xué)宗傳》的編寫體例,輯錄宋張載至清末劉古愚若干人,述其行事之概,兼附著述、語錄,以成此書。張?bào)K編纂《關(guān)學(xué)宗傳》較之以往學(xué)者著作的特點(diǎn)如下:
1.以理學(xué)為主流,但不排除名臣如石渠、吏行如湭西、文學(xué)如太青等人,因?yàn)樵趶報(bào)K看來,此數(shù)人皆學(xué)術(shù)深純粹然,儒者當(dāng)與圣門四科之列,故收錄進(jìn)去。張?bào)K這一原則顯然違背馮從吾的宗旨,馮從吾特意排除名臣之流,而張?bào)K則一概收入。
2.以地域?yàn)橄蕖報(bào)K說:“俾關(guān)中學(xué)者于茲取裁,亦在關(guān)言關(guān)之意云爾。”[6]張?bào)K嚴(yán)格按照陜西籍收錄,以地編人,外地學(xué)者即使宣講關(guān)學(xué),如橫渠再傳,呂大臨弟子周行己、沈彬老,二人皆浙江人,因非關(guān)中人士,亦不收錄。張?bào)K在此則與馮從吾相同。
3.在編寫次序上,首先撰寫人物傳記,如果人物有正史,則據(jù)史直書,無關(guān)學(xué)術(shù)者則不取;若正史無傳或傳而不詳,則博采諸書,擇優(yōu)增補(bǔ);其次則附人物學(xué)說,若人物有完整著述,則全書錄入,如果本人著述不可考,或散見于其他各家,則采集錄入,如果無法編采,則寧缺毋濫,它日搜集,再為增補(bǔ)。由此可見,張?bào)K態(tài)度之審慎。
4.不立宗派門戶。張?bào)K說:“是編不立宗派,節(jié)取眾長,凡有關(guān)于身心性命、發(fā)明圣學(xué)者,得搜采之。”[6]張?bào)K在人物擇取上,不立門戶之見,只要是發(fā)明心性之學(xué)的,皆搜集錄入。從其收錄的人物可以看出,他既收錄學(xué)宗朱子的呂柟、馮少吾、亦收錄傾向陽明學(xué)的南大吉兄弟,更不棄薈萃理學(xué)、心學(xué)的李二曲。
5.按語先加后刪,力求客觀。張?bào)K在編寫《關(guān)學(xué)宗傳》時(shí),認(rèn)為諸儒學(xué)說,義理精微,但奧妙玄通,令人費(fèi)解,故在《關(guān)學(xué)宗傳》初稿中,他仿效全祖望的《宋元學(xué)案》之例,加上按語以便學(xué)者理解。后又感覺此舉有強(qiáng)人認(rèn)同之意,故一概刪去,以使學(xué)者自己用心默認(rèn)體會(huì)。
6.刪除張載之前所有人物,新增二人。張?bào)K采納全祖望的觀點(diǎn),認(rèn)為關(guān)學(xué)在張載之前,尚有申顏、侯可二人,故在編寫《關(guān)學(xué)宗傳》時(shí),為審重之見,將其二人附在卷末,以求正于后人,可見審慎之態(tài)度。
7.重新編寫人物傳記。張?bào)K的《關(guān)學(xué)宗傳》并非是在前任基礎(chǔ)上的續(xù)補(bǔ),而是另起爐灶,搜集、查閱一千三百余種書,重新編寫人物傳記。這亦是張?bào)K之作較之以往學(xué)者的最大特色。張?bào)K的《關(guān)學(xué)宗傳》共收錄202人,在篇幅、內(nèi)容上皆超過前任之作,為歷代撰寫關(guān)學(xué)史之最。
張?bào)K的《關(guān)學(xué)宗傳》在很大程度上承繼馮從吾的謹(jǐn)慎、嚴(yán)格、細(xì)致的治學(xué)態(tài)度,汲取王心敬、李元春和賀瑞麟的編纂優(yōu)點(diǎn),終成為關(guān)學(xué)史上的集大成之作。
六、小結(jié)
自馮從吾開創(chuàng)為關(guān)學(xué)編纂道統(tǒng)史的先例以來,王心敬、李元春、賀瑞麟和張?bào)K相繼續(xù)編,使關(guān)學(xué)道統(tǒng)臻于豐富和完善。這些著作呈現(xiàn)出一些共同特征,首先,基本按照以地選人的標(biāo)準(zhǔn)擇取人物,雖然在“地”的界定上,有所不同,但主流仍然是按照籍貫進(jìn)行編選。其次,在編纂體例上,基本是以年代為序,按照事跡、思想、著作的框架進(jìn)行編纂。又次,五部著作的總體趨勢是不立門戶之見,但凡從事理學(xué)(廣義)研究,有志于身心性命之學(xué)的,皆在收錄范圍之內(nèi)。最后,在資料擇取上,皆體現(xiàn)出關(guān)學(xué)務(wù)實(shí)求真、兼取并包之學(xué)風(fēng),他們擇取史料一方面取之正史,以求史料正確無誤,另一方面擴(kuò)大范圍,廣泛搜集,對比分析,力求材料可靠。總之,關(guān)學(xué)學(xué)者前仆后繼的編纂關(guān)學(xué)道統(tǒng)史,使關(guān)學(xué)史日益豐富和完善,它反映和揭示理學(xué)在關(guān)中地區(qū)的演變和發(fā)展,它所呈現(xiàn)的關(guān)學(xué)發(fā)展脈絡(luò)以及文獻(xiàn)資料,對于把握關(guān)學(xué)源流,推進(jìn)關(guān)學(xué)的深入研究是具有重要的價(jià)值和意義。
[1]李顒.二曲集(卷十七)答董郡伯[M].北京:中華書局,1996.
[2]馮從吾.關(guān)學(xué)編(附續(xù)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7.
[3]周敦頤.周敦頤集[M].北京:中華書局,1990.
[4]李元春.四書心解序.(桐閣文鈔)[M].朝邑同義文會(huì)刻本,1884.
[5]賀瑞麟.答蔣少園[A].清麓文集(卷七)[C].劉轉(zhuǎn)經(jīng)堂,1899.
[6]張?bào)K.關(guān)學(xué)宗傳[M].西安:陜西教育出版社,1921.
[責(zé)任編校:趙立慶]
B2
A
1002-3240(2017)05-0032-05
2016-02-03
中國博士后第就九批特別資助項(xiàng)目(2016T90888),中國博士后科學(xué)基金第57批面上資助一等資助項(xiàng)目(2015M570812),陜西省博士后資助項(xiàng)目(2016BSHEDZZ63),中央高校專項(xiàng)資金資助項(xiàng)目(15SZYB05),陜西省社科規(guī)劃項(xiàng)目(2015C005)
李敬峰(1986-),河南洛陽人,陜西師范大學(xué)哲學(xué)系中國哲學(xué)教研室副教授,哲學(xué)流動(dòng)站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