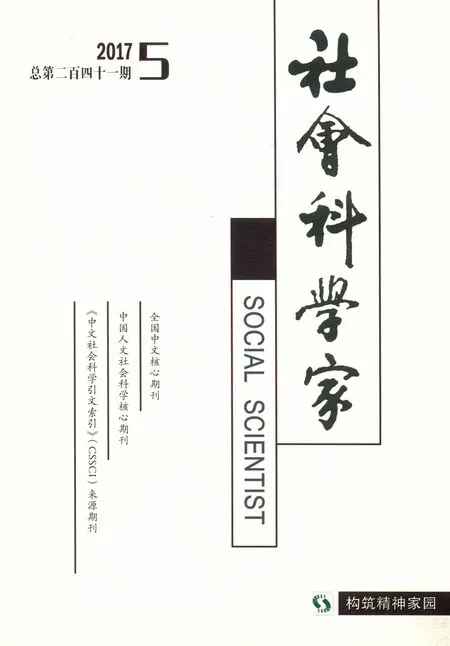春秋時期的本末認知與話語
李曉東,陳廷湘
(四川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春秋時期的本末認知與話語
李曉東,陳廷湘
(四川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4)
論者假定華夏族的“本末”認知觀念源于自然植物界的客觀存在物“樹木”;“本末”認知作為一種人與植物的類比認識,早在《詩經》中就已出現,即周時的“本枝”論;春秋時期“本末”成為知識階層和精英階層的公共話語,這些話語得到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模仿、回應及傳承;可以從“本末”的語義,“本末”話語的表述方式,“本末”話語的作用三個層面去理解春秋時期的本末認知;“本末”認知塑造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
春秋;本末;認知;話語;表達
關于“本末”,現代漢語中有兩種常見或習慣性的表達方式:一種謂某人、某人的行為是“舍本逐末”、“本末倒置”;另一種謂某種措施、某種方法是“治標不治本”,而應“標本兼治”。這兩種方式都代表說話者的某種看法或判斷,并力求使之具有說服力。眾所周知,這些成語不是在今天才開始使用的,而是自古代漢語傳承和沿襲下來的。如果要考察這類成語、說法及其背后的思維模式,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秦時代。
一、“本末”認知述源
1.由“木”而“本”的邏輯認知
作為宇宙、自然的產物,人類為了生存及延續,是離不開植物界的。樹木即是與人類生存息息相關而不可或缺的植物品類,尤其在農業尚難稱發達的古代時期,更是如此。樹木為古人的衣、食、住、行、娛等各個方面都提供了基礎性的支撐,同樣也為古人的群體組織和群體行為提供物質保障,例如農業、手工業的木制工具,戰爭行為的兵器等。在考古學或線性史觀中,常見“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的發展分期,但似乎對“木器”和“木器時代”的關注就少得多。
對樹木的廣泛應用,同樣也會映射到人類的認知當中。就華夏族而言,遠在商周時期,知識階層就已認識到樹木和人類社會生活密切相關,如箕子的“五行”說,將“木”列為“五行”中的第三位: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木曰曲直……曲直作酸……①《尚書·周書·洪范》,屈萬里著:《尚書今注今譯》,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版,第100頁。
合理的推測是,華夏族“本末”的認知觀念源于自然植物界的客觀存在物——“樹木”。這種認知是通過將樹木解構細分為樹根、樹干、樹梢、樹枝和樹葉等組成部分并且應用于日常生活中而實現的,然后繼續向社會生活領域延伸,進入精神和觀念的世界。值得一提的是“,本末”的辨析中還包含或體現論者所認同或看重的價值觀。
2“.本末”認知的先聲:《詩經》中的“本枝”論
“本末”認知很早就在先秦的文獻中表現出來,這就是《詩經》中的“本枝”論:“文王孫子,本支百世。”①《詩·大雅·文王》,王秀梅譯注:《詩經》,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577頁。
作為樹木的一部分,“本支”和周王朝的宗族、國家認知聯系在一起,體現了先秦社會中的一種“人與植物的類比認識”②(日)高木智見著,何曉毅譯:《先秦社會與思想——試論中國文化的核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0~64頁。。這里“本”指代周王室的嫡系親族,“支”同“枝”,指代周王室的旁系親族,“本枝”一起構成周王朝的統治支柱。為使周王室能夠長久存續,就要注意避免重蹈商朝滅亡的覆轍:“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③《詩經》,第672頁。
王室家族是“本枝”在國家層面上的意義,“本枝”后來也可以指宗法社會中個人及其所依附的家族背景。例如,孔子即認為人“身”是屬于“親”(宗族)的分“枝”,是應當禮“敬”的。如果不“敬”,就意味著對宗族的傷害,即是傷害到“本”了,而傷害“本”的直接后果,就是作為“身”的“枝”轉而無所依托,亦隨之而亡。④《禮記·哀公問》,《十三經注疏》,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847-848頁。
“本支百世”簡稱則為“世本”,著錄黃帝至春秋各統治者家族世系的古書亦名《世本》。周時的“本枝”及“世本”認知,作為象征上層精英統治者的觀念,也被后世所沿用及傳承。在春秋戰國時代,只要成為國家的最高主宰者“國君”,就可以稱為“本”;秦、漢以后,這種觀念同樣也被史籍所采用,如《史記》中記載帝王一系的體例為“本紀”,而次一級的公侯則為“世家”。
二、春秋時期的“本末”公共話語:各本其所本的話語現象
春秋時期的知識階層及精英階層普遍使用“本末”話語,這一時期的主要文獻《左傳》、《國語》之中,關于“本末”的言說即比比皆是。可以說,“談本論末”是春秋時代的一種論說風氣,也是當時思想世界的一個特點。這種風氣也直接影響了戰國時代的“本末”表達。
“本”、“末”本身的語義簡單明了,它總是和論者的某種觀點或看法密不可分,核心的功能是論者用以組織和闡釋論點或論題的一種形式邏輯。對當時的論者來說,他們通過“本末”這種表述方式去凸顯所堅持的觀念,旨在強調其重要性。下面即以《左傳》、《國語》、《老子》以及早期儒家為中心,來考察這一時代的“本末”話語。
(一)《左傳》、《國語》中的本末話語及其回響
《左傳》、《國語》中,與“本末”結合到一起的論題或主旨主要是“國之本末”、“周禮為本”、“治亂之本”、“忠信為本”、“義利之本”、“孝本與務本”、“不背本”。這些相同主題的“本末”話語在戰國時代繼續受到知識階層及精英階層的模仿及回應,從而使這種思維方式和敘事方式得以傳承和延續。
1.國之本末
《左傳》的“國之本末”論,作為一種國家觀念,沿襲自周朝的“本枝”論。對春秋時代的各個諸侯國而言,“本”、“末”自有其專屬含義:前者指各諸侯國的國君,后者則指國君的同姓親族(“枝”)或者異姓地方實力大族,雙方的關系呈現出復雜的狀態。
桓公二年載晉國公族的勢力已凌駕于公室之上,其關鍵在于晉國公族未能把握“本大末小”的原則:“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⑤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93-95頁。在桓公十六年記述衛國國君繼承權政爭之后,著者從“本”、“枝”、“末”三者的關系出發,又總結道: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后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⑥《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168-169頁。
在《左傳》的著者看來,國家的權力格局固然要注意“本大末小”,但更重要的在于“本末”或“本枝”內部之間的合作,所謂“本有保則必固”⑦左丘明撰,韋昭注:《國語·周語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0頁。。文公七年的記載,以“枝葉”對“本根”的“庇蔭”喻義再次強調公族對公室本具有的輔助作用:宋昭公想去“群公子”,樂豫建言“不可”,因為他認為“公族”是“公室之枝葉”,如果除去,公室就缺少了強大的政治支持力量,“本根無所庇蔭矣”。
《左傳》極大關注國之“本末”問題,目的就是提供歷史經驗,借鑒歷史教訓,傳播歷史知識和歷史智慧,期待各諸侯國防止“本小末大”及“末大折本”,穩定政局。這一立場可從昭公十一年的一段記載清楚地顯示出來:(楚)王曰:“國有大城,何如?”申無宇對曰:“……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然而春秋諸侯國的政治發展趨勢卻是“本末”的對抗漸漸超過“本枝”的聯合。到了戰國晚期,政治學者韓非子則徹底拋棄了“本枝”輔助論,而提倡“披枝”論,認為國君要將家族血緣關系與政治權力相分離,強化國君的中央集權:“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公子既眾,宗室憂唫。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①《韓非子·揚權》,張覺撰:《韓非子校疏析論》,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版,第740頁。
2.周禮為本
春秋時期東周雖為各諸侯國名義上的共主,但列國間仍具有“周禮為本”的共識。閔公元年仲孫湫就是否兼并魯國向齊桓公提出建議,顯示了這種意識形態強大的慣性力量:“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后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②《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257頁。
“周禮”既是規范共主與各諸侯國的親疏與等級制度,又代表中原文化上的認同,也是區分夷、夏的標準。盡管周禮仍然在春秋列國間維持其基本的文化習俗與慣例的認同地位,但是周禮繁復的“儀式感”已逐漸衰落,而其在治理國政、凝聚民心上的實際效用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這就是魯昭公時晉國的女叔齊所強調的“禮儀本末”的實用觀念。從魯閔公迄魯昭公,已歷經五代,對“禮”的認知由“周禮為本”變遷到了“禮之本末”,這也是諸侯國追求民多地廣的國家實力使然。對“禮”“尚質”而不再“尚文”,這一點在早期儒家那里也得到了共鳴。他們探討了“禮”的本質屬性和本質要求,同樣也不看重“禮”的形式:林放向孔子請教“禮之本”,孔子回答說“禮,與其奢也,寧儉”;③《論語·八佾》,(梁)皇侃撰:《論語義疏》,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51-52頁。而“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④《禮記·樂記》,第679-680頁。
至春秋晚期,長江流域新的強權吳國崛起,黃河流域“周禮為本”的意識形態遭到了“棄天背本”的空前挑戰。哀公七年載吳國致力于擴張,爭奪中原霸權,在強索宋國后,再度向魯國要求“百牢”。魯國的大夫子服景伯認為吳國的舉動多行不義“將亡”,因為“棄周禮”是“棄天背本”的行為,嚴重損害了“禮”的正義性。春秋時的儒家也秉持同樣的認知,如孔子認為“禮”的正義性是“本于天”,即源于天的:“是故夫禮必本于天”⑤《禮記·禮運》,第404、429頁。。孔子不止一次,反復申說“禮從天出”(孔穎達正義),把“禮”看作是天賦的。“天”或“太一”是“禮”的本原或根本,因而就具有了某種不容置疑的正當性。這是儒家對“禮”的起源及合法性的最高或終極的解釋。
戰國時的荀子同樣重“禮”。他認為“禮”有“天地、先祖、君師”三個本原,其中“天地”是生命的本原,“先祖”是人類的本原,“君師”是治理國家和人民的本原。“天地先祖君師”的“起始”意義是荀子所珍視的,他推崇“禮”的意義在于要憑借它來“別貴始”,于是“禮本”論便發展為“貴始”的“德本”論:“貴始,得(德)之本也”。⑥《荀子·禮論》,(清)王先謙撰:《荀子集解》,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340頁。那么“禮”還有哪些政治上的功能呢?荀子認為“禮”是“強國”的根本。基于此,相對地,他認為戰爭是不重要的“末事”。⑦《荀子·議兵》,第265、275頁。將戰爭看作“末事”的認知,荀子很可能是受到春秋晚期越國大夫范蠡的啟發:“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兇器也;爭者,事之末也。”⑧《國語·越語下》,第423頁。就戰爭和軍事本身而言,戰國的兵家也探討了“兵之本”,其觀點像是范蠡和荀子的反論:“夫兵有本干,必義,必智,必勇。”⑨《呂氏春秋·決勝》,張雙棣、張萬彬、殷國光、陳濤注譯:《呂氏春秋譯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頁。
3.治亂之本
春秋時期諸侯政權的更迭、國家的興亡,引起了《左傳》、《國語》的強烈關注,并試圖在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情境下探究其原因,這就是“亂本”、“禍本”和“亡本”論。
《左傳》、《國語》從四個層面來關注春秋時代的治亂之本:
(1)國君或主政者的執政得失
桓公十八年:初,子儀(王子克)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并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在政治上,妻妾、嫡庶、正副、都城應各安本位,各守本分,否則內亂必生。其中的“匹嫡”即指違反周以來的嫡長子繼承制度,普遍為當時的精英階層所反對: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少長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奸之本也……”①張純一撰:《晏子春秋校注》,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8-29頁。
《國語·晉語一》史蘇從國君夫人干政的角度來探討“亂之本”: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2)君臣之間嚴格的等級制度攸關治亂
《國語·齊語》中管仲認為“為君不君,為臣不臣”,是“亂之本也。”②《國語·齊語》,第161頁。盡管由于政治實力的對比,周天子與諸侯盟主之間的等級制度已有所動搖,但維護嚴格的君臣等級制仍是列國間的共識。如果君臣等級關系破裂,必將引起嚴重的政治內亂。成公十六年晉與楚、鄭鄢陵之戰后,卻至居功自傲,單襄公認為卻至的行為會招來政敵或國君的怨恨,而“怨之所聚,亂之本也。”③《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894-895頁。“卻氏家族,有三位卿、五位大夫”,號為“八卻”,“族大”逼君的權勢,使晉厲公深感威脅,第二年“三卻”等即被晉厲公所殺。
戰國時《韓非子》引述了《左傳》襄公七年的一段史事,作為君臣之義的負面典型: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管子·明法解》也說:“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
(3)晉、楚競爭諸侯盟主的結果
晉與楚、鄭鄢陵之戰前,晉卿范文子的政治、軍事意志都不強烈,本不愿意進行這場戰爭,這顯示了晉國霸權的逐漸衰落:“若以吾意,諸侯皆叛,則晉可為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④《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952-953頁。范文子認為晉、楚長期對立,反復爭奪中、小國的附屬是戰亂的一大主因。
(4)民間社會輿論與禍亂
《左傳》襄公十七年的一段敘述,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當時的統治階層對民間社會輿論的看法。宋國的皇國父為大宰,為宋平公筑臺,因為征用民役,妨礙了農收。子罕為民請命,向宋平公建議等“農功”完畢之后再去筑臺,但平公不許,于是筑者輿論峰起,責皇國父而譽子罕。但這種議論引起了子罕的擔憂,他親自執罰鞭打筑臺者,于是議論就停止了。有人問子罕這么做的原因,子罕認為小小的宋國,如果“有詛有祝”,實乃“禍之本也”。⑤《管子·明法解》,顏昌峣著:《管子校釋》,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518頁。聯系到子產不毀鄉校,這時的民間社會輿論處于“他者”的地位,都在精英階層的話語支配與定義之下。
戰國晚期的韓非子十分注重探究春秋時期的治亂經驗,他從文官制度的角度提出見解:“賞繁,亂之本也”;“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奸臣進矣。此亡之本也。”⑥《韓非子·心度》,第1196頁。等等。《莊子》書中從歷史思辨的角度,針對儒家學說理想目標與現實人性相違背的缺陷,提出另一種深具洞察力的“大亂之本”的觀點:“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⑦《韓非子·有度》,第72頁。
反過來說,有“亂之本”則亦應有“治之本”。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如《商君書·錯法》說“臣聞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賞行而兵強。此三者,治之本也。”⑧《莊子·庚桑楚》,劉文典撰:《莊子補正》下,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628頁。《管子·立政》認為“治國有三本……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勞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⑨蔣禮鴻撰:《商君書錐指》,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63頁。等等。
4.忠信為本
“忠信為本”既是對國君人格上的要求,也是對國君所代表的國家的要求,認為各諸侯國在交往時,需要講求“忠信”這種道義,而不是一味迷信武力。
《國語·晉語二》載宮之奇認為“忠信”是國家建立和鞏固的條件之一,如果違背,則“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這種理念又為叔向所繼承,認為諸侯國的盟主,無論晉國還是楚國,都應遵循這樣的準則:“忠自中,而信自身,其為德也深矣,其為本也固矣”。這種“固本”的認知為墨子所吸收,具體所指則為農業:“固本而用財,則財足。”①《國語·晉語二》,第308頁。
然而在春秋各國致力于兼并的政治現實下,“忠信為本”的道德約束畢竟難以發揮太大的作用;隨著戰爭兼并的加劇,道德約束與國家行為就越來越相分離。
5.義利之本
中國傳統上“義利之辨”的話語源于春秋時期晉國的里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②《墨子·七患》,王煥鑣撰:《墨子集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頁。僖公二十七年晉國準備與楚國進行城濮之戰,三軍主帥的人選上,講求德、義的卻縠得到認可:“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③《國語·晉語二》,第199頁。晏子則注意到“利”是人的本性,“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所以“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認為應以正義作為規范利益的前提,防止爭利失序。《逸周書》也說“故必以德為本,以義為術”。
然而在儒家一些人看來,“德”、“利”是對立的:“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④黃懷信:《逸周校補注釋·柔武解》,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131頁。荀子同樣不太重視“利”,而推崇“義”與“忠信”,視其為“大本”:“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背信而天下亂。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⑤《禮記·大學》,第993頁。
戰國晚期同樣倡“義本”之說,但認為“義”是一種極高的要求及標準:“故義者百事之始也,萬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⑥《荀子·強國》,第298-299頁。
6.孝本與務本
如不先入為主地考慮儒家的“孝”觀念,就會發現春秋時期“孝”與宗教“神”是緊密相關的。晉周在周與單襄公共事,只要談到“孝”一定就會提及“神”,于是單襄公認為應:“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孝,文之本也;……昭神能孝……”⑦《國語·周語下》,第61頁。在單襄公看來,“孝”是一種虔誠的從事宗教活動的行為和心理狀態,“文”代表某種人格精神力量,這種意義上的“孝”才能成為“文”的前提或基礎⑧韋昭注引《孝經》云“言人始于事親”,以“孝”后來的意義誤解“孝”的早先意義。。孔子以后,經過儒家對“孝”的重新解釋或定義,“孝”宗教上的話語意義逐漸淡化,最后僅僅意味著對父母和君王的絕對的“孝忠”。
《孝經》中孔子認為“孝”是“德”的前提,是“教”產生的基礎:“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⑨《孝經·開宗明義章》,《十三經注疏》,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2頁。孔子弟子曾參對“孝”異乎尋常地狂熱,他力圖將“孝”的觀念絕對化、普世化:“眾之本教曰孝”,“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后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詩》云:‘自西向東,自南向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⑩《禮記·祭義》,第818-819頁。曾子認為“孝”可以超越時間、空間的限制,成為一種永恒的宇宙精神。更進一步“,孝”有沒有自身的“本”呢?他認為是“忠”“:忠者,其孝之本與!”11《大戴禮記·曾子本孝》,《大戴禮記》,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147頁。
孔子弟子有子在探討“孝本”的基礎上提出了“務本”觀:有子認為“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12《論語義疏》,第5-6頁。秦國編寫的《呂氏春秋·孝行》篇中,從儒家“孝”的角度出發,提倡“以孝治天下”的“務本后末”觀:“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后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眾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于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
7.不背本
《左傳》和《國語》都推崇“不背本”,這種觀念顯然是由華夏族的“祖先崇拜”而來,成為一種普遍受到贊譽的宗族道德精神。例如《左傳》中的“楚囚”①《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845頁。,《國語》中的晉周②《國語·周語下》,第62頁。,都因為“不背本”的行為而獲得當時精英階層主流價值觀的肯定。
這里“本”有兩層意義,一層代表其家族先人,一層代表其母國,體現了一種雙重認同:個人的宗族身份認同和國家認同。這兩層意義和認同時常是混合在一起的。“不背本”在儒家那里,也稱為“不忘本”:“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③《禮記·檀弓上》,第115頁。《禮記·樂記》也說“禮,反其所自始”。可見“禮”本身就蘊含著“不忘本”的意義,即“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也”。④《禮記·禮器》,第455頁。如果將“不忘本”替換成肯定句式,就是前述荀子所推崇的“貴始”。然而“不忘本”既非天生,又非人所共有,這就需要采取某種方法來培養或引導,如“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⑤《禮記·鄉飲酒義》,第1014頁。在“不忘本”基礎上,還應進一步采取體現“報本反始”的祭祀行為:“社,所以神地之道也……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而“大報本反始”則是國家最高的祭祀行為:“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⑥《禮記·郊特牲》,第479、488頁。這些不同層次、等級分明的祭祀的意義在于:“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⑦《禮記·祭義》,第812頁。
(二)《老子》的“根”、“本”觀及其回響
《左傳》、《國語》中“本根”常常并稱連用,如《左傳》隱公六年周任建言及《國語·晉語八》陽畢建議平公滅欒氏,意指“本根”的連帶喻義(連本帶根),而非區分二者的差別。那么在《老子》中,“本”、“根”是否也存在類似的情況呢?
《老子》中關于“本”的討論極為罕見,僅有唯一的一條:“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榖,此非以賤為本耶,非乎?”⑧《老子》第三十九章,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8頁。《老子》中的“根”論要遠比“本”論多得多。老子所言的“根”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根源意義,如“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一種是根基意義,如“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相較于春秋時代的論者留心于“本”,老子則更為關注“根”。老子所著重的是“根”、“本”原始意義上的區別,即根源(本原)與基本的區別。戰國時韓非子精細地探討了老子所說的“根”的本意:“樹本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
繼承了老子哲學思想的莊子,對“本”、“根”的意義同樣是明確區分的:《應帝王》中有一寓言式的人物名為“天根”;《大宗師》云“夫道……自本自根”。莊子和老子一樣,也將“道”看作世界的本原或本體,認為“道”產生了宇宙和自然的一切。但莊子的問題意識在于,“道”本身又是怎樣產生的呢?老子對這個問題存而不論,并沒有提出清楚的說明。莊子則給出了進一步的解釋,認為“道”是“自本自根”的母體:它自己產生了自己(自根),同時還要維持自身的存在(自本)。
春秋以來各家各派的論者都提出了本末論,并且從未懷疑過各自本末觀的絕對真理性;而戰國的莊子一方面除了繼續使用這種本末話語,另一方面卻對本末話語本身的絕對性產生了懷疑,從而把思考的角度轉向了本末認知本身。《莊子》外篇《知北游》說:“彼為本末非本末”。在他看來,各家各派各本其所本,只是表達了不同的立場,在其自身所屬的傳承系統內或許不會受到質疑或挑戰,然而一旦超出各家各派的論域,那么就沒有任何一家比另一家更有本末話語上的特權,即己方的本末論是唯一正確的。
三、結語
以上對春秋時代整個“本末論”的面貌進行了詳盡的考察和審視,那么本末話語的意義何在呢?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去詮釋春秋時代的“本末”話語。①此節部分解釋參考了筆者碩士畢業論文《春秋戰國的本末論研究》(2007年)。
1.“本末”的語義。“本”本來是“樹根”的意思②徐中舒主編:《漢語大字典》卷三,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3頁。,但后來“本”、“根”的意義就各自分開了,至少在《詩經》里面,“本”就已指“樹干”了。《說文解字》以“木”作為區分本、末、根的參照:“木下曰本”③(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鳳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437頁。,“木上曰末”④《說文解字注》,第438頁。;而“柢”、“根”、“株”的意義完全一樣,都是“木根也”。“標”與“末”同義:“木杪末也。從木,票聲。”段注:杪末,謂末之細者也。古謂木末曰本標,如《素問》有《標本病傳論》是也。亦作“本剽”,如《莊子》云“有長而無本剽者”是也……《逸周書》中已有“標本”論:非本非標,非微非輝。壤非壤不高,水非水不流。嗚呼,敬之哉!倍本者槁。
2.“本末”話語的表述形式。春秋時的“本末”有兩種表達方式,一種是僅僅表述“本”的,另一種是同時表述“本”與“末”的,這兩種表述各有其特點。
在僅僅表述“本”的情況下,其語境意義大致有四種:
(1)某種決定性或基礎性的力量。例如《中庸》認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⑤《逸周書校補注譯·文儆解》,第118-119頁。;再如體現春秋“民本”觀念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⑥《禮記·中庸》,第878頁。。“本”與“源”、“基”在這個意義上是相通的,如前引史蘇論驪姬亂晉。
(2)充當某種前提條件或先決條件。例如“昏禮者,禮之本也。”⑦《尚書·夏書·五子之歌》,第118頁。
(3)事物產生的根源,或者事物的本質、本原,即哲學上的“本體”論。例如老莊以“道”作為世界的本原;曾子認為“神靈者,品物之本也”。⑧《禮記·昏義》,第1004頁。
(4)歷史事實變動的因果律。如前述的“治亂之本”。
在同時表述“本”與“末”的時候,其語境意義有兩種:一種顯示相互對立的意味兒,一種顯示相互統合的意味兒。前者重在區分價值上的重要與不重要,判定和分析是否存在“舍本逐末”或者“本末倒置”的情形,提倡“知本”或“務本”,從而明確達到“正本清源”的方法或途徑。后者則將重要與不重要都視為整體的構成要素,強調的是一體化。當“本末”與《詩經》中的“終始”⑨《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第150頁。觀念結合,就形成了“本末終始”論:“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⑩見《詩·大雅·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王陽明的解釋即著眼其統合意義“:夫木之干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11《禮記·大學》,第987頁。
3“.本末”話語的作用。如果綜觀一下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史,就會發現其中一個極其鮮明的“本末”特質:春秋時期的“禮本”思想、“德本”思想“、義本”思想“、民本”思想等,戰國時期的“農本工商末”思想“、法本”思想等,以及古醫學上的“標本兼治”論,都是通過緊密結合“本末”形式來表達的。如果缺少了這種“本末”特質的承載,春秋戰國的思想史無疑就將大為遜色。12《大學問》,《王陽明集》,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360頁。
春秋時代的論者,借助于“本末”的比喻、隱喻、轉喻、諷喻,用來說明事理,參與論辯,表達立場,影響他人,從而形成了層出不窮、各“本其所本”的話語現象。這種現象引起了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注意而競相模仿,塑造了諸子百家的“本末”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方式最終成為中國人的一種認知方式。
[1](漢)司馬遷.史記[M].中華書局,1959.
[2]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M].學林出版社,1984.
[3]顧德融,朱順龍.春秋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4]楊寬.戰國史(增訂本)[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5]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M].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6]許倬云.歷史分光鏡[M].中華書局,2015.
[7]葛兆光.中國思想史[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8]馬伯煌.中國經濟政策思想史[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9](英)葛漢瑞.論道者[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10](美)本杰明·史華茲.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M].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責任編校:陽玉平]
G05
A
1002-3240(2017)05-0140-07
2016-12-11
李曉東(1975-),四川樂山夾江縣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近現代史博士生,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史、近現代史;陳廷湘(1948-),四川彭州市人,四川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文化史、中國近現代的思想與學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