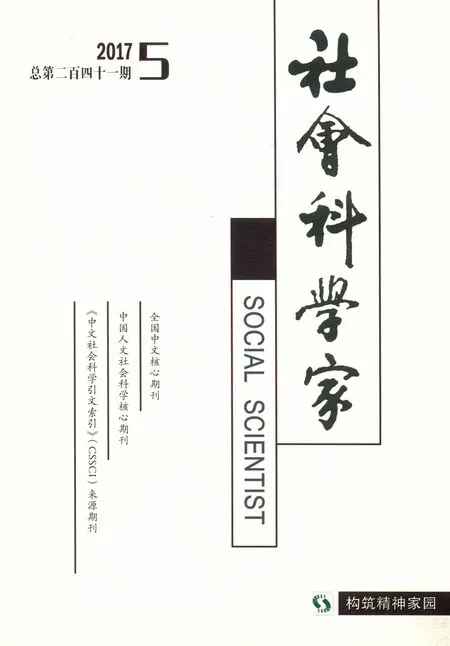從出土文獻詞匯變化看秦文化發展演變
李園
(東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從出土文獻詞匯變化看秦文化發展演變
李園
(東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秦始皇建立起了我國第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秦文化在我國文化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秦出土文獻的刊布彌補了傳世文獻的缺憾,能夠進一步了解秦文化的真面目。我們從秦人的避諱、秦地方言、秦統一前后稱謂變化等詞匯角度著眼,發現秦統一以后,秦文化具有皇權至上、強制性和與時俱進等特點。
出土文獻;詞匯;秦文化
據《史記·秦本紀》[1]記載,秦之先祖本為西陲部族,因襄公時有功于周室,始封諸侯,居于宗周故地。因為地處內陸,文化相對保守,形成了自己的風格與特色,李學勤先生稱之為“秦文化圈”①李學勤先生指出:“把文獻和考古成果綜合起來,我們覺得不妨把東周時代列國劃分為下列七個文化圈”,即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齊魯文化圈、楚文化、吳越文化圈、巴蜀顛文化圈、秦文化圈。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2頁。,“秦兼并列國,建立統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為后來輝煌的漢代文化的基礎。”[2]由于流傳下來的秦典籍并不多,主要有《詩經·秦風》、《尚書·秦誓》、《呂氏春秋》、《諫逐客書》等,加之在傳承的過程中,增刪整改,已經不能完整地呈現秦文化當時的狀態,值得慶幸的是,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出土文獻給我們提供了新的證據,使世人能夠重新認識秦文化的真面目。我們從秦人的避諱、秦地方言、秦統一前后稱謂的變化等詞匯角度來探討一下秦文化的相關特點。
一、避諱所反映的秦文化特點
避諱是古代文化在語言上的重要表現形式,分為“國諱、家諱、賢諱、特諱、官諱、俗諱”[3]等不同的種類,傳世文獻到了春秋時,才有了對避諱的記載,《辭源》將“避諱”解釋為“古人在言談和書寫時要避免君父尊親的名字。對孔子及帝王之名,眾所共諱,稱公諱;人子避祖父之名,稱家諱。避諱之法,一般或取同義或同音字以代本字,或用原字而省缺筆劃。”[4]秦文化在統一之前對避諱并沒有嚴格的規定,統一之后融匯中原文化傳統,頒布詔令或使用法律手段,規定不能使用的詞匯。
對秦始皇名號的避諱。《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于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鄲。及生,名為政,趙氏。”集解:徐廣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正義: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旦生于趙,因為政,后以始皇諱,故音征[1],這是傳世文獻對秦始皇名字由來及避諱的記載。出土的秦簡牘文獻為避“正”字,將“正”改為“端”,如“正月”改為“端月”,陳偉先生通過對秦簡牘“正月”“端月”的研究得出兩條結論:“第一,在同一年,或稱‘正月’,或稱‘端月’,二者不同時使用。第二,在秦王政時期,只稱‘正月’而不稱‘端月’。在秦始皇統一之初的二十六、二十七年,只稱‘端月’而不稱‘正月’。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只稱‘正月’而不稱‘端月’。在秦二世元年,只稱‘端月’而不稱‘正月’”,[5]說明在秦始皇時期,避諱帝王的名號,尚有不固定性,還在形成的過程之中。將“正”“政”改為“端”還表現在,將“矯正”“自正”“公正”“邦政”改為“矯端”“自端”“公端”“邦端”,甚至將“正”改為“平”,在秦始皇統一前的《睡虎地秦墓竹簡》中作“正”,在統一后的《岳麓書院藏秦簡肆·秦律令》[6]中作“平”。為了避秦始皇名諱,“正”“政”都需要用同義詞進行替換。
為避“皇帝”稱號,將字形似“皇”的“辠”字改為“罪”,秦時“罪”“辠”皆已出現,《說文》[7]①(漢)許慎撰,(宋)徐鉉,《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13.簡稱《說文》,下同。解釋“罪”指捕魚用的竹網,“辠”才是犯罪的意思,但是因為“辠”字似“皇”,所以用同音的“罪”字來代替。《禮記·服問》:“罪多而刑五”,陸德明釋文:“罪,本或作辠。辠,正字也。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為罪也。”[8]隨著出土文獻刊布的越來越多,學者證實了“始皇二十六年七月至三十年五月,一直采用‘辠’字,并可與抄寫年代更早的睡虎地秦簡相銜接。而在三十四年六月以后,直到二世元年,多條數據均采用‘罪’字,并可與漢代簡牘用字相銜接。由于兩種寫法前后分別,不存在交叉、混用的情形,可以相信秦代用‘罪’字取代‘辠’字,發生在始皇三十年五月至三十四年六月之間。”[9]不僅證實了統一以后,由于避諱,將“辠”字改為“罪”字的歷史事實,更考證出了這一事實出現的大體時間。
對秦始皇父親莊襄王名字的避諱。《史記·秦始皇本紀》索隱:“莊襄王者,孝文王之中子,昭襄王之孫也,名子楚。按《戰國策》‘本名子異同,后為華陽夫人嗣,夫人楚人,因改名子楚也’”[1],秦始皇統一后,為避父親莊襄王名諱,規定人們稱楚國為“荊”,而不能稱“楚”。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歷史上首次出現避諱國名,岳麓秦簡中有一條律令:
2026:●令曰:黔首徒隸名為秦者更名之,敢有有弗更,貲二甲。
大意是說是百姓和奴隸名字為“秦”的都要更改,如果有不更改的,懲罰繳納兩副鎧甲(或者兩副鎧甲折合的錢數②于振波先生指出:“秦律貲罰中甲的價格為金2兩1錘或1344錢。”于振波:《秦律中的甲盾比價及相關問題》,《史學集刊》,2010年第5期。),在當時也是比較重的懲罰。這是統一之后頒布的律文,陳松長先生根據該條律文指出:“秦代有關避諱的規定,也是有等級規定的。這里所劃定的范圍是黔首和徒隸兩大類,也就是說,它是針對沒有什么社會地位的一般百姓和徒隸而設定的,因此如果有爵位的人,可能就不受此令文的約束了”[10]。而里耶秦簡8-461木方記錄了一條與之相反的規定:
諸官為秦盡更。(8-461正AXⅦ)[11]
游逸飛先生改釋為“諸官?名?為秦,盡更”,意思是“所有秦朝官吏的私名若有‘秦’字,均須更改。”[12]根據木方抄錄內容的整體安排,游先生的這個解釋應該是合理的。孫兆華先生從律文針對對象的不同,提出“部分秦法律令的頒布可能有一個從特殊群體到下層人群的順序”[13],這一觀點可以作為深入研究的參考,但是真實情況是否是這樣,還需要更多的出土材料來印證。法律做出這樣的規定,說明當時名為“秦”并不是罕有的事情,在《岳麓書院藏秦簡(三)·學為偽書案》[14]中,記錄了一個名為“秦”的人,朱錦程先生指出“這則奏讞文書的時間是‘廿二年八月’,據此可知最遲在秦始皇二十二年(前225),秦國境內確有人以“秦”為名,屬尋常事,毋須因此受罰。”[15]可見,在秦統一之前,并不避諱以“國名”命名,秦始皇統一以后,從秦朝的官吏到下層的普通百姓都不能以“秦”命名,否則就會受到相應的懲罰。
由避諱可以看出,統一后的秦文化凸顯了皇權至上的特點,凡是和皇帝有關的事物,都需要避諱。秦避諱文化也經歷一個從無到有,從不確定到確定,以及內容不斷擴充的過程,是我國避諱發展的關鍵時期。陳垣先生指出“避諱為中國特有之風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歷史垂二千年。”[16]通過我們的研究證實,事實的確如此。
二、秦方言進入通語反映的秦文化特點
中國自古以來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形成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語言,《漢語大詞典》對“方言”的解釋:“語言的地方變體,一種語言中跟標準語有區別的、只通行于一個地區的話。”[17]古代的標準語即“雅言”,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普通話”,《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18]《荀子·正名》:“散名之加于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19]這是說因為普通話的存在,不同地方雖然語言不同,但是對事物可以有相同的認識。隨著人員往來的日益密切,語言也互相滲透,互相影響,“語言文字是全社會的公器。語言從誕生那天起,通與俗就一直處于相互交變中。”[20]在王朝更迭的古代,戰勝的君王自然會帶著自身從小到大所熟悉的語言文字,進入到新的統治系統中,秦統一六國后,在強大的皇權保護下,屬于秦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秦地方言自然而然地進入普通話。
如將表示“欺騙”義的“詑”改為“謾”,秦統一之前,在法律文書中,“詑”的使用很普遍,《說文》認為“詑”是沇州方言,“沇州即袞州,兩漢時袞州治昌邑,地域當在今山東境內。也就是說,‘詑’可能是齊方言詞”[21],從語言產生上來看,“詑”可能出自齊魯之地,但是從使用程度上來看,當時已經進入了普通話的范疇,“謾”則是秦地方言,《方言·卷一》:“虔,儇,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宋楚之間謂之倢,楚或謂之,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因為秦的統一,由法律規定強行進入到普通話中,到了漢初的《張家山漢簡》[22]中,“詑”“謾”均在法律文獻中出現,“詑”出現2次,而“謾”出現4次,說明“謾”已經為人們所接受,并且廣泛運用。
《說文·黑部》:“黔,黎也,從黑今聲。秦謂民為黔首,謂黑色也。周謂之黎民。”“黔”、“黎”都為“黑”義,“黑色,是長年露天作業,承擔重體力勞動者的正常膚色”[23],所以稱“民”為“黔首”、“黎民”。通過對出土秦文獻和傳世文獻《呂氏春秋》的研究,“黔首”在當時為秦地流行語,隨著秦的統一而進入普通話,正如《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1]出土文獻證實了秦統一后確實將“民”改為“黔首”,但是并不徹底,如《放馬灘秦簡》就“民”與“黔首”共同使用,在秦滅亡以后,“黔首”的使用就很少了。
其他進入普通話的秦方言,如秦統一后明確規定“豬”應稱“彘”,不能稱“豬”,《方言·卷八》:“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西或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貕,吳揚之間謂之豬子。其檻及蓐曰橧。”“秦代語言政策的變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直接導致秦統一后至西漢早中期的語言中‘豬’的消失。”[24]
秦文化因為中央集權而具有的強制性,為后世語言文化統一建立新的模式,如“驛站”名稱的由來,“驛站”本來叫“驛”,是中國古代供官府傳遞文書和軍事情報的人或來往官員途中食宿、換馬的場所,蒙古語叫作“站”,蒙古族建立了元朝之后,將“驛”改稱為“驛站”。
三、稱謂變化所反映的秦文化特點
秦始皇建立了我國第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一些舊有的稱呼已不適應新的統治形式,《史記·秦始皇本紀》: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謐。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后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出土文獻中也記錄了相應的規定,如里耶秦簡8-461記載了這些變化,隨著郡縣制的建立,統一前的封國稱為“邦”,統一后改為“郡”,如“邦司馬為郡司馬”;因為統一,一些邊塞消失了,“邊塞曰故塞”。統一前對君王的一切稱呼,統一后都改為“皇帝”,如“王游曰皇帝游”,“王獵曰皇帝獵”,“泰【王】觀獻曰皇帝”,“天帝觀獻曰皇帝”,“帝子游曰皇帝”;與帝王執政的有關稱謂也發生了變化,命曰制,令曰詔,如“受(授)命曰制”,“以王令曰【以】皇帝詔”;追封秦襄王,如“莊王為泰上皇”。秦文化與時俱進,既保持自己的傳統,又不斷吸收新的養分。
出土文獻對秦文化的研究意義重大,史料不足造成的缺憾得以彌補。文化的統一是其他一切社會活動運行的基礎,秦用法律規定了詞匯的使用情況,體現了秦文化“以法為教”的特點,從避諱、方言等表現出來的秦文化皇權至上、強制性的特點,為焚書坑儒埋下了伏筆。從稱謂的變化表現出秦文化與時俱進的特點,秦文化與其他地域文化,在融合與沖突中,完成了中央集權制的雛形,為后世提供了借鑒,漢承秦制,最終奠定了整個中華文化的基礎。
[1](漢)司馬遷,(宋)裴骃,(唐)司馬貞,(唐)張守節.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4.223-286;289-290;289;207-308.
[2]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M].13.
[3]向熹.漢語避諱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3.
[4]何九盈.辭源(第三版)[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4070.
[5]陳偉.秦避諱“正”字問題再考察[EB/OL].簡帛網,2014-08-27,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62.
[6]陳松長.岳麓書院藏秦簡(肆)[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
[7](漢)許慎,(宋)徐鉉.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2013.
[8](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禮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9.3600.
[9]陳偉.秦簡牘中的“辠”與“罪”[EB/OL].簡帛網,2016-11-27,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73.
[10]陳松長.秦代避諱的新材料——岳麓書院藏秦簡中的一枚有關避諱令文略說[N].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9-10(5).
[11]陳偉.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156.
[12]游逸飛.里耶8-461號“秦更名方”選釋[EB/OL].簡帛網,(2013-08-01),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75.
[13]孫兆華.從岳麓簡“秦更名令”看秦統一對人名的影響[J].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2).
[14]朱漢民,陳松長.岳麓書院藏秦簡(叁)[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228.
[15]朱錦程.秦代避諱補論[EB/OL].簡帛網,(2016-05-24),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61.
[16]陳垣.史諱舉例[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77.1.
[17]漢語大詞典編纂處.漢語大詞典(第六卷·下冊)[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1558.
[18](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1.94.
[19](戰國)荀況,王天海.荀子校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882.
[20]李圃.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
[21]朱湘蓉.秦簡詞匯初探[M].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95.
[22]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23]王子今.秦漢稱謂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15.
[24]胡琳,張顯成.“豕、彘、豬”的歷史演替:基于出土簡帛新材料[J].求索,2015(2).
[責任編校:陽玉平]
H03
A
1002-3240(2017)05-0154-04
2016-11-11
本文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公布三種秦簡字詞研究”(14CYY024)的支持
李園(1987-),女,東北師范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生,主要從事古代漢語、古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