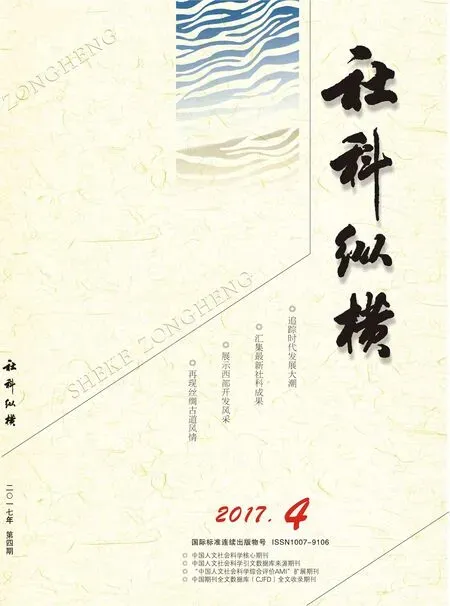《詩經》中農事詩的農學思想探析
譚清華
(中共柳州市委黨校 廣西柳州 545616)
《詩經》中農事詩的農學思想探析
譚清華
(中共柳州市委黨校 廣西柳州 545616)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現實主義的詩歌總集,整個《詩經》反映了周民族以農立國的社會特征和西周初期的農業生產情況。《詩經》農學思想極為豐富,在我國農學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其中的農學思想主要表現在“重農、保農”的農家樂思想、濃厚的農時觀、精耕細作的耕作技術思想、多種經營思想、倉儲和農產品消費思想等幾個方面。
詩經 農學思想 探析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現實主義的詩歌總集,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之后始稱《詩經》[1],并沿用至今。共收集了311篇詩歌,現存305篇,按用途和音樂分“風、雅、頌”三部分。其中《頌》和《雅》基本上都產生于西周時期;《國風》除《豳風》及“二南”的部分篇章外,均產生于春秋前期和中期。“風”是指所收集的各地民間歌謠,它反映下層民眾的社會生活。“雅”大部分為西周初期貴族的宮廷正樂,“頌”是周天子和諸侯用以祭祀宗廟的舞樂,除了單純歌頌祖先功德以外,還有一部分為春夏之際向神祈求豐年或秋冬之際酬謝神的樂歌。整個《詩經》反映了周民族以農立國的社會特征和西周初期的農業生產情況。首先,《生民》敘述后稷的神話色彩。后稷長大以后,發明了農業,他也就成了周民族的始祖和農業之神,反映了周民族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征。其次,從“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綿瓜瓞》等詩篇可看出周族確是“興于農”。《豳風·七月》則完整敘述了一年之中的農事活動與當時社會的等級壓迫關系。另外,在《詩經》中的《南山》《楚茨》《大田》《豐年》《良耜》以及《周書》內的《金滕》《梓材》《康誥》《洛誥》《無逸》等篇都記載了相關農事。所以,《詩經》農學思想極為豐富,在我國農學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以今天的標準來看,其中的農學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重農、保農”的農家樂思想
“重農、保農”思想是原始人類基于生產能力極為低下狀況所提出的一種農學思想,長期以來不斷得到人們的重視與實踐。到了《詩經》創作的春秋戰國時期,我國的原始農業已慢慢向精耕細作的農業模式轉化,農業生產力有了明顯的提高,人們的“重農、保農”思想也有了明顯的改變。在《詩經》中突出表現為民間對農業生產過程中快樂情境和自給自足、國富民安等豐收景象的描繪,這可以說是后來農事詩的發端,從文學史來說,也是后代田家詩的濫觴。如《豐年》中唱道:“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描繪了農家豐收的快樂境況。又說:“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暗示人們必須以農為重才能永享太平。當然,它也認為農業生產的豐收是神靈幫助的結果,所以農業豐收之時不要忘記“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也只有農業生產豐收才能更好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這是原始人類所具有的普遍共識。《噫嘻》則描繪了大規模耕作的情形:“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谷。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這段文字含義比較豐富,既突出了農時觀,又提及到多種經營。這句話只有從整體考慮才是突出大規模耕作的盛況。取名為“噫嘻”,包含一種以農為樂的思想,體現“重農、貴農、保農”觀。
二、濃厚的農時觀
整個《詩經》中,農時觀的內涵十分豐富,它既告訴人們怎么樣確定農時,還告訴人們適時而作、不違農時的道理。所以,《詩經》中的農時思想多處可見。
就怎樣確定農時來說,《詩經》仍根據人們對生產實踐的總結,提出利用觀天察物的物候、氣候等方法確定農時。農業生產是以自然物質為生產對象的生產活動,其收成好壞、效率高低深受自然環境的影響,因此,農業生產對自然條件有嚴格要求。但自然條件變化不居,只有靠觀察外界物象和氣象來感知自然界變化,所以農業生產過程中非常重視物候和氣候知識的獲得和利用。我國在原始社會時期已使用物候審時并適時安排農事了。隨著對植物品種及其生長規律的認識,輔之以對蟲魚禽獸出沒活動時間等觀察的經驗積累,最終形成以物候為標志的記時體系——物候歷。在天文歷法發展史上,物候歷是一種早于以觀察天象變化定時的天文歷。這種物候歷在《詩經》中主要表現在《豳風·七月》中,十五《國風》以《豳風》的年代最早。其中,一般人以為產生于西周初的《七月》,以詩歌形式記載了每一個月的物候,這是中國以詩歌形式總結和傳授物候知識的最早記載,有人稱其為“最早的有關物候學的詩歌”[2]。這種物候記載的目的在于適時安排農事,故它又是我國最早的一首農事詩。與《周頌》中的農事詩不同,它以相當長的篇幅,敘述農夫一年四季的勞動生活,并記載了當時的農業知識和生產經驗,像是記農歷的歌謠。它依據每個月的物候、氣候差異,對每個月的農事做了安排。例如《周頌·臣工》說:“序乃錢鑄,奄觀錘艾”。這句話的意思是在暮春時節命眾人把中耕用的錢镩收藏起來,準備開鐮收麥,說明農事安排看重農時。
三、精耕細作的耕作技術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我國精耕細作農業模式的形成,農學思想也日趨豐富,此時最主要的特點在于農學思想中注入了一種新的思想內涵——農業耕作技術思想,并且已成為農學思想中的核心內涵。從《詩經》內容來看,其耕作技術思想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耕作工具。農業工具的使用和改善是農業生產經驗日益積累的結果,是農業生產力的表現。在生產過程中,人們發現先進農具在農業生產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故而十分關注農業生產工具的使用和改進,在《詩經》中屢屢被提及,例如《周頌·臣工》記載:“序乃錢鑄,奄觀錘艾”。其中錢鑄錘皆從金,表明這些工具皆為金屬工具,說明當時生產工具制作已經達到一個空前水平。錢即現在適用于行壟間、雙手握柄貼地推進以除草松土的鏟,鑄即中耕工具,用來耘鋤田間雜草,類似于現在的鋤頭。在其《周頌》的《臣工》《載芟》《良耜》諸篇中屢屢提及,以耜“俶載南畝,播厥百谷”。耜即用來松土、挖掘溝渠的重要耕具,并且已經達到鋒利的程度。
(二)耕作方式。耕作方式不僅決定光和氣的使用效率,而且決定農業生產工具的使用效率,是農業生產水平的重要標志,所以,《詩經》十分關注耕作方式的記載和探討。《詩經》屢屢提及“俶載南畝”,如《小雅·信南山》中的“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南畝”就是根據“土宜”即地勢高低或者水流方向和是否向陽等因素來決定將壟修成南北向或東西向。《小雅·大田》中有“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谷”。具體說明了大田耕作技術,其中的“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說明農業生產中的輪作技術已經產生。《大雅·生民》有“藝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反映了當時的條播技術水平和輪作、插種技術,“禾役”指禾苗的行列。禾苗行列播植是為了通風和容易接受陽光,說明當時已經認識到采光和通風對于農業生產收成的重要。不僅如此,《詩經》中還出現了中耕技術的記載。中耕技術是指農作物種植之后,人們為了幫助農作物快速健康生長所采取的清除雜草、松土等措施和方法。《稻人》的“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就是一例,它反映了南方火耕水耨技術。在耕作過程中必須進行中耕,除草救苗,因為“若苗之有莠”影響作物的生長,同時也采取點播和條播來減少中耕耘耔的勞動量。
(三)殺蟲技術和水利灌溉技術。這是《詩經》中農業系統論的充分表現,這說明《詩經》不僅強調生產對象本身的成長規律,而且也十分重視農業外部環境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根據《大雅·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稚”的記載,說明西周時期人們已經對農作物病蟲害種類有了相當高水平的認識。《小雅·大田》中也說“田祖有神,秉畀炎火”。這說明當時人們已經認識到害蟲向火的特性,并且已經采取了利用火光誘殺害蟲的生物技術。《小雅·小宛》中記載“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不僅如此,還有許多記載使人們明白當時已經認識到蝙蝠、螳螂、蜥蜴對諸蟲,鼬等對鼠的賊害作用,這標志著人們已經把握各種昆蟲之間相制約、相勝服、相賊害的自然現象,開始關注和利用昆蟲之間的關系進行病蟲害防治,這是農業生態技術的反映。對于病蟲害的防治,它還強調用植物藥物治蟲的生態方法,例如“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莽草”就是“毒八角”。還如“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此處的“嘉草”為“襄荷”。春秋戰國時期,為了應對干旱氣候,灌溉技術得到人們的重視,這在《詩經》中也有所反映。《大雅·黍苗》有“原隰既平,泉流既清”。說明了平治水土要達到“既平、既清”的要求才有利于農業生產。《大雅·洞酌》有“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說明南北取水和農田用水的人工灌溉技術已經出現。首先是引泉水灌溉,《小雅·大東》有“有冽氿泉”。《邶風·泉水》有“我思肥泉”。《曹風·下泉》有“冽彼下泉”。共有六種名稱,說明當時人工灌溉技術的發達。后來,農田水利建設工程開始出現,《陳風·澤陂》中的“陂”就是這一時期創造的人工蓄水工程。
(四)選種育種技術。《大雅·生民》記載了“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這句話說明當時人們已經注意到播種前選擇優良種子的必要性,也介紹了秬、秠、糜、芑等多種優良品種。除此之外,《詩經》還說明了種與時的關系,要求不同品種不同時間播植。在《豳風·七月》中有“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和《魯頌·閟宮》的“九月筑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植稚菽麥”。這里的麥子是春麥,而《周頌·臣工》的“序乃錢鑄,奄觀錘艾”中所提到的麥子是冬麥。這兩句話說明當時人們已經認識到收獲期遲早和播種期先后不同的品種。
四、多種經營思想
當今人們對于遠古農業的研究多從古籍人手,《詩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研究資料,至少我們可以從中發現當時人們吃、用的物質種類繁多,這說明當時多種經營的農業模式已經十分成熟。我們從詩中看到,農夫們既要在田中耕作收獲,又要種桑養蠶,紡麻織絲,打獵捕獸;農閑時還得到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寒冬里鑿取冰塊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們夏日里享用,一年到頭,周而復始。
在畜牧業方面,當時已經出現并十分重視家畜飼養和繁殖技術,所養殖的家禽家畜種類繁多。首先,《詩經》中已提及到許多家畜名稱:羊、馬、牛、象、鹿。其次,它還提及到以大規模放養為主的群養方式,《小雅·無羊》:“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小雅·鴛鴦》:“乘馬在廄,推之秣之”。《周南·漢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說明了主人護馬喂馬的仔細周到。《大雅·靈臺》:“王在靈圃,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鶴鶴”,此記載說明王公靈圃飼養的興盛與快樂。《鄘風》記載“鶉之奔奔”,此記載說明當時已經開始了鵪鶉的養殖。不管是官營的還是民營的,畜牧技術均以放牧和割草圈養為主,這以上述的《小雅·無羊》和《小雅·鴛鴦》的“執豕于牢”,《大雅·公劉》的“乘馬在廄”,《周南·漢廣》的“秣”即割谷子喂養為證。非常重視家畜繁殖技術,例如《費誓》中說:“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攫,敏乃穿,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即在放種畜通淫配種期間,不得傷害種畜,應撤離誘捕野獸的設施。不僅如此,《詩經》還提及到牲畜的身體狀況,表明人們已經開始注意到牲畜的各種疾病,出現了病因學的發端和獸醫技術的初步發展。例如在《小雅·無羊》中用“濈濈、濕濕、矜矜、兢兢”表示牛羊健康,同時也用“騫、崩”表示牛羊病態。在《小雅·四牡》《小雅·杕杜》和《周南·卷耳》中分別用“玄黃”“瘏”等來表示牲畜病狀,從而說明當時獸醫技術的出現。最后,還記載有人們對于家畜的役使,《小雅·六月》:“戎車既飭,四牡骙骙”。《小雅·車攻》:“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小雅·四牡》:“駕彼四駱,載驟骎骎”。將馬分別用于戰爭、狩獵和交通。
在水產養殖方面,《大雅·靈臺》說:“王在靈沼,于牣魚躍”。此處的池為人工穿地通水或積水的工具,具體說明了人工養魚。在水產捕撈和人工養育方面,捕撈方法除了新出現的網、梁、潛技術之外,射、叉、釣等古老方法仍在使用。還多次提到“魚梁”這樣一種與魚笱連用的捕魚方法,如在《邶風·谷風》中說:“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在《齊風·敞笱》中說:“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在《小雅·魚麗》中提到“魚麗于罱”。《詩經》在此基礎上對捕撈工具做了詳細記載,除了網之外,還分別在《衛風·碩人》中記載“罛”:“施罛濺濺,鱧鮪發發”;在《豳風·九戢》中記載“九罭”:“九罭之魚,鱒魴”;在《小雅·南有嘉魚》中記載“汕”和“罩”:“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園藝業雖有所進步,但早期的園圃稱為囿,表明園圃業此時并未完全獨立。“九月筑場圃,十月納禾稼”反映了這種情況。園圃中所種的作物有該詩所提到的“韭”和《小雅·裳裳者華》中所提到的“蕓”,還有《詩經》中屢次提到的“葑”。到了春秋戰國后期,蔬菜又有所增加,例如,此時葵(冬寒菜)、姜蔥蒜等葷菜、筍、蒲等已經栽培和食用,在《小雅·北山》和《小雅·杕杜》中還分別提到枸杞,詩里稱之為“杞”。《小雅·瓠葉》中還提到“瓠”這一種葫蘆植物,《豳風·七月》或稱“匏”,《邶風·匏有苦葉》均異名同物,說明當時此物種植相當普遍。瓜果有《生民》中提到的“瓜”和《七月》中所提到的瓠、壺、匏,以及《魏風·園有桃》《齊風·東方未明》《鄭風·將仲子》詩中屢次提到的檀、桑、杏、梅、桃、棗、榛、梨、檖、桔、柚等。同時,《詩經》中記載有象、兕、梅、竹等亞熱帶動植物分布(據統計,《詩經》中至少有十篇記載兕、五篇記載梅、三篇記載竹),《詩經》中所記載的作物名稱達21種之多,其出現的先后次序是:蕢、麥、黍、稷、麻、禾、稻、梁、菽、苴、谷、芑、藿、粟、荏菽、秬、秠、糜、來、牟,多數是同物異名,概括起來無非就是黍、稷、稻、麥、桑、麻。商周時期糧食作物有黍、稷、稻、麥、菽、麻。說明當時氣溫較今天暖和,所以,此時的農事安排也略早于今天。
養蠶業是我國春秋戰國時期重要的副業部門,為保證我國居民的服飾做出了貢獻。其技術發展水平在《詩經》中亦已凸顯,據其記載,養蠶業開始人工種植桑樹,桑田已經出現,蠶桑事業遍及黃河流域。《鄭風·將仲子》中的“無折我樹桑”,《鄘風·定之方中》中的“說于桑田”,《魏風·十畝之間》中的“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說明了桑樹種植的普遍化和規模化,以及婦女在廣闊的桑田中采桑的場景。此外,我們從詩中也可看出養蠶業旺盛帶來了絲織業的繁榮,在《小雅·巷伯》中有“萋兮斐兮,成是貝錦”,這是我國關于錦的第一次記載,說明絲織業已經開始產生并迅速發展。
五、倉儲和農產品消費思想
農業產生和發展的動力是為了解決人們衣食住等生活需要,所以研究農學思想必須研究農產品的消費思想和消費狀況。在精耕細作的春秋戰國時期,他們吃什么?我們可從《詩經》中的《豳風·七月》看出:“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剝棗”;“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蘆、麻子這一類東西,當然這并不是食物的全部,而僅僅是其中的植物類食物。動物類食品包括人們所飼養的各種家禽家畜。為了應對季節變化和災荒年的需求,春秋戰國時期十分重視倉儲技術的開發。農畜產品儲藏技術方面,既有地面儲藏,也有地下儲藏,還有化學方法的儲藏。我國古代地面儲藏方式有倉、廩、庾三種,《詩經》中提及兩種,《小雅·甫田》記載:“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庾”為露地堆谷。《周頌·豐年》毛傳有“廩所以藏粢盛之穗也”。《小雅·信南山》有“疆埸有瓜,是剝是菹”。其中的“菹”,即鹽漬法,這是我國最早的化學保藏法。還有《大雅·鳧鷺》有“爾殽伊脯”,其中的“脯”,即切細曬干、晾干。還有《大雅·行葦》有“醓醢以薦”,其中的“醢”,即肉醬法。此時還出現了用冰冷藏的方法,這是地下儲藏方法的改進,見于《豳風·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中的夏天“鑿冰”。果蔬和畜產品加工技術主要有釀造技術,除了釀酒之外,先秦時期,我國人民已利用麥類和其他谷類發芽糖化,用濾去米渣后的糖化液汁煎成“飴餳”。《大雅·綿》記載:“周原膴膴,堇荼如飴”,使人們食物結構和種類有明顯的改善。
[1]周振甫.詩經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2.
[2]曹宛如.中國古代的物候歷和物候知識[A].中國古代科技成就[C].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257-263.
[3]章可敦.詩經經濟意識解讀[J].學術交流,2007(1).
[4]朱小鳳,劉文婷.淺論詩經中的農事詩[J].大眾文藝,2012(2).
[5]李成軍.論詩經中的飲食習俗與禮儀[J].學術交流,2010(8).
[6]呂華亮,王洲明.詩經名物研究的價值與意義[J].甘肅社會科學,2010(6).
[7]尹北直,張法瑞.詩經與傳統農業文化的形成[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4).
[8]黃志立,池萬興.從詩經中關于畜牧與農耕的記載看周代社會[J].語文知識,2012(2).
[9]張連舉.從詩經看周代的農業技術[J].廣東農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2).
[10]陳鵬程.試論詩經所反映的周人農業生產形態[J].安徽農業科學,2007(34).
[11]趙敏俐.略論詩經樂歌的生產、消費與配樂問題[J].北方論叢,2005(1).
[12]王文清.簡論詩經反映的周代自然科學知識[J].聊城大學學報(社科版),2004(2).
[13]畢國忠,張明閣.詩經農事詩與原始農業文明[J].農業與技術,2004(4).
[14]王新建,羅麗.先秦農事詩的社會及技術信息研究[J].唐都學刊,2003(3).
[15]馬志強.論詩經的農業經濟思想[J].河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1(2).
I207.222
A
1007-9106(2017)04-0116-05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道教農學思想史綱要”(項目號:10XZJ0007)的系列成果之一。
譚清華(1969—),哲學碩士,中共柳州市委黨校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史、道教科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