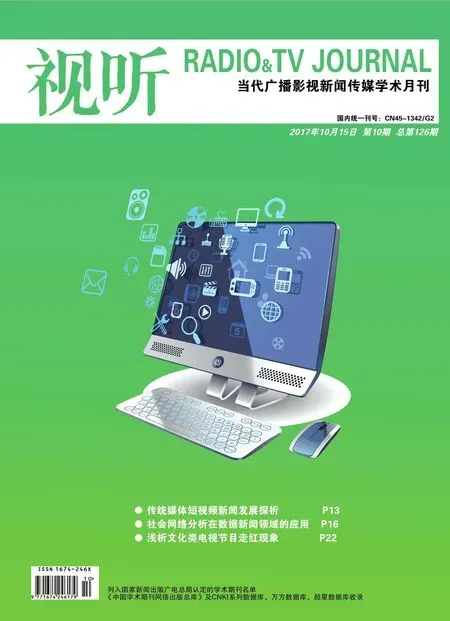淺析先鋒派電影風格的創新表現
——以《紅塵之門》的創作為例
□ 張興動 童 皓
淺析先鋒派電影風格的創新表現
——以《紅塵之門》的創作為例
□ 張興動 童 皓
近年來,先鋒派電影受到國內外電影節的青睞,雖然以好萊塢為中心的傳統主流敘事電影仍然影響巨大,但精英觀眾的增多也帶給了先鋒派電影發展的活力。當代先鋒派電影結合新的電影技術以及新形勢的要求,繼續對表現形式和表現技法進行探索和創新,對其他姊妹藝術新的借鑒也賦予了先鋒派電影新的風格特點。
建構主義;創作風格;視覺色彩;創新表現
一、先鋒派電影在藝術電影中的再次盛行
西方先鋒派電影分為前期先鋒派電影和后期先鋒派電影。前期先鋒派電影出現于20世紀10年代末,20世紀30年代突然中止;后期先鋒派電影出現于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延續至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隨后便逐漸退出觀眾的視野。近些年,傳統主流敘事電影在電影界已經暴露出其內容與形式方面的眾多弱點,隨著高素質觀眾人數的增多以及審美形式的多樣化,先鋒派電影在最近幾年頻繁出現在國際性的電影節和國內觀眾的視野中,比如《長江圖》(導演楊超)、《路邊野餐》(導演畢贛)以及《冬》(導演邢健)等等。在這三部影片中,《路邊野餐》和《長江圖》的風格傾向于作家電影,而《冬》的風格則傾向于表現主義。雖然先鋒派電影流派紛呈,但先鋒派電影的創作者可能同時接受多種思想潮流的影響,某些創作者可能橫跨若干個類型或流派,某些創作者可能難以歸入任何一個類型或流派。正是考慮到這些因素,也只能將以上三部電影作品列入某一個近似的范疇當中,所涉及的創作者與電影作品上的標簽只是一個大致的概念。
二、建構主義電影《紅塵之門》的創作核心
(一)結構特點
建構主義電影起源于蘇聯,是前期先鋒派電影之中的亞類型。在這一時期,吉加·維爾托夫創作的《扛電影攝像機的人》被看作是先鋒派電影中建構主義這一亞類型的典范。建構主義拒絕藝術中約定俗成的結構或者秩序,它主張將現存材料加以分解,然后按照藝術家的意圖,重新組織或者構建,并在工作中突出機械與技術的作用。
本文作者創作的短片《紅塵之門》采用平行蒙太奇的敘事手法,短片的兩條線索同時展開。一條線索記錄門外的各色人群,著重刻畫喧鬧都市群體中的生活細節;另一條線索記錄街頭獨奏二胡的老人,旨在傳達個體的精神狀態。兩條線索記錄的內容既各自獨立,又遙相呼應。同時,被記錄者雖同處鬧市,但群體的動態和個體精神上的靜態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關系。
(二)表現對象
“打倒銀幕上永生的國王和王后,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拍攝的普通凡人萬歲”是維爾托夫的電影理論之一,正如《扛電影攝像機的人》一樣,維爾托夫第一次將社會上的普通人作為世界的主人公搬上銀幕,這在當時是一個相當程度上的突破,也映射了維爾托夫電影理論的核心——反虛構的紀實性。
《紅塵之門》的創作者將拍攝對象鎖定為一個在都市街頭獨奏二胡的老人和一扇紅色玻璃門外各式各樣的普通人群。面對眾多的表現對象,創作者依舊堅持“不知不覺地記錄生活”的主張,影片中所有的表現對象均是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創作者捕捉并客觀真實地用鏡頭記錄下來的。正因為《紅塵之門》做到了真實地記錄生活而非像故事片那樣虛構生活,普通人平淡、平和的真實生活狀態才得以真實地表現出來。
(三)表現形式
維爾托夫在《扛電影攝像機的人》當中很少使用長鏡頭,他通常是將一個自然的整體或運動動作分解,編輯時再按照意圖將它們重新組接。《紅塵之門》的創作者在表現門外閑散的個人匯集成人群時,使用了一個長鏡頭。但在這個鏡頭的處理上,創作者同樣將這個自然的運動動作進行分解之后再重新組接,并在這些片段之間造成遞進、交換和沖突。
《紅塵之門》的創作者也堅持了“電影之眼”之關系與時間和空間的原則。創作者將時間上相互分離的現象在視覺上聯系在一起,以視覺事實的交流為基礎,將不同空間的人群在視覺上聯系在一起。第一條線索中,門外的各色人群記錄于廣西防城港市,時間為秋季,著重刻畫喧鬧都市群體中的生活細節;第二條線索中的在街頭獨奏二胡的老人記錄于四川省成都市,時間為春季。不同時間、不同空間的兩個原本獨立的表現對象,經過重新組接而聯系在了一起,既刻畫喧鬧都市群體中的生活細節,又傳達了個體的精神狀態。
三、《紅塵之門》在風格上的創新技巧
(一)聲畫對位
西方先鋒派電影在過去強調創造一種“讓畫面來主宰一切”的純視覺電影,不可否認的是,《紅塵之門》之中的畫面仍占據主導地位,但創作者對聲音進行過精心的設計。整部短片,創作者僅使用了三句旁白。它們分別為:1.也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我不再因為自己是一個普通人而感到自卑。2.我們都是普通人,說著普通的話,做著普通的事,然而讓我們真正感到幸福快樂的,可能并不是因為我們是誰。3.很多時候生活總是平淡的,而平淡的生活里,有著我們長久的堅守。三句旁白與短片的畫面齊頭并進,從不同的方面闡述著普通人平淡平和的生活狀態和他們的快樂,并在整部短片中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另外,音樂與畫面的對位也大大提高了短片的表現力。眾所周知,二胡是中國的古典樂器,它所代表的是傳統,而探戈作為西方音樂,它代表的是現代。創作者巧妙地運用聲畫對位的方式將街頭老人的二胡獨奏和探戈舞曲結合在了一起,以中和的表現手法將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東方和西方相關聯,這種普通人平淡平和的生活和精神狀態便拓展為全世界的共通。《紅塵之門》的結構篇幅雖短小,但創作者通過使用聲畫對位的方式,不光增添了短片表現對象的廣闊性,而且還豐富了短片的精神內涵。
(二)色彩表現
《紅塵之門》創作者吸收了印象主義電影和法國詩意現實主義電影的風格,并結合當今時代大背景下電影行業的發展,橫跨多個流派、多種思想潮流。短片除了含有明顯的蘇聯建構主義電影的風格特點以外,還體現出了濃厚的印象主義電影的風格。創作者在創作過程當中,抓住紅色玻璃門這個重要的物件,并將攝影機置于紅色玻璃門之后,創作者透過這扇獨特的門來觀察人,并通過攝影機真實地記錄下這扇門外各色人群的生活狀態。短片在片頭部分以全紅色的單色畫面為主,中間及片尾部分開始出現變化。
創作者通過攝影機的運動,使畫面產生單色和彩色之間的自然變化。單紅色畫面帶給觀眾強烈色彩沖擊的同時,伴隨攝影機的運動,又回到了彩色的真實環境中。甚至有一部分鏡頭,創作者通過畫面分割的手法,在同一個鏡頭中既包含部分單色畫面,又包含部分彩色畫面。如此一來,現實和幻覺的交替與疊加在攝影機的運動中,既顯得格外自然,又使得畫面具有更加強烈的張力。
(三)表現手法
《紅塵之門》在拍攝的手法上,靈活運用視聽語言。創作者綜合地使用了推鏡頭、拉鏡頭、搖鏡頭、移鏡頭、甩鏡頭、長鏡頭以及慢快門拍攝,在剪輯手法上綜合地使用了定格、慢速、疊畫等手法。在拍攝過程當中,創作者采取了一種隨意的、自由的拍攝方式,它使得短片的生活化氣息更加濃厚,也拉近了創作者與觀眾、觀眾與片中人物的距離,更加具有親切感。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紅塵之門》的創作者在短片的風格上顯然受到先鋒派電影思想潮流的影響,并借鑒了其他姊妹藝術的表現手法,比如《紅塵之門》的片頭和片尾分別出現的一個墨點和三個墨點,短片中出現的二胡獨奏者可以被看作是個體,另一條線索中的各類人群則被看作是群體。片頭出現的一個墨點象征了二胡獨奏者,而在傳統文化中,“三”為“眾”,片尾出現的三個墨點實際上則象征了門外各種各樣的人所組成的群體。但不論是單獨的一個墨點還是三個墨點,都是出現在短片的紅色背景之上。一方面它與片名《紅塵之門》形成呼應的關系;另一方面,所有的墨點都是單色畫面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這正象征著無論是短片中出現的人物還是觀眾自己,其實都是喧鬧都市之中的一份子,也是組成這個繁華世界的一份子。
四、結論
先鋒派電影充分挖掘電影的表現潛力,以創新的精神和追求積極地探索電影的表現形式,并創造出獨樹一幟的影像風格。先鋒派電影對電影藝術的追求使其具備了傳統主流敘事電影所不具備的某些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先鋒派電影都有它獨特的價值和值得研究的方面,和其他傳統主流敘事電影以及其他藝術作品一樣,先鋒派電影之中也有優劣之分。因此便要求先鋒派電影的創作者需要結合時代的發展,積極地進行探索,借鑒其他先鋒派藝術作品及姊妹藝術的長處,創造出獨樹一幟的電影風格,使先鋒派電影更具前瞻性和創造性。
1.華明.西方先鋒派電影史論[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6.
(作者單位:廣西藝術學院影視與傳媒學院)